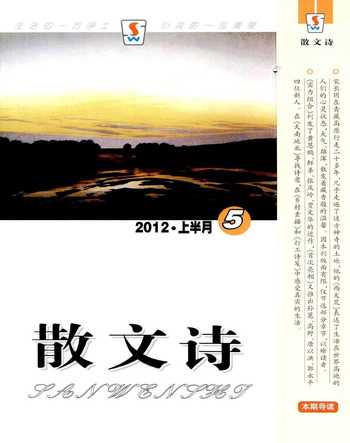賞析
許淇畫并文
少年時代,我擁有一本書攤上淘得的英國莎士比亞以后的名詩譯詩選集,其中就有葉芝的幾首我格外喜歡。那并不確實存在的令人神往的小島,名叫“茵尼斯弗利島”,或譯成別的漢字,念起來,鈴聲猶如一串鳥鳴。葉芝的愛爾蘭民間傳說中有這樣一個神秘的天堂,其實并不神秘,不過是他故鄉的可以終老的一隅,葉芝的詩從民歌來,單純而富音樂感,啟發和捕捉散文詩的調子——聲音和色彩的基調。我認為,抒情散文詩往往難在第一句開頭的定調,猶如閘門打開,往后即洶涌而至了,就在于你控制和疏導了。試讀葉芝的另一首著名的短詩《當你老了》:“當你老了,頭發灰白,滿是睡意,/在爐火邊打盹,取下這一冊書本,/緩緩地讀,夢到你的眼睛曾經/有的那種柔情,和它們的深深影子;”(裘小龍譯)不必分行,流暢地潺潺而下,是詩,也是散文詩。葉芝的詩,給予我寫散文詩捕捉聲調和意境很多啟發,他的散文也寫得好,我讀了去年出版的新譯本《帷幕的顫抖》,前一部分是自傳體回憶錄;后一半《凱爾特的曙光》是記事散文,兩部分每節散文中都夾雜詩句,散文和詩參半,可謂文中有詩、詩中有文。這種文體,值得散文詩人們借鑒。
這里介紹的哲理短詩,是葉芝經常自我譬喻的,說創作就像一棵樹的花與葉,雖然變化繁多,根,卻只有一根,這個根,就是祖國文化的根。葉芝在1923年獲“諾獎”,授獎詞說:“……將民族的精神以高度的藝術形式表現于詩作中。”20世紀初,愛爾蘭的民族解放文藝復興運動,葉芝是中堅和領袖之一,另有格雷戈里夫人、約翰·沁孤(郭沫若譯)的中譯本我也曾讀過,郭沫若翻譯的《約翰·沁孤戲劇集》,其中《騎馬下海的人》那特有的愛爾蘭風情和詩一般的臺詞,也是我散文詩創作的養料。
葉芝的創作風格很復雜。他早期著迷于民間藝術和神秘主義。他的父親是一位無名的“拉斐爾前派”畫家,那畫派的唯美和唯靈影響了少年的詩,后全家遷居倫敦,葉芝又結識了王爾德,因此,葉芝的創作道路,應該說是由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而漸轉向后期象征主義。20世紀初,現代派崛起詩壇,美國現代派詩人艾茲拉·龐德曾擔任葉芝的工作助手,晚期的葉芝,創建了自己的一套象征主義體系。和愛爾蘭民族復興文藝復興結合起來,具有宏大的歷史感,“把這樣一生的工作稱為偉大,是一點不過分的。”(瑞典諾貝爾獎授獎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