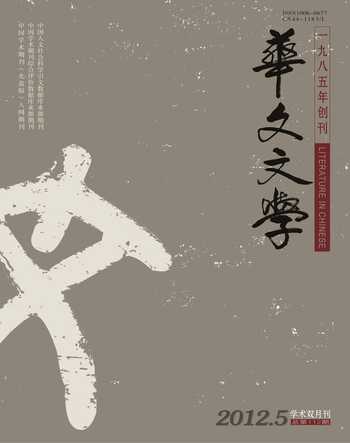鏡像內外:《第九個寡婦》中的中國/女性書寫
孟婷婷
摘 要:嚴歌苓的近期作品(《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等),因其中國現當代史的歷史背景以及完全“本土化”的題材,獲得的解讀多從女性主義視域、人道主義話語以及“重寫革命歷史題材”的角度入手。上述入手點誠然具有其有效性,然而“本土化”卻不能遮蔽嚴歌苓筆下“中國”以及“中國女性”書寫中的海外華文創作特質。對嚴筆下“中國女人”及“中國歷史”的解讀,不能忽視其海外華文作家身份、海外生存經驗及其所迎合的東西方市場。從《第九個寡婦》中關于“中國女人”和“中國歷史”的書寫入手,剖析其呈現中國歷史的“懸置式”方式及其回歸母體文化的“他者”路徑,可以透視嚴歌苓內在化于這一“本土化”“女性書寫”中的男權意識與西方目光,從而探究海外華文創作當下困境的“宿命式”根源。
關鍵詞:嚴歌苓;《第九個寡婦》;中國;女性;海外華文書寫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2)5-0017-12
嚴歌苓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初版于2006年。同她之前的幾部長篇一樣,《第九個寡婦》甫一問世即獲如潮好評,斬獲《當代》2006年度“專家五佳”、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提名等主流文學獎項,再版時更是由復旦大學學者陳思和作跋。然而,跟以前幾部長篇不同,《第九個寡婦》的故事并非上演在大洋彼岸,主人公也不再是心靈流離失所的華裔移民。表面上看來,這是一部嚴歌苓對母體文化的“回歸”之作:故事發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中原農村,寡婦王葡萄將土改中錯劃成惡霸的公爹從刑場上救回,秘密藏匿于自家紅薯窖中三十余年;三十余年里,“紅色”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運動令這個傳奇愈發驚心動魄,傳奇中同時展開著王葡萄前后與五個男人的情感糾葛(以及與七個男人的肉體糾葛),“好看”程度可以想見。語言風格上,嚴歌苓一改之前的優雅,換上一腔純正的河南土話,村野字眼也常常隨著人物對話形諸筆端。這樣看來,嚴歌苓似乎的確欲借這部作品回歸“中國”——如她所言,反思“中國”、“中國女人”及“中國的歷史”①。
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從2006年至今可謂汗牛充棟,論題多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和所有女性作家作品的命運相同,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的批評數量眾多,其中的討論重點又是嚴歌苓在《雌性的草地》及《扶桑》中業已形成、并繼承至《第九個寡婦》中的關于“雌性”或者說“母性”的表達。誠然,面對以女性為絕對主人公的文本,女性主義批評可謂“當仁不讓”,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第九個寡婦》中蘊含的政治性和時代性使其題材頗為吊詭,用單調的女性主義論證公式是不足以透析的。第二,“新歷史”角度的解讀。論者多認為王葡萄這個“小人物”的傳奇人生提供了關于當代中國“大歷史”的另一種“真實”,如其2010年版封面所言,講述了“大歷史中小人物的生命哭歌”②。這一視角也是筆者將要在本文中剖析并予以批駁的。第三,從“人性”層面展開的解讀。王葡萄尊重生命、相信人的價值,熱愛生命、盡享人生中的每一刻歡愉,對抗生命中的所有“異己力量”——對于人物的這種個性,從“人性”角度進行歌頌是無可厚非的,但同時又流于淺表。
作為一個旅居海外二十年之久、嫁作美國外交官之婦、任好萊塢專業編劇多年、作品同樣面向西方市場的華文女作家,文化意識的熏染、意識形態間的游走、商業利益的考量背后,其所提供的“中國視角”是否真能如陳思和先生所言,是“來自中國民間大地的、民族的、內在生命能量和藝術美”③,又是否真能提供對“中國”和“中國歷史”的另一種書寫呢?即想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提供某種可能。
一、“中國鏡像”中的“歷史記憶”
有論者稱《第九個寡婦》是“地窖中的歷史”④,的確,初讀之下,我們的眼球很難不被其中的“歷史感”抓住:開篇一句“她們都是在四四年夏天的那個夜晚開始守寡的”,即將讀者帶回“鬼子進村”的抗戰后期;緊接著插敘女主人公王葡萄的身世,三十年代北洋軍閥中原混戰時期的生靈涂炭于是歷歷在目;土改、大躍進、“文革”,統統抽象或具象成王葡萄眼睛里門縫兒外的“腿”——“十四軍”的腿、“老八”的腿、“紅衛兵”的腿;就連七十年代末計劃生育的推廣中,四十八歲的她也要和門外醫生護士的“腿”們較量一番,“掩護”強行被拉去結扎的年輕媳婦。顯然,從抗日到文革,故事主體的三十幾年跨越了歷史敘事中最為敏感的“紅色中國”時期,而如果我們將葡萄嘴里“洋和尚”、“洋姑子”的記憶也算在內,甚至可以說嚴歌苓是在通過這個“中國女人”的眼睛記錄現當代中國幾十年的歷史變遷。
嚴歌苓在一次訪談中談到《第九個寡婦》的創作動機時這樣說:“……這部小說就是那種非寫不可的故事……在國外的生活給了我地理、時間和心理的距離,使我意識到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是怎么回事。”⑤這一席話中的“野心”可謂昭然若揭:嚴試圖言說的,不僅僅是“女人”,也不僅僅是“中國女人”,更是“中國人”和“中國”;而故事中敏感的時代、巨大的時間跨度更明確地指向了“中國歷史”。換句話說,“中國”在嚴的這部長篇中被王葡萄這個“中國女人”置換,后者于是成為“中國”的鏡像;透過這個鏡像,嚴歌苓試圖折射的不僅僅是某個特定時段的中國,更有這個民族、這個“古老東方”的“神秘國度”中某種亙古綿延的質地。
以女性的身心體驗來演繹鬼魅的家國歷史,是我們的“民族寓言”被講述的重要方式。“中國”與“女性”的對位,實際上是由一重“他者”到另一重“他者”的鏡像轉換——由西方眼中“東方”作為“他者”,到男權眼中女性作為“他者”。的確,各自由“西方”和“男權”主導的兩重權力秩序中,“東方”和“女人”扮演了相類的角色:她們是弱者,但她們的存在同時令強者頗感岌岌可危;她們被“當權者”排擠,但同時又為權力秩序建立所必需——她們的存在令“西方”和“男性”這樣的主體性建構成為可能。有人說,“在后殖民社會里的西方人眼中,女人是今日世界最后一塊殖民地”⑥。這或許更點出了將“東方”與“女性”對位的深意:在“西方”的目光里,將不再負有殖民地身份的“東方”重新鏡像化為這“和平發展”的世界里“最后一塊殖民地”,恐怕是可以讓他們回味“帝國”記憶的最后一劑鴉片。
《第九個寡婦》中,由主人公王葡萄折射出的“當代中國”(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及其“歷史記憶”,大體上有以下三個主要特征。
凝滯的時空
主人公王葡萄的兩只“眼睛”,是《第九個寡婦》中反復出現的一個重要意象:“那兩只眼睛不太對勁——缺了點什么……沒有膽怯,不知輕重”;“只有她一對眼睛沒長成熟,還和七歲時一樣,誰說話它們就朝誰瞪著”;“七歲八歲的孩子盯人,眼睛才這樣生”;“月亮把她照得又成了十四歲、十六歲,兩眼還是那么不曉事,只有七歲”;“這雙眼最多六歲,對人間事似懂非懂,但對事事都有好有惡”;“葡萄眼睛還那么直直的”……這雙永遠停留在六七歲的眼睛,實際上正是葡萄非線性發展的時空觀的外化。
葡萄一生里呈現在小說中的幾十年,正是具有“超穩定結構”的中國農村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具撼動性的外界力量入侵的幾十年——入侵者,即所謂的“現代化進程”:土改,一舉摧毀了鄉土中國建立在宗族制基礎上的鄉紳制;“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粉碎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文革”,則與前兩者一起,毀滅性地顛覆了鄉土中國的道德規范和質樸信仰。上文中我們提到,所有這些入侵鄉土中國的外界力量在王葡萄那雙“生壞子”的眼睛里都被具象(或者說抽象)成了門縫兒外擠滿的“腿”。至于是日本鬼子還是八路軍,在她看來“都是同樣的人腿,不過是綁腿布不一樣罷了。有時是灰色,有時是黃色,有時不灰不黃,和這里的泥土一個色。”值得玩味的是,這些“腿”從來都只出現在門縫兒外,即便是已經進了葡萄家大門的土改工作隊的“腿”,葡萄也是將自己鎖在磨棚里透過門縫兒去觀察的。換句話講,門外的“腿”,“腿”的主人(日本鬼子、國軍、八路軍、紅衛兵、計劃生育工作者),以及“腿”所代表的外界入侵力量,從未真正侵入過王葡萄的世界,它們都是過客,用葡萄的話來講,就是“耽不長”——“兵荒、糧荒、蟲荒、人荒,躲一躲,就躲過去了”。小說用葡萄“想說給”右派老樸的一句話托出了她眼中門縫兒外的“腿”與門縫兒里的世界的關系:“十四軍來了,駐下了,后來又走了。八路軍來了,也走了。土改隊住了一年,還是個走。過去這兒來過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學生、日本鬼子、美國鬼子,誰耽長了?你來了說他投敵,他來了說你漢奸,又是抗日貨、又是日貨大減價,末了,剩下的還是這個村,這些人,還做這些事:種地、趕集、逛會。有錢包扁食,沒錢吃紅薯。”(第七章)這即是王葡萄的時空哲學:門縫兒里的“扁食”和“紅薯”的輪替是亙古的,絲毫不會隨門縫兒外“腿”的變遷而變遷。
正像她的眼睛不肯隨線性時間長大一樣,王葡萄的時空觀同樣超越在線性歷史進程之外,她的歷史觀是循環往復的,這也就決定了她的生存經驗實際上并未與歷史本身建立起有效的對話關系。這樣的敘事策略不消說有其迷人之處:和《紅高粱》、《白鹿原》等一批“新歷史”小說一樣,它規避掉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以“發展”這一線性特征來尋求其合法性的主流歷史話語霸權,拆解了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一類的話語建構,使得“小人物”在“大歷史”中得以凸顯,散發出“對抗性”的魅力。不過實際上,《第九個寡婦》與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末的“新歷史”小說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個話題我們會留待本文第二部分詳述。
傳奇的故事
不同于賈平凹對方術和靈異的迷戀,《第九個寡婦》的傳奇色彩是“現實主義”的——嚴歌苓不想讓神和鬼分散讀者對這片傳奇的古老土地本身的興趣。
故事里最傳奇的傳奇,自然莫過于王葡萄將僥幸逃生于槍決的“惡霸”公公孫二大藏在地窖里三十余載,并在公公生存經驗的指導下熬過了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在這個駭人聽聞卻又取材于現實生活⑦的大傳奇中,嚴歌苓穿插了數個小傳奇:活在世事紛爭之外、每年一次上山祭祖的龐大侏儒群族帶大了王葡萄的私生子;投共后又反共的銀腦十幾年后成了港商;葡萄先后與六個男人間的愛情或“非愛情”;失明的孫二大被轉移到山上的侏儒祖廟后和山中的豹子建立了惺惺相惜的情誼;以及小說結尾處,孫二大暗示葡萄是那位輪回投胎轉世、護衛家族的“祖奶奶”等等。
正因其無關乎鬼神,小說中“現實主義”味道的傳奇故事反而更為人物形象本身披上了散發著神秘光彩的羽衣。嚴歌苓試圖告訴我們,締造傳奇的,不是神鬼精靈,而是人,這片神秘而古老的東方土地上充溢著旺盛生命力的人們。這即暗合了嚴一貫于創作中傾注的人本主義熱情。
頗具張力的“性”
男人,與孫二大一道,構成了王葡萄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舞臺。性,于是成為《第九個寡婦》中推動敘事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葡萄”這個名字,被她鐘情的第一個男人——害癆病的戲班琴師朱梅解釋為“一碰盡是甜水兒”,隱晦地點出葡萄“能滋潤男人”的旺盛性活力。小說里,這個“風流寡婦”前后經歷過七個男人:懦弱無能的丈夫鐵腦,風流倜儻的琴師朱梅,為追求“進步”和親爹劃清界限的孫少勇,憨厚踏實的民兵隊長冬喜,最擅長“放火箭”的公社書記春喜,一度蜚聲文壇的右派作家老樸,甚至還有無賴、貪婪、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喪失人性的史五合——“她管他是誰,她身子喜歡就行。”葡萄的性觀念可以說是非常地“后現代”——實際上是非常地蒙昧、原始、貼合著最自然的人性萌動。
文中幾乎所有的性愛場面,嚴歌苓的處理都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歡愉,二是悲憫。葡萄很享受“那股快活的熬煎”,“男人在暗地里怎么這么好,給女人的都是甜頭”;天災、饑荒里,“她天天盼著天黑,和冬喜往床上一倒,就不饑了”;她看不上春喜的“革命”、“進步”,可在春喜的半強迫里,還是“怎么弄她她怎么帶勁,吭吭唧唧到最后打起挺來”;她不愛聽春喜滿口的“放火箭”、“放衛星”,但即便每次都要“把汗津津的手搭在他嘴唇上”,她還是常常和春喜“在墳院旁邊的林子里歡喜”,因為“這么饑的日子,沒這樁美事老難挨下去”。“悲憫”,則可以說是葡萄對眾生的情懷:她心疼害肺癆的朱梅“嗓子底下的小風箱”,“后悔自己走得太快”;她細心地注意到少勇“軍帽下露出的頭發又臟又長”,燒水給他剔頭;對“心里不愛,身子愛”的春喜,葡萄也會愛憐他“為了點麥種,把他愁得比他哥還老”;甚至當靠威脅、恫嚇強奸她的史五合那“花白的頭在她懷里拱來拱去”,她也會悲憫這個“一無用場、不長出息的男人”那“可憐巴巴的手”。
實際上,歡愉和悲憫幾乎是嚴歌苓筆下所有“性”的主題,尤以后者更顯著。《少女小漁》中,小漁把貞潔獻給她做義工時照顧的一位瀕死的病人,只因為“他跟渴急了似的,樣子真痛苦、真可憐”;《扶桑》更是將這樣一種被陳思和稱為“宗教精神”⑧的悲憫發揮至極致,扶桑無限豐饒,任勞任怨地供奉著踐踏她的男人,她“誠心誠意”地迎合男人們的占有劫掠,甚至感恩戴德。這些在主流價值觀、道德觀中被視為“無恥”的品行,在嚴歌苓這里卻被賦予了“母性”或“雌性”的魅惑氣息,從而上升為雌性的大度、寬容及對人性弱點的容忍;這種無私的給予于是越過世俗貞操的觀念,躲過文明道德的譴責,顯得無比合理而宏大。
當然,《第九個寡婦》中“性”的魅惑并不止于“雌性”被無限擴展的混沌氣息。與“新歷史”小說一樣,用被壓抑的情感和性去對抗文中那個個人無名化、情感無名化、欲求無名化的時代,是一種并不鮮見的反撥革命歷史敘述、將歷史情欲化、偶然化、個人化的敘事策略。只是,與上文中我們已經有所闡述的“凝滯時空”相同,這里的“性”雖可以推動情節,卻不似《白鹿原》中的性那樣具有推動歷史車輪的力量。這一本質上的差異,我們也會留待本文第二部分詳述。
二、“被懸置”的歷史
以上筆者歸納了《第九個寡婦》中“歷史記憶”的特征,而這部長篇中歷史記憶的吊詭之處也正于焉浮現。
從十二歲到四十八歲,凝滯的時空觀決定了王葡萄在這三十余載歲月中絲毫不為外界力量撼動的價值觀。土改工作隊把“老把眼睛藏在羞怯、謙卑以及厚厚的腫眼泡后面”的蔡琥珀變成了能用“階級覺悟”教育葡萄的婦女主任,卻沒能動搖葡萄“再咋階級,我總得有個爹”的認死理;“三反五反”把李秀梅的丈夫變成了過街老鼠般的“瘸老虎”,葡萄卻愿意和他嘮家常,幫他偷蜀黍;“大躍進”里,小學生們滿懷“共產主義的神圣”搶奪豬食大鍋去煉鋼,沒“覺悟”的葡萄為了自己喂的豬娃不餓肚子干脆一屁股坐到鍋里;當“年輕閨女、小媳婦的眼神”都“溫溫地”從“進步”的春喜臉上“摸過去,摸過來”時,葡萄卻“根本看不見他”;“樸同志”無論是當“著名作家”還是當“反黨老樸”,葡萄見了也都是讓他來幫忙剁豬食,在她看來,這不過是“過一兩年換個人打打”;看著那個“二流子”作派的女知青,葡萄心里第一個反應就是替她爹媽心疼她,葡萄眼里,她就是個“女娃”,不管什么知青不知青……故事行將結束時,孫二大多舛而堅韌的一生也即將走到終點,葡萄抹掉眼淚,她傷痛,但她不悲哀,孫二大的這一走是“老天收走”的,是順應她心中對生命、對動蕩人世的理解的:“誰說會躲不過去?再有一會兒,二大就太平了,就全躲過去了,外頭的事再變,人再變,他也全躲過去了。”
可見,和她的眼睛一樣,葡萄沒有過非生理意義上的“成長”,就像她看史屯的眼光,“末了,剩下的還是這個村,這些人,還做這些事:種地、趕集、逛會。有錢包扁食,沒錢吃紅薯。”——她看不到自己的生存環境隨歷史進程的變遷,因為她的眼光、價值觀、生存哲學和思維方式是無變遷的。小說甚至用王葡萄那人到中年仍然“緊繃繃”的腰臀曲線、那“水豆腐一樣嫩,粉皮一樣光”的俊俏臉蛋來強化這種時空的停滯,強化葡萄的“未成長”。因此,故事里葡萄雖然從十二歲長到了四十八歲,《第九個寡婦》本身卻不是一部《青春之歌》那樣奠基在線性時間觀基礎上的“新中國女性成長小說”。作為女主人公的王葡萄,始終出走在歷史進程之外,并未參與歷史并在其中接受脫胎換骨的淘洗。——這也正是我們在上文中懸而未解的一個問題,即《第九個寡婦》與“新歷史”小說在時空處理以及性因素處理上的本質不同:由于“個人”的“出走”,前者并未將歷史“個人化”、“欲望化”,“個人”與“情欲”在這里都不再具有《白鹿原》中推動歷史車輪、改變歷史軌跡的重大作用,個體經驗或者“力比多”都不再是原動力;相反,歷史在這里被“布景化”,為個體與欲望的展開搭建“舞臺”,“舞者”本身卻未能對這“舞臺”的架構、光澤、色度進行任何涂抹——只是,《第九個寡婦》的舞臺(“紅色中國”)足夠多義也足夠光怪陸離,模糊了個人與歷史之間未能粘合的突兀觀感。
這一“時空凝滯”的敘事策略于是在無形中抽空了歷史、將歷史懸置,那么,這個用“大歷史中小人物的生命哭歌”來概括的故事是否真的說出了“大歷史”?王葡萄這個“中國鏡像”那凝滯的、無縱深感的歷史記憶又是否可以就此等同于“中國”的歷史記憶或其一部分?——“地窖中的歷史”的提法,或許應該被質疑了。
三、被疊加的“東方鏡像”與“人性”話語
問題的關鍵于是聚焦到王葡萄——這個在文中承擔了折射“中國”與“中國歷史”重擔的鏡像上。嚴歌苓用以置換“中國”的這個鏡像,到底能否勝任,這有待我們一層層剝開王葡萄這枚“洋蔥頭”,對這個人物形象的結構加以剖析。
無法掙脫的“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
毋庸置疑,進行創作的文化身份及話語背景、甚至作品需要去迎合的消費市場都會對創作本身產生“潤物細無聲”但同時又相當根本性的影響。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女人”,嚴歌苓跨國婚姻的修成正果、美國身份的獲得決定了“自我”與“他者”的界限開始模糊。那么,即便堅持漢語寫作,這些既要講給中國人聽、也要講給海外華人和西方人聽的故事中,恐怕很難不交織著意大利導演貝爾特魯奇所言的“縱橫交錯的目光”⑨,即內在到嚴歌苓自身創作中的紛繁的話語建構與文化景觀。
在上文中我們引述的創作談中,嚴歌苓將創作動機最終指向了“中國女人”——這個音節頗為簡單的復合詞,本身已經很值得玩味。“中國”,特別是嚴歌苓從事創作的西方話語背景下的“中國”,指涉著西方對“古老東方”包括“孱弱”、“神秘”等在內的各種指認;而“女人”,又添了一層父權社會的凌越。這一“雙重壓迫”下的族群,實際上是嚴歌苓再熟悉不過的一類。“王葡萄”之前,嚴歌苓樂此不疲地描繪著的是一個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⑩。從和美籍意大利老男人“假結婚”的小漁,到迫于生存被同性戀者“借腹生子”的伊娃,再到將“雌性”光輝散發到極致的舊金山頭牌妓女扶桑,嚴歌苓對這一掙扎在種族、性別、階級、政治等多重邊緣的群體的描摹越發駕輕就熟,她也愈來愈熱衷于構建“東方/中國/女性”這一話語結構的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講,王葡萄好像是不同的——她沒有經歷過生存環境與文化環境的“移植”,她好像不必被強調“來自中國內地”。這樣一來,對這個形象的剖析就很容易直接陷入“年輕女人”所展開的女性主義話語空間——可王葡萄真的只提供了這一個層次上的可能性嗎?
的確,王葡萄十分“本土”。《第九個寡婦》告別了“無根狀態”、文化沖突等等海外華文文學的“御用主題”,十分“現實主義”地描摹了一幅四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的中原“鄉土浮世繪”,嚴歌苓甚至放棄之前精致優雅的文字,在河南方言上下了一番大工夫。難怪有人說,“嚴歌苓在《第九個寡婦》里開始尋求著對‘母體文化的歸依”{11}。但實際上,這種形似“鄉愁”的“歸依”早在《扶桑》中業已開始——甚至可以說,它自嚴歌苓“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12}的最初就淡淡地滲進嚴歌苓的創作中,滲進她筆下每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的血液里:她們可能面目模糊,但多數有“麻花辮”或“大髻”的標志,衣著要和“絲綢”扯上些關系,首飾非翠即玉;她們常常需要一個“出賣”的職業,出賣肉體,或者出賣尊嚴;她們在異質文化面前異常柔弱,集中表現為在“性”上的“包容”或者說旺盛活力,但這種孱弱在嚴歌苓筆下又被闡釋為“母性”的包容,甚至披上了一層來自“古老東方”的、“雌性”的光輝,因此可以在弱到最弱處,彰顯強大的力量,同時收回被出賣的尊嚴。這種敘事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來自邊緣文化的女性繼續掙扎在“被看”的他者的邊緣;第二,“神秘的東方”賦予了她們神秘的力量,這種力量又常常要通過“性”的渠道來傳遞。和她們一樣有一半市場在西方的葡萄,會有何不同嗎?
“粉底兒白花”的緞子小襖,“簡直就是整個一個女人身體”的手,“又白又宣乎、兩顆奶頭紅艷艷的”的“一對奶”——哪一處不吸引著西方男人“欣賞東方古玩”{13}一般的目光?將死里逃生的政治犯藏于紅薯窖三十余載,身懷六甲照樣站在秋千上直入云霄,剪得出“連環套連環”的窗花、輪回轉世、護衛家族的“祖奶奶”——哪一樣不指涉著“新奇而神秘”的東方生活?“打散的麥秸上”葡萄汁液一樣漫溢的女體汁水,在蜀黍棵里“嘴巴叼住嘴巴”,“心上能一下子放下這么多男人,個個的都叫她疼”——又有哪個歡愛的場景不指向東方女性旺盛的生命活力與性活力?
可見,正如《扶桑》一樣,《第九個寡婦》建構了“他性的、別樣的,一種別具情調的‘東方景觀”{14},其中對“母體文化”的歸依并不是純粹的“鄉愁”,而是滲透了西方對東方的文化想象與文化期待。與嚴歌苓筆下“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無異,生長在鄉土中國的葡萄還是被貼上了“東方”的標簽、帶到了“西方”面前——這無疑是被海外華文寫作的話語背景與市場導向所命定的——“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于是成為嚴歌苓筆下女性形象無法掙脫的身份建構。嚴歌苓將對“他者”目光的認同深刻地內在化,這種“自我東方主義”{15}氣質,讓她在父權制下,重復著男人的敘事;在后殖民的時代,回應著殖民的話語。
有人說嚴歌苓的“華人故事”描摹的是“一群清醒逃離第三世界生活處境的出走者”{16},其實葡萄也一樣——她凝滯的時空觀、她對“進步”或者“革命”的拒絕姿態,本身就是嚴歌苓清醒地安排的一次“出走”——她選擇生活在那個古老的、封閉的、有著內部運行秩序的“神秘東方”(但同時這個“東方”及其連帶的一切特征本身又是西方的建構),逃離“第三世界”這樣一個純粹政治經濟化的、剝開神秘面紗后赤裸裸地以其物質貧乏和經濟落后示人的、不再散發著“東方”惑人魅力的語境。
但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又要作為歷史布景展開在故事里,因為它代表了意識形態上的別種“他者”,由此同樣具備“可供觀賞”的差異性——特別是當她們的舞臺被設在“紅色中國”的歷史幕布下。50~70年代因此成為嚴歌苓赴美后關注最多的歷史時期:《天浴》控訴了極“左”意識形態對人性和青春的扼殺,《人寰》隱喻了“文革”中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出賣。前者摘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最佳實驗小說獎”及臺灣“全國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一等獎,后者則在臺灣獲得“《中國時報》百萬小說獎”。這背后,不能不說意識形態上的冷戰邏輯起了一定的作用。
嚴歌苓將“紅色中國”的幾十年稱為“物質饋乏的幾十年”,并認為在這種匱乏里,“中國最豐富是故事,種種離奇的故事”。海外經歷告訴她,“美國的同學都羨慕我們中國人的閱歷,因為他們美國作家筆下最慘的悲劇也不過是亂倫之類的”{17}。顯然,西方對那“慘無人道”的幾十年獵奇的目光是嚴歌苓選擇講述這類“離奇”故事的重要動因之一。
綜上,《第九個寡婦》中,“中國內地”是王葡萄這一形象的重要一層。“土生土長”沒能助她逃出“父權”和“西方”等多重話語,創造者內在化的西方目光把扎根于中原鄉土的葡萄變成了“中國女移民”系列中的新形象,給她貼上“東方風情”和意識形態的標簽,一方面迎合著西方始于若干世紀前、卻至今未能被現代交通和傳媒顛覆的東方想象,另一方面滿足著他們“自由與民主”話語的優越感。
“民間的地母之神”
陳思和先生對《第九個寡婦》的解讀是用魯迅先生的兩句詩起興的:“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陳先生認為,“慈母讓人聯想到中國民間地母之神,她的大慈大悲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永遠是人性的庇護神。地母是弱者,承受著任何外力的侵犯,但她因為慈悲與寬厚,才成為天地間的真正強者,她默默地承受一切,卻保護和孕育了鮮活的生命源頭,她是以沉重的垂淚姿態指點給你看,身邊那些沐猴而冠的‘大王們正在那兒打來打去,亂作一團。莊嚴與輕浮,同時呈現在歷史性的場面里。”《第九個寡婦》中的葡萄,正是這位以“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為“兩大特點”的“地母”,她將“人類的愛的本能、正義的本能和偉大母性的自我犧牲的本能高度結合在一起,體現了民間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質”。同時,陳先生認為,王葡萄所體現的美學準則是“來自中國民間大地的、民族的、內在生命能量和藝術美”。{18}
可以說,“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確實準確地概括了葡萄的質地。她舍命救下了劃成“惡霸”的公爹,背著這個沉重的秘密挺過了三十余年;她實心實意地幫著寡婦李秀梅一家活命,毫不介意“瘸老虎”的階級敵人身份;她心疼少勇“沒人給洗被單”,心疼老樸從小就是孤兒,心疼懷上了野娃子的女知青;好不容易熬過三年的大饑饉,她還記得“給了花狗兩個饃一盆湯”;她甚至舍不得殺那頭看著自己長大、已經老得站不起來的驢,又擔心它半夜死了,“披上被單坐在它旁邊”。她體諒萬物,和牲畜講話也要用“咱”,的確是一種“渾然不分的仁愛”。
她同時也在用最寬廣的胸襟包容命運拋給她的一切。水災卷走她的家人,逃難的鄉親一起做主把她賣給孫家,她就在孫家踏踏實實地活,“頭一天吃罷晚飯就上了鍋臺”。丈夫被冤枉成“奸細”打掉了半個腦殼,婆婆被日軍炸死在回家的鐵路上,公爹繼而被打成惡霸分光了勤儉持家攢下的家產,她看似別無選擇地包容了時代的霸權,實際上是在包容人生路上的“熬一熬就熬過去”的小挫折。和平生愛的第一個男人只說過一晚的話,等了兩年等來的卻是死訊;被她視為家族與愛情希望的“二哥”差點親手斷送了公爹的性命,也斷送了葡萄心中剛剛點燃的激情;在大饑荒中給她溫暖的冬喜為救人死在塌窯里;老樸和她也只能跟隨“大形勢”做做露水夫妻;葡萄生命中的男人,不是留不住,便是對她不起,她卻依然肯相信愛情,包容男性人性中的弱點,如慈母一般關愛、保護、縱容與原諒。
然而,這“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真的如陳思和先生所言是“來自中國民間大地的、民族的”嗎?實際上,“地母”這樣一種類似宗教的精神向度在王葡萄之前的“舊金山名妓”扶桑身上早已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扶桑》中,嚴歌苓著迷于“跪”這個被賦予了屈辱意義的動作:“……跪著的姿式使得(扶桑)美得驚人,使她的寬容和柔順被這姿式鑄在那里。她跪著,卻寬恕了站著的人們,寬恕了所有的居高臨下者……”{19}筆者實在難以從這一對“跪”的解讀中透視到“中國民間大地”、“中華民族”——我們恐怕不能把十九世紀末國人面對侵略者的麻木解讀為“仁愛”與“寬恕”;相反地,它使筆者產生了一個并不十分恰當的聯想,即《圣經》里“不要反抗惡行,誰要打你的右臉,把左臉也伸過去”{20}的教義。這樣的宗教精神,究其實質渲染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彌散著西方話語中所謂的“人性的力量”。
這里我們還是要回到嚴歌苓的海外求學與創作背景。初到美國,嚴歌苓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攻讀英文寫作碩士。在那里,與其說她在接受嚴謹的英文寫作訓練,不如說她開始誠懇地接受西方文化中“人道主義”話語的規訓。正如她在訪談中所言:“原來我是喜歡美國的!因為我喜歡的就是這樣一個美國精神,它是一種文化里帶出來的。”{21}這種精神上的源流關系主導了嚴歌苓小說中對“人性”的關注,她喜歡觸摸和挖掘東西方人性在特定時空磨礪下的或光輝綻放或畸形扭曲,她認為“無論中國人還是西方人,有趣的故事說到底,都是能最深地體現人性的故事”{22},“人道主義精神”是“很多文人他寫得好”{23}的精神根基。
葡萄們和扶桑們身上閃耀的“母性”和“雌性”正是“人性”的嚴歌苓式的表達。嚴歌苓認為,這種將“女性”“人性化”的處理,其意圖是“否定女性是第二性的論調”,凸顯陰柔面對陽剛時在“生理、心理、甚至性的持久上”更“長久”{24}。她甚至用動物世界中雄性對雌性的爭奪否定女性“第二性”的定位。
因此,嚴歌苓筆下的東方女性,常常是西方男人主動追求的對象。然而,這種追求中包含著“看”、想象和征服,作為被追求者的東方女性并不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嚴歌苓并未意識到這種被追逐中的不平等,在一個個東方女人為西方男性青睞的故事中,她頗顯自得。同時,通過對“母性”和“雌性”的定義,她抹去了兩性間的權力張力,將性別政治中的男權壓迫單一化為母子關系中兒子對母親的撒嬌搗蛋、母親對兒子的憐愛縱容。
由此可見,“地母”般宗教關懷的實質,是自文藝復興起一直活躍于西方話語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并非“來自中國民間大地的、民族的”力量。而嚴歌苓通過“母性”、“雌性”對人性的解讀中,又不自覺地流露著已經內在化了的男權目光。可悲的是,這種“人性”話語在當下可謂“東西通吃”:西方人眼中,“紅色中國”史早已被充分妖魔化,源自自身文化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在這妖魔化的歷史幕布前優越性十足,成為自己用“人權”進行政治施壓的有力聲援;在中國讀者這里,用“人性”而非“革命”來觀照的歷史記憶本身已經足夠新奇而魅力四射,我們對這種對抗宏大敘事的個體形象的期待好像絲毫沒有在業已長達三十余年的后文革時代中退潮。
綜上,《第九個寡婦》中女主人公王葡萄這一形象實際上只有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是“東方”,二是“人性”。至于同樣構成看點的意識形態因素,如前所述,只作為舞臺布景存在,不參與角色構成。顯然,王葡萄這個“中國鏡像”,作為“東方景觀”和“人道主義話語”的合體,其折射“中國”的能力是堪憂的。換句話說,《第九個寡婦》所提供的“中國當代史”記憶,既不“中國”,也不“歷史”,它正像陳凱歌匠心烹制的《霸王別姬》,雖然“太過清晰地指稱著中國”,但“它既不伸延向中國的歷史,也不再指涉著中國的現實”{25}。或許,嚴歌苓想用王葡萄時空觀的凝滯傳遞“古老中國”具備的某種可以超越歷史、超越政權暴力的質地,但一位因“人性”標簽而具備了普適性的“地母”,又怎能真正折射出何為“中國女人”、何為“中國”、以及中國的歷史與個人到底呈現著何種關系?
四、重構的“女性”與“鄉土”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說個故事給西方聽”的比較成規模的開端可能始自對諾貝爾獎有了自覺追求的“尋根派”。拉美文學在西方世界文壇上的大豐收讓“尋根派”看到了曝露“民族秘史”的驚艷效果,于是,道家文化(《棋王》)、神秘的蠻荒之地(《爸爸爸》)、歷史背景模糊的世外桃源(《受戒》)等等“東方景觀”成為文學熱衷的表現對象;其中,反抗幾十年本土歷史壓抑的文本(《紅高粱》、《罌粟之家》等)成為重要的一支。然而,這種文學題材上的繁榮似乎遠遠不及關乎“國族”和“歷史”的影像在銀幕上那么耀眼,“第五代”關于歷史的講述,讓“大紅燈籠”映紅的“東方”攜著妖嬈的風情出現在西方面前,稱職地扮演了“他者”的角色——高粱地里火紅的生命力與性活力(《紅高粱》),老房子中被扼殺的個人與欲望(《大紅燈籠高高掛》),京劇舞臺上濃墨重彩的性別錯亂與意識形態壓迫(《霸王別姬》)——這種“有意識的與公開的”{26}民族寓言,既言說著“第五代”的輝煌,又宣告了“第五代”以“拒絕進入文化、歷史的象征式,拒絕與主流電影、主流文化作出任何妥協”{27}為精神旨歸的生命的終結。
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歷史已然向前邁進了二十余年,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緩解(或者說控制的形式發生了變化),經濟起飛中,國人“大國崛起”意識也在膨脹。“民族寓言”中的“東方景觀”和“他者目光”雖然無法擺脫,時代語境畢竟已經不同。《第九個寡婦》,作為一部產生于海外女作家之手的“鄉土浮世繪”,在對“女性”和“東方”的處理上正體現了視角的某種演進。
女性——用另一種方式重入秩序
戴錦華在談及女性形象于第五代鏡頭中的“復活”時這樣說:“……第五代將文化反思運動的內在矛盾推到了極致……為了徹底解脫這一困境……必須借助女性表象來重新加入歷史、文化與敘事。正是在第五代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視野終于再次出現,并且因男性欲望的目光將女性指認為一個特定性別的存在……女人的進入,不僅為第五代提供了懸置已久的象征性的成人式,解脫了其‘子一代無名、無語的狀態,而且為他們提供了敘事之復歸的契機。”{28}在同一篇文章中,戴女士從“男主角的視覺缺席”出發剖析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欲望主體、欲望視域的發出者的懸置”{29},這一懸置又為西方將自己主體化提供了空位,于是,“女人”作為一個符碼,不但重構了“男權文化中傳統女性規范的復歸與重述”,同時重構了西方話語秩序中的“東方”文化屈服,“將躋身于西方文化邊緣中的民族文化呈現為一種自覺的‘女性角色與姿態”{30}。
第三部分中,筆者已經簡要闡述了王葡萄是如何被內在于男權與西方這兩重秩序中的。只是,女性重新進入并建構秩序的方式,在嚴歌苓這位自“出道”起就著眼于兩性性別差異、關注女性生存與心路歷程的女性作家筆下,自然與張藝謀、陳凱歌鏡頭中所呈現的有所不同。
首先,開卷之前,故事的名字已經告訴我們,故事寫的是個“寡婦”。小說開篇就直接呈現了王葡萄被變成寡婦的那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情節;接下來和五個男人的情感或肉體癡纏都沒有再給她一個“妻”的身份;故事行將結束時,葡萄與孫少勇的正式結合似乎已是板上釘釘的事,但畢竟一直到故事講完,這段新姻緣也只是作為暗示出現。同時,小說對葡萄死去的丈夫鐵腦的插敘非常簡潔,幾乎全部描寫都指向了鐵腦的軟弱、無能、怕事、不成器,以至于孫家收賬要靠葡萄,被村里人笑話孫家“母雞打鳴”。
“寡婦”成為女性社會屬性的一個重要分類,本身是男權壓迫的一種體現,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寡婦”的身份雖然不能屏蔽男權,卻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王葡萄屏蔽了夫權。短命的丈夫懦弱無能,孫家公婆又同待女兒一樣待她,因此,不同于深陷“奪夫之爭”的“頌蓮”(《大紅燈籠高高掛》),葡萄生活中可以說并沒有令人窒息的夫權壓迫。再加之父母早亡,葡萄對公爹的救護又被嚴歌苓闡釋在了“人道主義”的層面上,唯一的兒子又被送給侏儒撫養,這樣,男權在《第九個寡婦》中給葡萄的,已經不再是具有“封建中國特色”的“三從四德”式的壓迫。換句話說,在嚴歌苓這位堅持強調“女性不是第二性”的作家筆下,女性向男權秩序的復歸超越了“夫為妻綱”的狹隘層面,作者雖然并沒有擺脫內在化了的男權目光,但至少不再以向西方展示“朽壞的古中國”為樂趣了。因此,《第九個寡婦》中女性“復歸秩序”的方式反倒更能令我們洞徹一種普遍意義上的“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強大力量,而非被以往遮掩于所謂的“封建中國精神糟粕”身后、面目模糊的陽具攜帶者(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從未以正面示人的陳老爺)。
事實上,這種“回歸方式”上的差異,源于兩種完全對立的回應“現代性”的立場。“第五代”身處1980年代“文化反思”的熱潮中,正如戴錦華所言,其影像的“初衷在于清算中國傳統文化的‘陳年古簿、‘膏丹丸散,掙脫歷史之軛,為現代化進程掃清道路”{31};但在“國學熱”如火如荼、“孔子學院”數量不斷擴大、“有朋自遠方來”伴隨奧運五環響徹全球的當下,現代性,可能反倒被更多地視為“一個陌生的、咄咄逼人的異己力量”{32},將那個“古老的、熟悉的世界”{33}推向沉淪。嚴歌苓或許想借這個“寡婦”重溫那個未被現代性入侵的鄉土中國非“封建糟粕”的一面,遺憾的是,曾經藏身于“三從四德”身后的男性目光還是借尸還魂——但至少,剝離了“夫權”的“寡婦”更能令我們透視到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男權壓迫。
可見,“寡婦”的身份設置實際上暗含了嚴歌苓意圖將女性從夫權中解放出來的某種嘗試,正因此,陳思和先生將標題改作“秋千”{34}的提議恐怕不太合適。
其次,王葡萄是個“快樂寡婦”{35}。筆者在前文中已經多次簡述過她多舛的人生道路:早孤,早寡,唯一的親人在迫害中奪了命回來卻至死不能見天日,有情人一一負她而去——可你看她活得多“興頭”,“啥也不勝活著”是她樸素的樂生信條,因為“如果女人認為男人給她的苦也是苦的話,那她最苦的就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當作第二性,女人是無限體,只要不被打碎打爛,她一直可以接受”(嚴歌苓語){36}。琴師朱梅死了,她坐在馬路牙子上哭過了還是去找門路救公爹;寡婦懷胎,她愣是瞞著孩子“革命”的親爹一個人生下來又安置妥當;大饑荒逼得只差人吃人,葡萄煮了豬食充饑,一樣吃得“滿嘴清香”,覺得“吃著真不賴”;無賴五合強暴了她,她用緩兵之計送他上了西天……小說里一再設問:“誰能難得倒她王葡萄?”“誰敢欺負她王葡萄?”不錯,王葡萄不投井、不上吊、從不為誰“消得人憔悴”,再苦的日子她一句抱怨都沒有,“葡萄是好樣的,她再傷心傷肺都不會撒手把自己摔出去摔碎掉”。但她并不是不反抗,她執著于生、勇敢去愛,在“寡婦”這一多重邊緣的身份中活得“喜洋洋樂滋滋”,活過了“頌蓮”和“菊仙”,活成了一個“強者”。
嚴歌苓力圖渲染的“母性”或“雌性”實質上遮蓋了兩性間的權力張力,將男女間的權力秩序簡化為母子情感關系。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嚴歌苓的這一視角使得她筆下的女性形象比異性形象更高大、更寬廣,也更堅韌。
可見,女性的觀照視角使得女性在《第九個寡婦》中雖然未能走出男權的目光,卻擺脫了被第五代用作清算傳統文化武器的命運,開始與男性而不是單一的“夫權”或“綱常”對話;同時,“抑郁而終”、“抹脖子上吊”不再是女性與殘酷現實、與男性霸權作斗爭的最終退路,女性在這里用超越男性的堅韌對抗著命運,活成了強者。
東方——走出“鐵屋子”
從“現代性”開始作為一種參照性的異己出現在中國文學里,傳統文化就是以魯迅先生筆下的“鐵屋子”形象示人的,這個意象一直延續至80年代,甚至在50~70年代文學中都并未消失,因為“現代化”始終從屬于主流話語。無論是渣滓洞烈士,還是“橫空出世”的人民公社英雄,其“奮斗目標”都是打碎舊制度、沖破舊藩籬、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到80年代,“鐵屋子”重新被具象化為《大紅燈籠高高掛》里陰森的老房子和■人的死人井,“舊中國”仿似固化在了這個意象里。
嚴歌苓談到自己的海外創作經驗時曾說:“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都是新鮮的,都是刺激。即便遙想當年,因為有了地理、時間,以及文化語言的距離,許多往事也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人省思的意義。”{37}可能真的是“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吧,身處“現代性”話語發源地的西方文化中時,嚴歌苓對傳統中國的解讀反倒并非“鐵屋子”式的。
《第九個寡婦》的故事展開在河南一個叫做“史屯”的村子里,因此有人稱其為“一幅中原鄉土浮世繪”{38}。鄉土,作為一個與“現代”、與“都市”相對立的概念,自出生之日起就內在了其與“現代性”的對抗性張力關系,是一個負載著“傳統”的所在。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嚴歌苓展開給我們的,是一片怎樣的鄉土。
可能有人會說,除了王葡萄,現代化大潮幾乎席卷了史屯的每一個人,連終日藏身地窖的孫二大都明白“這回跟過去都不一樣”,那么,史屯是否已經喪失了展現“傳統中國”的能力?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正如學者孟繁華所言,90年代以來,當代主流文學“根本性變化”的兩大特征之一,即對鄉土中國“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發現。“所謂‘超穩定文化結構,是指在中國鄉村社會一直延續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雖世風代變,政治文化符號在表面上也流行于農村不同的時段……無論政治文化怎樣變化,鄉土中國積淀的超穩定文化結構并不因此改變……政治文化沒有取代鄉土文化。”{39}這一特征在“先進”得“聞名全省”的史屯,同樣未被抹煞。
小說在前兩章用了大量筆墨插敘葡萄公爹孫二大的軼事,孫二大強干、慷慨、熱心、幽默的形象背后,浮現的正是鄉土中國的鄉紳自治秩序。“每回派糧,派不著他自己往里墊,就怕人說他沒能耐。人家挖個窯蓋個門樓,他去指手劃腳,這不中那不對,人家買個牲口置輛車,他也看看牙口拍拍木料,嫌人家買貴了,上當了。就連人家夫妻打架,他也給這個當家給那個做主。壯丁錢湊不夠,他賠上老本幫人墊,因為海口夸在前頭了,胸脯也當當響地拍過了,辦不成他就逞不了能了。”鄉紳階層主導下中國鄉村自治制度的存在,是中國現代化進程開始以后除共產黨政權之外的其他政權都未能實現基層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化的根源,因此,共產黨政權建立伊始,鏟除鄉紳階層是粉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農村獲得有效稅收的關鍵性步驟。作為調停史屯各項事務的“偽保長”,孫二大被打倒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而在這種必然面前,史屯人好像明顯喪失了冒死救“老八”的“仁義”,墻倒眾人推地將孫二大送上了斷頭臺——其實不然,細讀文本,我們很容易發現史屯人對這位鄉紳、對這種自治狀態的懷戀。
斗爭大會上,男兵們扯著嗓子喊口號,臺下的村民們卻“誰也不說話”,而在土改工作隊威逼利誘下才肯“抓耳撓腮地站起來”的史修陽,也要小聲說句“二大,得罪了”才開始“發言”,更何況,史修陽本身是一個被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啟者之一——鴉片——腐蝕了其鄉土性、徘徊在自治鄉土邊緣的形象。接下來,發言者對孫二大的各種指責中,都穿插了村民們沒敢說出口的鳴不平。同時,作者一直在強調“宏大敘事”氣氛的鼓動力量:
“他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一股怒氣在心里越拱越高。他們被周圍人的理直氣壯給震了,也都越來越理直氣壯。剝削、壓迫、封建不再是外地來的新字眼,它們開始有意義。幾十聲口號喊過,他們已經怒發沖冠,正氣凜然。原來這就是血海深仇。原來他們是有仇可報,有冤可伸的。他們祖祖輩輩太悲苦了,都得從一聲比一聲高亢,一聲比一聲嘶啞的口號里喊出去。喊著喊著,他們的冤仇有了具體落實,就是對立在他們面前的孫懷清。”
把二大送上斷頭臺的,不是瞬間喪失了仁義的史屯村民,是口號、是“白毛女”的煽情效果、是“這回跟過去都不一樣”的大勢所趨。
口號短暫的鼓動力量后,老婆兒們已經開始抹著眼淚慨嘆“孫懷清那人是不賴”,待到難捱的饑饉和荒謬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地席卷史屯時,人們早就“忘了孫二大是個被他們斗爭、鎮壓的人”,他們“常常漏嘴”:“孫二大活著的時候,咱這兒啥都有賣。”“孫二大活著就好了,他能把那孬人給治治。”兩句簡單淳樸的懷緬,已經展現了鄉紳自治下鄉土中國經濟、政治兩個方面的良好運轉,他們懷戀這樣的社會組織方式,“遺憾不再有這樣的長輩為他們承事了”。
文革后期,葡萄膽大包天的藏匿最終泄露,整個史屯竟然開始齊心合力保守這個秘密。鄰居李秀梅幫葡萄傳話,史老舅托葡萄帶豬尾巴、豬奶子給二大“磨磨牙”,連公社書記的媳婦都偷偷塞燒雞給“你舅老爺”。一場場政治運動過后,瘋狂過、仇恨過、相互嫉妒與傾軋過的他們重新回歸了平靜、祥和、靠“仁義”自治的社會組織形態。鄉紳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雖已缺席,但其用以協調鄉土中國生活秩序的原則,卻在《第幾個寡婦》中被暗示了悄然復活的必然性。可見,在《第九個寡婦》里,“鄉紳”不再是抽著鴉片一步步走向滅亡的惡霸地主,也并非“妻妾成群”、窩藏了一部“宮闈秘史”的富商;這個階層“無為而治”下的社會,不再孱弱、愚昧、麻木不仁、民不聊生——相反,她井然有序,安居樂業,被施加的“現代化”對其不過是一種打擾。
除這一涉及政治經濟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外,《第九個寡婦》同時展現了鄉土中國樸素的倫理道德觀。五合那么無賴,偷東西被抓也要央求“可不敢叫我媽”;冬喜為救危窯里的老太太,葬身在了塌窯里;葡萄接濟孤兒寡母,那是理所應當、不用謝、不用客套的;“三反五反”中被打倒的“瘸老虎”臨到自殺,也記著葡萄的話選擇了跳河,沒糟蹋村里唯一的那口井……《第九個寡婦》里沒有弒父、沒有性變態、沒有瘋狂的復仇,相反,倫理的力量、鄉土道德的力量重新浮上紙面;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那個在神秘的飄渺中朽壞得行將滅亡的傳統中國,相反地,她開始讓人生出希望來,這個希望不是“新世界代替舊世界”的現代性希望,而是源自對傳統倫理秩序中真善美的堅持與守望。
實際上,《第九個寡婦》中,連對鄉土生活細瑣的描寫都不再局限于土炕、大紅綢子、嗩吶花轎、敬龍求雨,在河南農村前后長達五年的實地考察讓嚴歌苓落在納鞋底、拌豬食、包扁食、焙蝗蟲上的筆墨像王葡萄干活兒一樣利索、漂亮,這是比只有“饃”、鴉片、裹在大紅色里的女人的“古老中國”真實得多的東方生活圖景。
《第九個寡婦》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再悶在“鐵屋子”里的、鮮活的傳統中國,她秉持著自己的秩序,堅持著自己的倫理,在包扁食、焙蝗蟲里真實而勤懇地生存。這里,關于“東方”的表述雖沒有徹底走出、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中既定的“東方景觀”,不得不說是一種視角上的進步。
《第九個寡婦》相對于“第五代”電影在表現女性和傳統中國上也有超越之處。雖然內在化了的西方與男權意識無法擺脫,但卻是嚴歌苓站在海那邊努力回望“中國”和“中國女人”的某種突破性的嘗試。
結語
以上通過對《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這一形象的剖析,透視了這一“中國鏡像”背后的自我東方主義意識,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這部小說所表述的“中國”、“中國女人”及“中國歷史”的質疑。但同時,其中東方女性帶著飽滿的樂生精神、以“強者”姿態回歸那個無法擺脫的“他者”身份,以及不能脫去的“東方景觀”中浮現的“鄉土中國”,又是不能被盲目忽略的。王葡萄,是一個游走在“女性”和“他者”之間的“中國女人”;而作為小說中的“中國鏡像”,這個形象又在某種程度上穿越了這個鏡像的限定。
事實上,作為嚴歌苓第一部題材徹底“本土化”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所開啟的這一“轉型”已經昭示了海外華文寫作所面臨的“御用主題”們無以為繼的困境。以《第九個寡婦》之前嚴歌苓的最后一部反映海外華人移民生活的長篇小說《扶桑》為例,她在其中巧妙地轉換人稱、將史料與故事并置,語言精致華美到有堆砌之嫌,可謂是一個“東方神韻”十足的“傳奇”,但閉門造車的無力感已然顯露,對跨國戀情的描摹也未能超出同類題材的“鏡像之戀”主題。這樣的創作困境下,將目光投向母體文化可能是海外華文創作的必然選擇。
遺憾的是,《第九個寡婦》的轉身——如本文所示——并不那么成功,這又昭示著海外華文寫作走出上述困境的舉步維艱——當文學成為產業、當閱讀成為消費,小心翼翼地取悅東西方兩個市場的海外華文作家們,恐怕還要和這種游走在“非中國”與“中國”之間的“中國表述”妥協很久。漂泊的“無根”狀態、文化的“臥底”身份使他們不能——潛意識中可能也并不愿意——實現對母體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歸依,這不是變更題材或者修煉“鄉音”可以改變的。
筆者從《第九個寡婦》中看到的,是嚴歌苓們已不愿再去重復“紐約客”的故事,但他們卻無法對抗自己“紐約客”的現實身份。因此,去講述一個“紐約客”被期望去講述的“中國”,對于他們來說,或許是宿命式的。
① 嚴歌苓在關于《第九個寡婦》的訪談中稱:“在國外的生活給了我地理、時間和心理的距離,使我意識到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是怎么回事。”《嚴歌苓說:“這是一個非寫不可的故事”》,http://www.sznews.com/reading/content/2006-04/26/content_105796.htm。
②⑤{34} 嚴歌苓:《第九個寡婦》,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③ 陳思和:《自己的書架:之五》,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wxhg/wxdl/userobject1ai1970192.html。
④ 金理:《地窖中的歷史與文學的個人——評嚴歌苓小說〈第九個寡婦〉》,《文藝爭鳴》2009年第2期。
⑥{11}{13}{15}{16} [美]陳瑞琳:《冷靜的憂傷——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特質》,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頁,第47頁,第48頁,第11頁,第50頁。
⑦ 嚴歌苓在訪談中曾提到,《第九個寡婦》取材于河南農村一個真實的故事。http://www.sznews.com/reading/content/2006-04/26/content_105796.htm。
⑧ 陳思和:《嚴歌苓從精致走向大氣》,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頁。
⑨ 轉引自戴錦華:《縱橫交錯的目光——后89中國藝術電影中的多重認同》,《皮圖游戲》,泰山出版社1999年版。
⑩ 嚴歌苓:《失眠人的艷遇》,短篇小說集《失眠人的艷遇》,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
{12} 嚴歌苓:《十年一覺美國夢——復旦大學講座的演講詞》,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頁。
{14} 滕威:《懷想中國的方式——試析嚴歌苓旅美后小說創作》,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
{17} 《足跡那么遠文字這么近——〈第九個寡婦〉塑造中國式地母》,收錄在“霓裳小軒”2009年5月制作的電子書《嚴歌苓文集》中。
{18} 本段中所有對陳思和先生所作評論的引述均出自《自己的書架(之五)》。http://sports.eastday.com/eastday/wxhg/wxdl/userobject1ai1970192.html。
{19} 嚴歌苓:《扶桑》,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頁。
{20} 參見《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節。
{21}{22}{23} 王威:《嚴歌苓“解析”嚴歌苓》,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274頁。
{24} 嚴歌苓在訪談《嚴歌苓說:“這是一個非寫不可的故事”》中表示:“我對女性是第二性的提法不以為然。”
在另一篇訪談《嚴歌苓新小說敘說農村史詩》中又說:“女性不是第二性,在生理、心理等等方面,甚至在性的持久上,女性都比男性長久,陰柔比強悍更有力量。”(http://news.sohu.com/20060310/n242231248.shtml)
{25}{32}{33} 戴錦華:《影片分析舉隅:〈霸王別姬〉》,《電影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6}{28}{29}{30} 弗·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張京媛譯,《當代電影》1989年第6期。
{27} 戴錦華:《性別與敘事: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87-199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1} 戴錦華:《遭遇“他者”:“第三世界批評”閱讀筆記》,《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87-199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頁。
{35}{36} 轉引自《論嚴歌苓小說中的女性世界》,華僑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作者張寧,第30頁,第23頁。
{37} 嚴歌苓:《〈少女小漁〉臺灣版后記》,莊園編《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頁。
{38} 梁振華:《理想主義、偽“新歷史”、電影化及其他——嚴歌苓〈第九個寡婦〉閱讀札記》,《藝術廣角》,2009年第五期,第12頁。
{39} 孟繁華:《當代文學:農村與鄉土的兩次歷史演變》,http://dadao.net/htm/culture/php/template1.php?id=9693。
(責任編輯: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