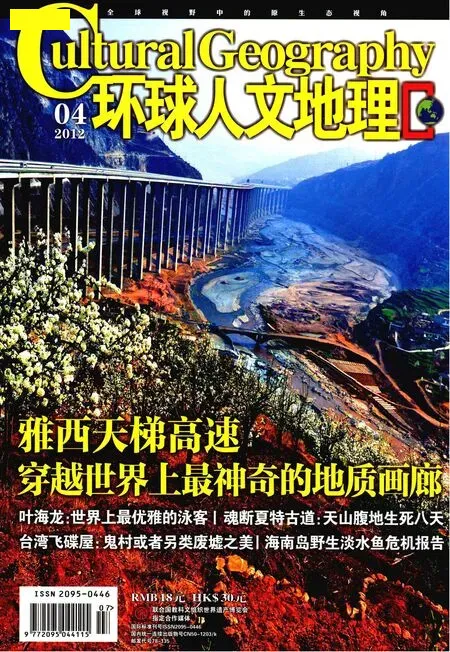草海獵魚遇險記
魏斷新
宇宙茫茫,自然蒼蒼,我自幼生活在大巴山、嘉陵江、渠江流域,那時這一帶有許多濕地,當地人叫它“草海”。小時候我常去草海,草海濕地讓我讀到了歲月的滄桑與久遠,從泥沼里逸出的,不僅僅是歲月風雨,還有歷史以及無數飄落的命運。
上世紀80年代,導演黃健中在拍攝由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燕兒窩之夜》時,還在嘉陵江一片長達二三十公里的濕地上拍到了優美的蘆葦蕩,然而十分遺憾的是,幾十年不到,在所謂“江河渠化”的影響下,那片濕地已修了堤,住上了人,種了莊稼,嘉陵江、渠江的草海、濕地早已蕩然無存。
蘆葦蕩里,草海上的夜色
記得第一次去草海,是一個深秋的早上,啟明星還掛在泛著青黛色的夜空,爺爺梅跛子就領著我上了路。那時,清涼的風吹走了我的朦朧睡意,也吹得滿山的白夾竹桃發出颯颯的響聲,像細密的秋雨灑在地上。跛子爺爺身上背著魚網、獵槍,還有煮飯用的鼎鍋、引火的干柴、米,劃船用的槳等,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在我前面移動。我真不知道他那小小干瘦的身軀哪來那么大的力氣,好像不知道累似的,還一路催我快走。
我們沿著山路走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到達湖邊。他往小船上裝那些東西,催我快上船。當時,我還不知道爺爺是在偷獵,因為那時政府已經頒布了不準打鳥的禁令,尤其是在草海棲息和繁衍的野鴨、天鵝、黑觜鶴、丹頂鶴等。而捕魚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魚蝦是構成草海生態環境中的鳥類的重要食物。當時,我只覺得爺爺是為了讓我去好玩,所以乖乖地上了船,坐在船頭,看著爺爺迅速地掛上槳,有節奏地用力劃著,在他的劃動中,小船無聲地劃進了草海,消失在了蘆葦叢中。
草海一片靜謐,在片片蘆葦叢中,不時露出一些彎彎曲曲的水道,水面上有氤氳的水汽在飄浮,一片蒼茫,水道兩邊的青草、蘆葦、花朵發出好聞的香氣和芹菜氣味兒,亮晶晶的水面上,無數蜻蜓飛來飛去,發出細微的響聲。偶爾還能聽見青蛙呱地一聲發出沉悶的叫聲,帶著水氣向四周溢散,傳得很遠很遠,更增加了草海的廣闊與無垠。在一片草灘上,棲息著一群漂亮的野鴨、大雁和幾只白鶴。我興奮地指給爺爺看,跛子爺爺卻“噓”了一聲說:“我們現在不要驚動它們,而且槍聲也會暴露我們。我們要先到草海中心去捕魚,待明天回來時再收拾它們。”
太陽升起來了,暖洋洋地曬得人直想打瞌睡,加上四周是一片死沉沉的綠,除了蘆葦還是蘆葦,我早已對此失去了新奇和興趣。中午,吃了點東西后,便在船頭睡著了。當我醒來時,月亮己經升起來了。
草海的夜色很美,銀灰色的月光如水銀一般在夜色中流淌。蘆葦、茅草在廣袤無垠的夜色中顯得很蒼茫,點綴其中的蘆葦蕩、沼澤、湖面如一顆顆珍珠一般,發出粼粼的波光。
草海湖泊里,不時有魚躍出水面,發出清脆的拍打水面的嘩啦聲。各種候鳥都在草海中棲息著。天鵝把頭插在翅膀中睡覺,一只只飄浮在水面,就像掉落在水中的朵朵浮云。在它們周圍,是一些用同樣方法睡覺的野鴨子,團團簇簇,像簇擁在天鵝周圍的斑斕的云彩。大雁則在蘆葦叢中歇息,它們密密麻麻地在草海的蘆葦坡地上睡覺,而坡地的高處,則佇立著幾只放哨的大雁。盡管如此,危險仍然會悄悄臨近,所以,看似寧靜的草海,卻并不平靜,到處都充滿生命的律動與喧囂和生生死死的競爭,許多動物都借著寧靜的夜色,活躍在草海之中,尋找著生存的機會。草海是它們賴以生存的天堂,而它們各自的生存,都遵循著一種自然法則,那就是物競天擇。
四周很靜,跛子爺爺的回聲傳來,顯得蒼老而沙啞,他自己聽了,起初也一愣,他沒料到湖水四周的綠色屏障竟會傳來回聲,好久才回過神來,開始戰戰兢兢地撒網打魚。不一會兒,他就打了半船鯽魚、鯉魚和十分少見的銀魚。他高興極了,嘴里也哼起歌來。
夜半遇險:大魚襲擊小船
也就在這時,跛子爺爺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他停住了手中的活,聚精會神地向湖心望去,只見湖水中陡起一陣條形波浪,波浪中有一條魚翅似的東西,如旗一般劃破平靜的湖面,正緩緩地向小船駛來。跛子爺爺看清以后便大驚失色,急忙收起網,對我大叫一聲:“快!娃子!拿起你手里的小槳,幫我快劃!不然,我們就沒命了!”
我聽了,也害怕、緊張起來,同跛子爺爺一起,飛快地劃著槳。小船飛快地向湖外劃去。
可是,那條大魚的速度也不慢,它很快便追上了我們,用它那碩大的頭不斷撞擊我們的小船,撞得小船顛簸著,有好幾次差點翻了過去。我甚至看見了大魚那瓦塊大小的金黃色鱗片和它那雙黑里透紅的大眼睛。不知為什么,那雙大眼睛里透出的光卻并不令人感到恐怖,而是某種憐惜、勸誡之光,甚至像奶奶的眼睛一樣,透著某種慈祥。后來奶奶說,那是因為大魚可憐我,因為我還是個孩子,不然的話,你那使壞的跛子爺爺,恐怕早就沒命了。不過當時我還是嚇得大哭起來,或許,正是因為我那帶著恐懼的響亮哭聲救了我們吧,大魚似乎聽見了哭聲,停止了撞擊小船,向我凝視了片刻,終于搖搖頭,一擺尾,甩開我們,向湖心深處游去。
跛子爺爺渾身冒著冷汗、熱汗,拼命地把船劃出好遠好遠,才在一片蘆葦叢中停下來,大口大地喘著粗氣說:“好險!好險!”
這時,跛子爺爺才告訴我,這魚叫鱘魚,老百姓叫它鰉魚,長的有兩三米,體重幾乎有一千多斤,力大無窮,常常可以用尾巴打翻一條小船。許多年前,他就曾經仗著年輕氣盛,帶了一把漁刀潛到水里去找鰉魚,想殺死它,在水里與鰉魚搏斗了一夜,結果是兩敗俱傷:鰉魚被他刺傷了多處,他也被魚尾抽得傷痕累累,有些地方還露出森森白骨。人和魚的血柒紅了大片的湖水,其狀令人慘不忍睹。要不是鰉魚負了重傷,他的這條命早就丟了。
不知為什么,聽了跛子爺爺的敘述,我心里涌上了一股復雜的感情,我不明白地問,鰉魚在湖里生活得好好的,爺爺你為什么要去殺它呢?爺爺聽了,沉默了許久,說:“娃子,等你長大了,你就明白了,這都是為了生活呢!”
可我還是不明白,為了生活,就可以去傷害別人或者別的生物嗎?它們也是有生命的啊!而且,我們在傷害別的生命的同時,不是也在傷害自己嗎?
對于我的問題,爺爺聽了,似乎不以為然,他說:“娃子!你還不懂呢!人吃動物,動物吃人,都是可以的,關鍵是誰能吃誰!這點你可要記住!不然,你以后長大了,可要吃虧呢!”
不知為什么,我聽了爺爺的話,小小的心靈變得沉重起來,許久沒有說話。在小船返回的路上,草海依舊是那么蒼茫,那么靜謐,但我依然感到了處處充滿許多神秘、恐懼,危機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