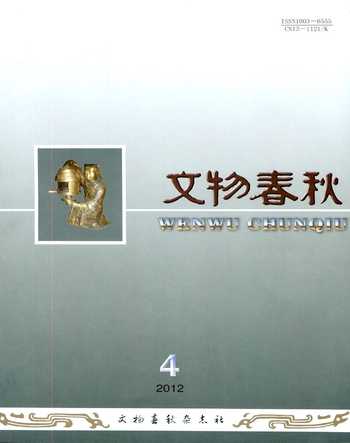兔形玉件的演變
穆朝娜



【關鍵詞】玉器;兔紋;兔形飾;演變
【摘要】玉器上的兔題材作品可歸納為單體玉器和兔紋玉器兩類,前者主要見于商周時期的片雕玉器和隋唐以后的圓雕作品,后者包括兔紋飾和宋明時期圖畫般效果的兔紋玉器。最早的兔紋玉器為嵌飾和佩飾,自隋代以后出現書鎮、耳飾等功能。在審視這些兔紋玉器時,有必要把它們置于歷史的長河中,并與其它類型的工藝品相關聯,從而能比較完整地去認識這類玉器。
在古代工藝品領域,兔是一個并不鮮見的裝飾題材。史前時期的陶器中有以此為飾的作品,比如石家河文化的兔形陶塑。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兔紋也偶有所見。漢代青銅器,特別是畫像石上的兔紋頗為流行。隋唐時期的銅鏡,兔紋或與嫦娥為伴,或為獵捕對象,更多的是作為十二生肖中的一員。玉器中的兔題材又是如何表現的呢?本文擬就這個問題及相關的背景進行討論。
一、最早的玉兔
目前所見最早的玉兔可能要算是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的兔形飾了。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兔形飾屬于凌家灘文化,距今5300年,起始年代大致與良渚文化相當。玉料受沁呈黃白色,與良渚文化玉器的外觀性狀相似。飾件由兔形的上部和榫形的下部組成,兔呈伏臥狀,但無足部表現,嘴前伸,似在嗅著什么,耳朵向后伸,背部呈弧形上凸,尾巴不似兔子反若魚,上翹分叉;榫部長條形,上面對鉆成四孔。整個器形與良渚文化的玉梳背相若,或許這件玉兔形飾也曾具有同樣的功能。倘如此,與良渚文化中既具有中規中矩的造型,又與神人紋飾密切相關的玉梳背相比,這件玉飾件顯得更加生活化,隱隱透露著幾分溫情。
史前時期的動物形玉器中,除了這件玉兔形飾外,再無可以確認的玉兔了。史前時期的玉器包括兩類動物造型,一類是想象出來的動物,另一類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動物。對后一類動物的表現,主要集中于飛翔的鳥、水中的魚、龜、蛙以及蟬等昆蟲,這些動物迥異于人類的生存方式,給了史前時期的先民們獨特的視覺感受,并成為他們借其神力與神靈進行溝通的媒介。另一些既不飛也不游的動物,或由于神異性差,或與先民的生活相去較遠,因而被先民們忽略,兔便是其中之一。玉兔在史前玉器中的缺位,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史前時期玉動物題材選擇的功利性前提。
二、剪影式的片雕玉兔
商周時期的玉兔出土數量較任何時期都多,且以片雕為主,表現的是兔子的側面形象,即所謂的剪影式藝術。但商與西周玉兔的造型與風格有別,體現了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不同審美取向。
商代玉兔主要出土于晚期墓葬,以伏臥蜷縮式和低首弓背式為主體造型,一般長3~5厘米,高1~2厘米,厚0.2~1厘米。伏臥蜷縮式的玉兔前后腿蜷屈于腹下,頭后縮,貼伏于前腿上,圓眼,大耳后伸,貼于兔背,短尾后伸,尾尖微上翹;一般在口部對鉆出圓孔,既可以系綴,也可以達到表現兔嘴的目的,但也有近尾部兩鉆一孔的;耳、目、腿及爪皆以單陰線刻劃出輪廓,除輪廓線外,再無其它裝飾紋樣,做工簡約粗率。伏臥蜷縮式玉兔表現了兔子安靜伏臥的狀態,隱含著一絲驚恐與不安。低首弓背式玉兔體現了商代玉工以圓為雛形制作玉器的設計理念,理論上當時制作的應該是一式兩件,分別由同一圓形的兩個半圓琢出。這樣的玉兔背部向上隆起,低頭,或后腿蜷臥、前腿半伸,或前后腿相互交叉若被捆綁在一起,尾極短且上翹,除身體的輪廓線外,又以陰線雙勾之法在玉兔身上琢出勾云紋。勾云紋是商代玉器上普遍施用的紋樣,呈現出高度的統一性,與玉器的表現題材無關,是一種符號化的紋飾。低首弓背式玉兔表現的仍是安靜狀態的兔子,溫順而馴服。
除了上述兩種形式外,商代晚期的玉兔還可見到一種比較活潑的形式,兔張口,頭略前伸,大耳后伸,但不貼于背部,后腿蜷曲,前腿前伸[4](圖二)。這種形式的玉兔與西周時期的玉兔更為接近,從而為我們尋找商代玉兔與西周玉兔的淵源關系找到了依據。
西周時期(主要是早期)玉兔的大小同商代差不多,但耳朵顯得特別大,向后伸展達身體長度的一半,且不再貼于背部,頸部明顯,臀部向上翹起,增強了兔子蓄勢待發的動感,口部有鉆孔,或口部與尾部均有鉆孔,尾極短,或僅表現尾尖,或順臀部下垂外翹,前后腿的下半部明顯拉長,與這一時期的玉虎等動物造型的肢體特征完全相同,體現了動物造型在腿部近乎程式化的表現方式[5](圖三)。西周時期玉兔的動感較商晚期更強一些,形象上更顯自然輕松。
三、寫實性的圓雕玉兔
商周以后至漢代的漫長歲月里,兔不再是一個玉工關注的題材。這段時間的玉器裝飾領域里,龍、螭、鳳鳥等神異類動物扮演著主要角色。隨著漢風的衰落,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嬗變,重新實現政治統一的隋唐王朝把玉器的制作帶進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現實生活的熱愛和寫實性表達逐漸成為藝術發展的主流。
隋唐至宋代的玉兔皆為圓雕,一般沉穩安靜,但細部的表現有所區別。隋代李靜訓墓出土一件白玉兔,長2.7厘米,高2厘米,昂首前視,雙耳后抿,面部細節不做表現,前肢并排伸于胸前,后肢蜷曲于腹下,首尾用簡單的陰線刻出毛發,其余部位光素無紋。這件玉兔的穿孔很有特點,在腹部左右橫穿。像這樣的穿孔實在讓人費解,如果穿絲帶系佩,玉兔便頭下腹上倒置過來,無法保持悅目的觀賞性,或許另有別用。
唐代玉兔的數量也不多。一件長2.45厘米、寬1.02厘米、高1.25~1.35厘米的玉兔,四足蜷縮于腹下,背向上隆起,以簡單的陰線刻出圓眼,僅粗具兔之形而已,但可以感覺出來它表現的是蜷縮成一團的兔子,安靜中帶點狡猾,并有一絲驚恐。玉兔上沒有穿孔,或為鎮。與此玉兔形象相若的還有一只當作印鈕的兔,印為漢白玉質,通高7.5厘米,通長13厘米,以兔為鈕,兔弓背,頭伏于兩條前腿上,后腿作蹲踞式。
宋代玉兔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玉兔了。這件玉兔是可以確認的最早的文房用品中的玉鎮,長6.7厘米,高3.6厘米。兔作伏臥狀,雙目前視,眼、耳、腿、尾等部位用勾撤法做出輪廓,以細密的短陰線刻出兔毛,寫實感更強。宋代墓葬中還出土一對水晶兔,水晶無色透明,兔作蹲臥狀,雙眼前視,兩耳豎起,前后腿微弓,無尾,用粗陰線勾勒身體的各部位,線條粗獷簡練[10]。兔背上下對鉆一孔,為唐宋時期玉器上常見的特征。
縱觀隋唐至宋代的玉兔,數量雖不多,但皆圓雕,兔呈伏臥狀,足、耳貼于身,或微外露一點,腹部橫穿一孔,或背腹豎穿一孔。由于采用圓雕的表現手法,玉兔較商周時期的片雕更為寫實,顯出溫順可愛的一面,功能已超越了單純的佩玉范疇。清代也有少量的兔形玉器,或為穿孔墜飾,或為十二生肖之一,造型基本如唐宋時期。
四、圖畫般效果的兔紋玉器
圖畫般效果的玉器最早見于宋代,這與宋代繪畫的發展以及文人氣息濃厚的審美情趣密切相關。宋代的繪畫作品中可以見到以兔為題材的作品,如北宋崔白繪有“秋兔圖”和“雙喜圖”,畫面中的兔子皆以樹石為背景,作半蹲回首狀。
圖畫般效果的兔紋玉器最早也見于宋代,是一件多層立體鏤雕的雙兔紋玉嵌件:一棵大樹枝繁葉茂,一兔半蹲,豎耳回首,另一兔臥伏,抬頭前視,地紋若山石之狀[11]。這件作品無論構圖還是做工,都體現出對遼代秋山玉的模仿,風格樸素自然,充滿野趣。
以植物為背景的雙兔紋玉器在明代還在繼續,但圖案的構成元素發生了一些變化。如湖北鐘祥梁莊王墓出土的雙兔紋玉佩飾,年代為明早期,圖案多層鏤雕而成,雙兔一大一小,但一兔半蹲回首、另一兔抬首向前的姿勢基本保持,植物紋的背景作折枝花式,有長著圓圓果實的荔枝,有修長舒展的蕉葉,靈芝狀云紋點綴其間[12]。若與宋代的同類題材相比,可以看出明代的雙兔植物紋已趨于圖案化。
五、充滿道教色彩的搗藥兔子
兔子搗藥題材最早見于漢代,是漢代人追求長生不老和信仰神仙世界的一種反映。漢代畫像石上的兔子搗藥紋中,兔子已不再是普通的兔子,而是一只仙兔,有的甚至長著翅膀,可以飛向神仙的世界。漢代搗藥的兔子更像是東王公與西王母的屬下,有的畫像石表現的就是兔子在他們身旁忙著搗藥和濾藥的情景。晉代的畫像石中始見兔子在圓形開光內搗藥于樹下的圖案,圓形開光是否代表月亮則不得而知。倘若如此,則由此搗藥兔子就與月亮扯上了關系。唐宋時期的銅鏡上可見到在月宮搗藥的兔子,除了桂樹外,有的還有起舞的嫦娥。
兔子搗藥題材在玉器上的表現遲至明代才出現。明代玉器中有雙兔搗藥,兔子相對而立,共持杵,一起搗臼中的藥。明代定陵孝靖皇后的棺內出土有一對金環鑲寶石玉兔耳墜,兔子直立,雙耳上豎,以紅寶石嵌飾雙眼,兩前爪抱杵作搗藥狀,下有臼,兔身上以細密陰線刻出毛發[13](圖七)。這些玉器為明代晚期的作品,與嘉靖帝崇信道教不無關系,雖然它們有的不屬于嘉靖當朝的作品,但仍留有那個時期的烙印,與嘉靖萬歷時期常出現的壽字紋玉器一樣,是傳統題材應時而復用的作品。
綜上所述,玉器上的兔題材作品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單體玉器,另一類是兔紋玉器。單體玉器主要見于商周時期的片雕玉器和隋唐宋明清時期的圓雕作品;兔紋玉器包括凌家灘文化的兔紋飾和宋明時期圖畫般效果的玉兔作品。最早的兔紋玉器為嵌飾,商周時期的片雕玉兔多數穿孔,主要當作佩飾,自隋代以后,以兔為題材的玉器作品應用范圍擴大化,涉及嵌飾、書鎮、耳飾等功能。商周時期的玉兔創作是否夾雜著與思想觀念有關的情感,尚需進一步研究,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佩戴這些玉兔的人非尋常之輩,而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這幾乎是早期玉器使用的一個通則。商周以后,玉器中的兔題材暫時缺位,但它卻活躍在漢代畫像石領域,成為畫像石上的一個重要裝飾題材,具有鮮明的信仰與觀念內涵,是人們心目中的仙兔,與長壽、不老密切關聯。王朝的更替無法阻止思想觀念的傳承,只不過有時為顯性呈現,如兔子搗藥題材的直接表達;有時為隱性顯現,如隋唐以后的圓雕玉兔或兔紋作品。雖然我們看到的是一只寫實性的兔子,但很難說它們身上沒有因漢代以來兔子被仙化所積淀的特殊情感。所以,在審視這些玉兔作品的時候,有必要把它們置于歷史的長河中,并與其它類型的工藝品相關聯,既關注它們的外觀性狀,也考慮它們的文化內涵,從而達到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統一,比較完整地認識這類玉器。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2]陶正剛等:《山西靈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3][4]唐際根主編:《安陽殷墟出土玉器》,科學出版社,2005年。
[5]寶雞市博物館:《寶雞
[6]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中),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年。
[7][8]古方主編:《中國古玉器圖典》,文物出版社,2007年。
[9]丁敘鈞編著:《古玉藝術鑒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參見楊立新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6),科學出版社,2005年。
[11]周南泉主編:《中國玉器定級圖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莊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下),文物出版社,1990年。
〔責任編輯:許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