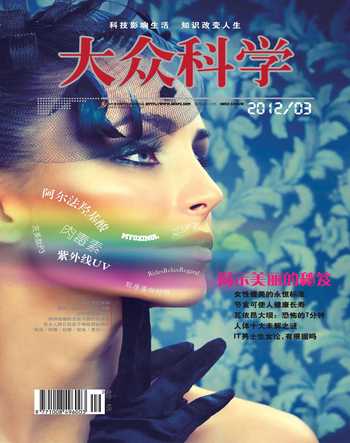瓦依昂大壩:恐怖的7分鐘
佚名
1943年,意大利剛剛結束墨索里尼的獨裁統治,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擺脫出來,整個國家早已滿目瘡痍,缺少從面包到汽車的幾乎一切物品。為獲得重建所必需的電力供應,也為了滿足電力集團對利潤的渴望,在亞德里亞電力協會的游說下,國會35位部長中的13位被召集起來,開會決定在意大利東北部阿爾卑斯山區建一座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大壩之一的瓦依昂大壩。
根據法律規定,要表決這類議題,必須有超過半數的部長到會,因此表決結果是非法的無效的;但1948年,意大利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路易吉·埃納烏迪還是批準了這一議案。
一場科技史上的大災難,正悄然而至。
先進的大壩設計
瓦依昂大壩位于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區皮亞韋河的左岸支流瓦依昂河上,離水城威尼斯僅90公里。阿爾卑斯山區良好的森林覆蓋和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使得這里春夏秋三季雨量充沛,山谷中河流淙淙,水利資源十分豐富。早在1939年,工程師們就進行了考察,提出了最早的設計方案:鑒于單獨一個山谷的溪流的水力較小、而相鄰山谷相距很近,還提出了修建穿山隧洞,將相鄰的峽谷湖泊、溪流聯接起來,集中水量和落差,建立大型水電站的工程構想。根據規劃,瓦依昂大壩的壩身達230米。1956年,大壩正式開工。
瓦依昂大壩的獨到之處在于采用了雙曲拱結構。雙曲拱是意大利人異乎尋常的靈感與想象力在服裝設計領域之外的卓越體現,這種壩體在水平和垂直兩個方向都呈弧形,前衛大膽的設計使載荷施加在壩拱上,減輕了梁的載荷,不但受力條件更好,可以承載更強的負荷,而且壩身可以造得很薄,節省了工期和用料。
為改善壩體應力狀況,沿壩體周邊還設置了一道像鉸一樣的縫,將壩體與其下的墊座分開,壩體從上到下也設置了4條水平縫,從而大大加強了拱的作用。為保證澆筑質量,所有這些縫都在冬季進行灌漿。地基也作了全面處理,進行了灌漿作業。考慮到兩岸巖體內裂隙發育,還采用了預應力錨索進行加固,左岸用125根,右岸用25根,每根長55米。大壩設計師、著名建筑學家塞門薩宣稱,瓦依昂大壩可以承受超過設計值11倍的負荷而安然無恙。
羅馬政客放衛星
上世紀50年代末是一個躁動的時期,大躍進的情況正在很多國家發生。那時正值世界核電開發的黃金時代。核電具有更高、更穩定的發電量,這無疑是比水電更大的誘惑。
1957年4月,瓦依昂大壩開工不到一年,羅馬的政客們便放了一個大衛星:大壩改成為核電站配套服務的抽水蓄能電站,高度從初始的230 米增加到264. 6米。這樣就使水位上升到海拔722.5米高程,其不但在雙曲拱壩中首屈一指,且成為世界第二高的大壩;庫容也增加到初始設計的三倍,達1.65億立方米。
設計方案換新,總設計師當然也換人,一顆新的高產衛星似乎就要冉冉升起了。
然而,瓦依昂山谷的地質構造卻不是那么令人鼓舞:數千萬年前這里是一片海洋,形成了石灰巖和粘土相互層疊的結構,石灰巖層間的粘土層在受水浸潤時極易形成泥漿,使巖層間的摩擦力降低,存在滑坡的隱患。施工剛開始,工程人員就發現左壩肩岸坡很不穩定,有學者提出有產生深部滑坡的可能性;但設計師認為深部滑坡不可能發生:一是鉆孔未查到深部有明顯的軟弱面,二是非對稱向斜起到天然阻止斜坡移動的作用;三是地震勘探顯示河谷兩岸巖石很堅硬、彈性模量很高。于是,施工照常進行,直到大壩建成,仍未對岸坡的穩定性及發展趨勢作出明確判斷。不過,設計師還是按常規,考慮了水庫可能發生的各種災害,如大壩壩體破壞、滑坡等問題,并在大壩下游及與居民點相近的地點設置了一系列諸如防洪墻、泄洪道之類防洪減災設施。
只有女記者蒂娜·梅琳在報紙上大聲疾呼庫區滑坡的危險性。由于她是意共黨員,她的呼吁被嘲諷為共產黨對私人企業不懷好意的干涉,并被以“散布虛假和誤導性信息可能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起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瓦依昂地區的村民們希望在此修建一座橫跨水庫的步行橋,卻被否定,理由是“庫區的地質條件不允許”。
災禍苗頭頻現
1959年秋天,瓦依昂大壩竣工。1960年2月,水庫開始試驗性蓄水。原本相對穩定的巖層在巨大的水壓下開始滲水,水和巖層深處的粘土發生作用,坡體開始變得不穩定。
同年10月,當水位到達635米時,左岸地面出現一道長達近2公里的裂縫。隨后發生局部崩塌,塌方體積達70萬立方米,壩前出現高達10米的涌浪。一個月以后水位上升到652米,崩塌滑坡再次發生,岸坡位移速度達到每天3.5厘米。
恐懼萬分的水電站工人連夜撤離,這次沒人敢無視問題了。蓄水隨后停止,水位被降至600米以下,位移隨即減少至每天0.3厘米左右。設計部門認為,水位上升引起孔隙水壓力上升是造成滑坡發生的關鍵因素,并認定降低水位上升速度就可以阻止滑坡發展。
在以后兩年里,這一措施有一定成效。可是,隨著蓄水和排水試驗的反復進行,岸坡位移也隨之時大時小,始終無法徹底消除,庫區地震也十分頻繁。
1962年底,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買下了瓦依昂水庫。為盡早通過驗收,從1963年初開始,蓄水試驗的步子再次加快。4月份,庫區水位達702米;7月中旬,水位增至710米,某些控制觀察點錄得每天超過0.5厘米的移動量;到8月份增加到每天0.8厘米。9月初,水位至715米時,位移速度增至每天3.5厘米。有關部門企圖降低位移速度,開始緩慢降低水位至705米,但從9月28起瓦依昂地區普降大雨,進一步惡化了岸坡結構,位移反而繼續增加至每天超過20厘米的驚人水平。瓦依昂山谷中發出奇怪的聲音,水庫里的水也變得渾濁,山腳下的公路在兩年的時間里移動了半米多。當地政府發出警告,惶恐不安的村民開始陸續逃離家園,然而這一切已經太晚、太晚。





恐怖的7分鐘
1963年10月9日22:39。連日的大雨這天剛剛停息。這是一個雨后晴朗的夜晚,瓦依昂山谷仿佛睡著了一般,夜幕下的一切都顯得那么靜謐安寧。
就在這一刻,瓦依昂水庫南坡一塊南北寬超過500米、東西長約2000米、平均厚度約250米的巨大山體忽然發生滑坡!超過2.7億立方米的土石以100公里的時速,呼嘯著涌入水庫,隨即又沖上對面山坡,達到數百米的高度!整個時間不超過45秒!
滑坡時發出的巨大轟鳴聲,幾十公里以外都能聽見!
此時,水庫中僅有5000萬立方米蓄水,不到設計庫容的1/3。所有的水在一瞬間沸騰起來,橫向滑落的滑坡體在水庫的東、西兩個方向上產生了兩個高達250米的涌浪:東面的涌浪沿山谷沖向水庫上游,將上游10 公里以內的沿岸村莊、橋梁悉數摧毀;西面的涌浪高于大壩150米,翻過大壩沖向水庫下游,由于壩下游河道太狹窄,越壩洪水難以迅速衰減,致使涌浪前峰到達下游峽谷出口時仍然高達70米!
先前設置的防洪設施在巨大的洪水面前形同虛設。洪水涌入皮亞韋河,徹底沖毀了下游沿岸的1個市鎮和5個村莊。從滑坡開始到災難發生,整個過程不超過7分鐘,共有1900余人在這場災難中喪命、700余人受傷。
巨大的空氣沖擊波使電站地下廠房內的行車鋼梁發生扭曲剪斷,將廊道內的鋼門推出12米。正在廠房內值班和住宿的60名技術人員除1人幸存外,其余全部死亡;正在壩頂監視安全的設計者、工程師和工人們無一幸免。
揮之不去的陰霾
唯一在洪水中幸免于難的是瓦依昂大壩本身。壩體設計方案提供者意大利模型結構試驗研究所不愧是世界頂尖的結構力學研究所。
事后計算得知,滑坡引起的涌浪對壩體形成的動荷載相當于設計荷載的8倍。在這樣巨大的沖擊力下,按照“無拉應力設計”準則設計的大壩依然十分堅固。表面具有一定斜度的拱形壩體將巨大的水平沖擊力化解成向上的沖擊波,減輕了直接沖擊壩身的力量。洪水過后,瓦依昂大壩僅僅是右側壩肩輕微受損,主體安然無恙。幸存的大壩攔住了部分泥石流,避免了更大災難的發生。滑坡后第二天,瓦依昂山谷從痛苦中蘇醒過來,大壩依然莊嚴地聳立在那里,但壩前不再是一汪清水,而是足足高出壩頂150米的泥漿和滑坡體。
另外一個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的,是身處瓦依昂水庫北岸山坡的薩索鎮。由于地勢較高,滑坡體沖到小鎮腳下僅幾十米的地方停了下來,全鎮數千人因此逃過一劫。大難不死的薩索人事后足足舉行了一個月的彌撒,并在每年的10月9日舉行紀念活動,感謝萬能的上帝對小鎮的庇護,這一習俗沿襲至今。
災難發生后,意大利政府在對災民進行緊急救援的同時,還不得不面臨瓦依昂水庫的善后處理問題。由于壩前滑坡體對大壩產生的壓力很大,災后的首要大事就是抽空水庫中殘留的蓄水,并緊急開鑿另外的穿山水道,將奔流而來的上游來水引開,繞過瓦依昂水壩流入皮亞韋河。善后工程進行了一年多方結束。至于對災民的安置、賠償,災區重建等工作,則一直持續到80年代。然而,災難已經徹底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滑坡體掩埋了瓦依昂山谷幾乎所有良田,一些沖毀的村莊被完全廢棄,生活再也回不到過去;災難在人們心中造成的陰影也許永遠揮之不去。

亡羊補牢前車鑒
由于滑坡涉及的范圍太大,當地地質水文情況又極為復雜,時至今日瓦依昂災難的許多細節仍不清楚。
然而,毫無疑問,貪婪是導致災難的罪魁禍首。政客們明知在表決程序非法的情況下仍然通過決議,這背后是電力集團對利潤的渴求;建設方在明知地質查勘不充分、地質人員素質不高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利潤的誘惑同樣是一個重要原因。不貪婪,大壩的高度就不會是后來的264.6米,對邊坡的浸泡就不會有那么嚴重,至少滑坡的規模會大幅下降;即便大壩加高,發現滑坡苗頭及時停止蓄水,而不是急于通過驗收,也可以挽救上下游數千人的生命。
官僚主義則在這場災難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瓦依昂災難發生后兩天,國電公司宣稱“這次山體滑坡是不可預測的”。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1965年7月,國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事件的責任,只有意共向議會提交了對SADE、國電和能源部長的不信任案,但最終調查結果與國電的結論毫無二致。
從技術角度講,瓦依昂大壩的設計是成功的,建筑質量是過硬的,經受住了8倍于設計值的沖擊而安然無恙;然而,我們不能只從技術角度孤立地研究壩體結構本身,還要著重研究水利設施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影響,看水利設施能否與人和自然和諧相處。
瓦依昂水壩從建成到毀滅,沒發出一度電,卻造成了上下游慘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瓦依昂山谷失去了昔日的秀美,直到今天仍然到處可見大片裸露的山體,生態沒有完全恢復。瓦依昂水庫依然存在,只是保留了一個很小的供觀賞的人工湖,完全失去了蓄能發電的作用。水利設施不能為民造福,無法與自然和諧相處,再好的壩體又有何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瓦依昂大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之作。
值得欣慰的是,瓦依昂災難促進了立法程序的改變。應民眾的要求,阿爾卑斯山地的水電、流域開發項目,必須得到當地議會的通過才能實施。此外,災難還促使意大利政府加強了對工程咨詢顧問的監管,實行了“專家咨詢終生負責制”。亡羊補牢,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