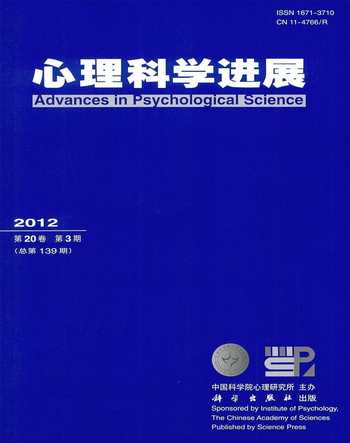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特點與理論分析
張春雨 韋嘉 羅禹 陳謝平 張進輔
摘要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研究有近30年的歷史。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更容易出現負面身體意象、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等。男同性戀追求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體。針對這些特點,研究者提出一些理論假設進行解釋,包括性客觀化理論、內化同性戀污名、性別角色假設、進化心理學假設和AIDS/HIV假設等。未來研究要進行整合的和多樣化的研究取向,方法上采用以網絡調查為主的定量研究和以現象學分析為主的定性研究。最后,國內研究要更注重文化特異性。
關鍵詞男同性戀:身體意象;性客觀化理論;內化同性戀污名;AIDS/HIV
分類號R395
1引言
身體意象(body image)是指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以及如何看待他人對自己身體的評價(corey,1996)。身體意象是一個多維度的結構。Rucker和Cash(1992)認為身體意象包括兩個成分:一是知覺成分(perceptualbody image),如對體型的估計;二是態度成分(attitudinal body image),如在情感、認知和行為三方面對自己身體的關注。而后,Cash(2002)進一步將態度成分區分為評估一情感維度(evaluative-affective)和認知一行為投入維度(cognitive—behavioral investment)。前者涉及到對身體外觀的自我評價,如身體意象不滿意(body imagedissatisfaction);后者涉及對身體外觀重要性的認知評估和行為表現,如與身體外觀相關的自我圖示(self-schemas)。身體意象存在消極的方面,稱為負面身體意象(negative body image)或身體意象失調(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指個體對身體的消極認知、消極情感體驗和相應的行為調控(陳紅,馮文峰,黃希庭,2008)。進食障礙(eating disorders)則可能是負面身體意象最嚴重的表現之一。
過去對身體意象的研究更多關注女性,而近年來男性的身體意象逐漸成為研究熱點(Martins,Tiggemann,&Kirkbride,2007)。其中,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備受關注,一方面因為男同性戀具有特殊的社會文化身份,他們在身體意象上表現出獨特的特點。另一方面由于男同性戀人群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既富有爭議又不可忽視的群體,對其身體意象的研究不僅具有健康意義,更具社會文化意義。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更容易出現負面身體意象、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等(Morrison et al.,2004;Kaminski,Chapman,Haynes,&Own,2005;Tiggemann,Martins,&Kirkbride,2007)。同時,男同性戀表現出對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體的追求(Yelland&Tiggemann,2003)。針對這些結果,研究者們提出了一些理論解釋,包括性客觀化理論(sexualobjectification theory)、內化同性戀污名(internalizedhomonegativity)、性別角色假設、進化心理學假設和AIDS/HIV假設等。這些理論為理解男同性戀身體意象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2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特點
這里體現了男同性戀與其它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人群在身體意象上的差別,需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男同性戀在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等負面身體意象的水平上與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異;二是男同性戀所追求的理想身體(idealbody)與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異。
2.1男同性戀的負面身體意象
研究者們在身體不滿意、進食障礙等方面探討男同性戀與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異,在身體不滿意方面,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表現出了更高的身體不滿意(如Kaminski et al.,2005;Tiggemann etal.,2007;Boisvert&Harrell,2009;Carper,Negy,&Tantleff-Dunn,2010,),也表現出了對體重的過度關注(Peplau et al.,2009)。Levesque和Vichesky(2006)以64名男同性戀為被試,發現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更不滿意自己的整體外觀或其他身體部分(如上半身等),更希望自己不要超重。Morrison等(2004)進行了一項元分析研究,這項研究檢驗了20項相關研究數據,包括984名男同性戀被試。研究發現,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更易出現身體不滿意,但是兩者差異的效應值相對較小(d=0.29)。在六個以進食障礙量表(Eafing DisordersInventory)的身體不滿意分量表為測量工具的研究中,其效應值處于中等水平(d=0.40)。Boroughs,Krawczyk和Thompson(2010)則發現,少數性取向男性群體(sexual minority men)(主要包括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等)的身體變形障礙(bodydysmorphic disorder)水平要高于男異性戀。也有研究關注與男性進食障礙相關的因素,發現在控制整體心理健康這一因素后,男同性戀性取向同樣可以解釋進食障礙的一部分變異,說明男同性戀的一些獨特經歷可能與進食障礙存在聯系(Russll & Keel,2002)。這些研究數據都表明,男同性戀可能具有更高的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等,他們具有更高的負面身體意象。
2.2男同性戀的理想身體
既然很多研究支持男同性戀具有更高的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等負面身體意象,接下來的問題是男同性戀渴望擁有怎樣的理想身體外觀。研究發現男同性戀的理想身體主要包括兩個要點:瘦(thinness)和肌肉(muscularity)。Yelland和Tiggemann(2003)的研究包括了三類人群:男同性戀,男異性戀和女異性戀,結果發現,男同性戀在追求瘦(drive for thinness)和追求肌肉(drive for muscularity)上都顯著高于男異性戀,而在追求瘦上。男同性戀與女異性戀則沒有顯著差異,這說明男同性戀既想要瘦,也想要肌肉。Kane(2009)認為,早期研究主要采用臨床被試,在病理性和女子氣上都更高,所以得出的結論是男同性戀更追求瘦而顯年輕的理想身體。而近來研究的被試人群擴展到了社區和網絡,發現男同性戀不僅追求瘦,也追求有肌肉的身體。很多研究支持這一觀點,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表現出更高的追求纖瘦、追求肌肉和害怕肥胖等傾向(Kaminski et al.,2005;Boisvert&Harrell,2009;Carper et al.,2010)。但也有研究發現,男同性戀和男異性戀都渴望自己的身體可以更瘦、更有肌肉,只是男同性戀的身體不滿意更高(Tiggemann et al.,2007)。
結合身體不滿意和進食障礙來看,有研究發現,男同性戀最不滿意的身體部分是體毛(bodyhair)和肌肉,而對于自己的身體吸引力,男同性戀則認為體重和肌肉對自身的身體吸引力最重要(Martins,Tiggemann,&Churchett,2008)。Blashill(2010)的研究同時考察體重不滿意(body fatdissatisfaction)、肌肉不滿意(muscularity dissatis—faction)和身高不滿意(height dissatisfaction)在男同性戀身上的消極作用,結果體重不滿意對飲食節制(dictary restraint)和抑郁的預測作用要大于肌肉不滿意,而身高不滿意則與飲食節制和抑郁不存在顯著聯系。Smith,Hawkeswood,BodeH和Joiner(2011)的研究也發現,不管是男同性戀還是男異性戀,體重不滿意比肌肉不滿意對進食障礙的預測作用更大。以上兩個研究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男同性戀理想身體的第一層目標是不要肥胖,而擁有肌肉則是其第二層目標。
3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理論解釋
研究者們在探討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特點的同時,也對產生這些特點的原因做出了理論假設,并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對這些假設加以驗證。
3.1性客觀化理論
性客觀化理論最初由Fredfickson和Roberts(1997)提出,他們對性客觀化的定義是:個體體驗到自己被看作為一個身體或身體各部分的組合,自己的價值被以對他人的用途來衡量。該理論認為,生活在性客觀化文化中的個體會采取其他觀察者的視角來評價自己和自己的身體,并努力去達到他們的文化所強調的性理想和身體理想。性客觀化理論雖然起初被用于描述和解釋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性客觀化現象,但該理論同樣適用于其他性客觀化群體,男同性戀就是其中之一。男同性戀的亞文化使他們的身體被客觀化。男同性戀亞文化是一個關注身體的亞文化,這一文化給身體外觀、纖瘦和肌肉賦予了很高的價值(Wood,2004)。它通過媒介和其它相關的信息,向男同性戀灌輸其強調的身體外觀和身體吸引力標準,激發男同性戀內化這些信息,形成自我客觀化(self-objectification)。自我客觀化又激發男同性戀的身體羞恥(body shame,),增加出現失調性進食態度和進食行為的概率(Martins et al.,2007)。同時,男同性戀文化建構了一個身體吸引力的理想結構,而這一理想結構是大多數男同性戀所無法達到的,對身體外觀的看重也強化了個體對實際身體意象和理想身體意象差距的感知,導致負面身體意象和身體不滿意,進而誘發一系列的負面身體實踐,如過度鍛煉和進食障礙等(Duncan,2007;Gil,2007)。Drummond(2005)的研究對14名18~25歲的男同性戀進行深入訪談,發現年輕的男同性戀一方面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和文化阻礙,可能使他們在身體和情緒上受到傷害。另一方面,他們的這種狀況又驅使其更關注自己的身體,更看重他人對他們的感知和看法。Legenbauer等(2009)的研究也發現,與其它性取向人群相比,男同性戀具有最高水平的社會文化理想內化水平(internalization of socio-cultural ideals),這使得男同性戀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吸引力。男同性戀所處的審美驅動的文化(aesthetic-driven culture)促使他們更可能去關注身體,為性客觀化提供了途徑。
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中存在兩個載體:一是媒介(media)。當今男性吸引力的標準是以肌肉建構為基礎的,例如廣告等給男性的身體不安全感提供了途徑,它們傳播了這樣一個信息:男性需要不斷改善和提高自己的身體,因為他們的身體外觀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他們的同一性。Christopher(2009)的研究發現,媒介的影響對男性身體意象存在預測作用,和男異性戀相比,男同性戀會更大程度地內化媒介信息。McArdle和Hill(2009)的研究也發現,與男異性戀相比,在男同性戀身上,媒介的影響與身體不滿意和自尊的聯系更緊密。Carper,Negy和Tanfleff-Dunn(2010)的研究同樣發現,男同性戀更易受到媒介的影響,這一影響在性取向和身體意象關注之間起顯著的中介作用。這些研究都表明媒介在傳遞男同性戀身體信息上的作用。
另一個載體是男同性戀群體或社區(community)。男同性戀文化中,群體和社區為男同性戀傳播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理想身體外觀的標準。Hospers和Jansen(2005)的研究認為,男同性戀社區給予男同性戀的理想身體壓力要更大于其它社區。同時,跟男異性戀相比,男同性戀更大受到了同伴對身體吸引力的影響。男同性戀更易受他人所說和所想的影響而努力提高自身的身體外觀(Yelland&Tiggemann,2003)。Meany。Walen和Davis-Gage(2009)對男同性戀進行訪談,發現男同性戀對身體的看法受到了社區的影響,被試描述了成為男同性戀社區成員的相似期望:瘦、有肌肉和有吸引力。
研究者們通過實驗或調查來進一步驗證性客觀化理論在男同性戀身上的適用性。Martins,Tiggemann和Kirkbride(2007)進行了兩個研究,一個研究采取調查方式,測量被試的特質性自我客觀化(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發現男同性戀比男異性戀表現出了更高的特質性自我客觀化、身體羞恥和身體不滿意,同時,身體羞恥在特質性自我客觀化與身體不滿意之間起中介作用。另一個研究則采取實驗的方式,通過控制情景誘發被試的狀態性自我客觀化(state self-obiectification)。實驗包括68名男異性戀和57名男同性戀,被試被隨機安排要求在鏡子面前穿女式游泳衣(swimsuit)或毛衣(sweater),穿游泳衣而不是男士泳褲會誘發男性的自我客觀化,檢驗發現,在穿游泳衣的被試身上的自我客觀化水平確實高于穿毛衣條件下的被試。男異性戀在兩種條件下的身體羞恥水平和吃零食數量并沒有顯著差異,相反,男同性戀在穿游泳衣條件下則報告了更高的身體羞恥,吃了更少的零食。這說明,實驗控制下的狀態性自我客觀化誘發了更高的身體羞恥、身體不滿意和飲食節制。Kozak,Frankenhauser和Roberts(2009)的研究發現,男同性戀的自我客觀化程度高于男異性戀,男同性戀對他人的客觀化程度也高于男異性戀,這說明,在評價他們自己或其他男性身體時,男同性戀更傾向于關注表面和外部的表現。而男異性戀在做這些評價時則更關注身體的功能,例如身體健康、身體強度等。Wiseman和Moradi(2010)的研究以少數性取向男性群體為
被試,發現內化吸引力的文化標準(intemalization of cultural standards of attractiveness)在性客觀化體驗與身體監管(body surveillance)之間起中介作用;身體監管在內化吸引力的文化標準與身體羞恥之間起中介作用;身體羞恥在身體監管與進食障礙之間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說,性客觀化受到了社會文化標準的影響,影響男同性戀的身體監管,身體監管可能使男同性戀產生身體羞恥,進而導致進食障礙,這是一個一系列的過程。總之,性客觀化理論得到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認可,但為進一步明確其作用機制,后續的深入研究還需要繼續進行。
3.2內化同性戀污名
內化同性戀污名是指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者內化了主流社會指向他們的消極態度和信念,從而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產生消極態度和信念(Jackson,2008)。Reilly和Rudd(2006)的研究發現,對同性戀身份的消極態度(內化同性戀污名的一個指標)能夠顯著預測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和自尊。Strong(2005)對40至60歲的中年以上男同性戀進行了深入訪談,分析發現,被試有意識地經歷了內化同性戀污名,在他們人生的某些階段,由于自己的男同性戀身份而產生消極情緒。并且,對大多數有此經歷的人來說,內化同性戀污名對其身體意象產生了消極的影響。Kimmel和Mahalik(2005)結合少數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model)來研究與污名相關的壓力對男同性戀的影響。該模型認為,男同性戀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成員一樣,會經受與污名化相關的慢性和彌散性壓力,其中包括內化同性戀污名、污名期望(expectations of stigma)和歧視事件等,這些都可能是壓力的來源。污名期望是指男同性戀對因其性取向而受到社會拒絕和歧視的預測。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男同性戀渴望擁有強有力的身體,以防御和反抗他人的歧視,另一方面這些因素也可能會因自身的內化羞恥而發展為消極的身體意象。他們的研究對357名男同性戀進行了網絡調查,發現少數壓力模型與身體意象不滿意存在顯著聯系,印證了少數壓力模型的假設。不管是內化同性戀污名,還是少數壓力模型都強調污名和歧視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該假設的影響途徑還需要今后研究加以驗證。
3.3性別角色理論
該理論一方面從男同性戀和男異性戀在男子氣(masculinicy)和女子氣(femininity)上的差異人手,認為具有高女子氣的男異性戀更可能關注自己的身體意象,出現進食障礙。該理論認為,男同性戀可能也具有高水平的女子氣,這可能導致了他們也更關注自己的身體,更易出現負面身體意象(Jackson,2008)。另一方面,研究者認為男同性戀存在高度的性別角色沖突(gender role conflict),使他們與傳統男性規范產生沖突,在傳統男性規范的壓力下,男同性戀不能像男異性戀那樣處理沖突,這可能使男同性戀體驗到提高身體吸引力的壓力,以讓自己被社會接受,或被其他男同性戀渴求(Blashill&Vander Wal,2009;Sanchez,Greenberg,&Vilain,2009)。 Strong,Singh和Randall(2000)的研究發現,高女子氣低男子氣的男同性戀比高男子氣,中低女子氣的男同性戀報告了更高的身體不滿意。Jackson(2008)的研究發現,在男異性戀身上,性別角色沖突與進食障礙不存在顯著聯系,但在男同性戀身上,兩者則存在顯著聯系。Blashill和Vander Wal(2009)的研究也發現了性別角色沖突對進食障礙的預測作用,同時,社會敏感性(social sensitivity)在兩者的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這可以理解為,性別角色沖突導致了個體對他人情緒或行為的高度敏感性個體更關注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致使個體產生進食障礙的危險性增加。以上的研究支持了性別角色理論的假設,但也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這一假設,如Russell和Keel(2002)的研究認為,男同性戀的女子氣并不比男異性戀高,這對性別角色理論的前提提出了質疑。而Hospers和Jansen(2005)也發現,男同性戀的身體不滿意度和女子氣之間不存在相關。Blashill(2011)進行了一項元分析研究,發現,男同性戀的女子氣與肌肉不滿意之間沒有聯系,相反,男異性戀的女子氣與肌肉不滿意存在顯著負相關。鑒于這些不一致的結論,這一假設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3.4進化心理學假設
有研究者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提出性別內競爭假設(intrasexuaI competition)(Lj,Smith,Griskevicius,Cason,&Bryan,2010),認為性別內的地位競爭的目的是吸引伴侶以達到適應環境,性別內的地位競爭導致了對理想伴侶的關注,對女異性戀和男同性戀來說,要得到這樣的關注就要提高自身的身體吸引力,如變得更年輕、讓身體外觀更具吸引力。Li等(2010)的研究對四類被試(男女同性戀和男女異性戀)進行實驗,考察在競爭和不競爭兩種條件下,被試在身體意象和進食態度上的差異。實驗中的競爭和不競爭兩種條件都不涉及身體吸引力方面的差異,而主要是從興趣、學業和就業等方面的高低地位差異來考察。結果發現,在男同性戀被試身上,性別內競爭提示詞導致了更大的身體意象不滿意和更嚴格限制的進食態度,這一效應同樣體現在女異性戀身上,但這一效應在男異性戀和女同性戀身上并沒有體現。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性別內競爭假設。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擇偶或選擇伴侶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男同性戀之所以報告了更多的進食和身體意象關注。可能是因為男同性戀和女異性戀一樣,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吸引男性(siever,1994)。而男性一般更看重伴侶的審美價值(aesthetic value),即更關注伴侶的外貌身體特征。相反,男異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共同目標是吸引女性(一般更看重穩定和權力),所以他們則追求高社會地位和穩定的高收入(Lacey,Reifman,Scott,Harris,&Fitzpatrick,2004)。Lippa(2007)的研究也支持這一結論,在選擇伴侶的特質時,男性更強調身體吸引力,而女性更強調誠實、幽默、熱心、可靠等特質。但性取向的不同也會導致一些差別,同性戀更少強調伴侶在家庭和婚姻中的特質,男同性戀看重伴侶年齡、手、牙齒、可靠、誠實、金錢等。可以看出,男同性戀在選擇伴侶時既強調身體吸引力,也強調女性在選擇伴侶時的一些特質。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Li等(2010)的假設,男同性戀的伴侶選擇是更看重對方的身體,男同性戀也努力提高自身的身體以吸引伴侶。Meany-Walen和Davis-Gage(2009)發
現,男同性戀被試表達了對友誼(companionship)和接納的關心以及害怕孤獨的傾向。他們認為如果擁有了理想的身體外觀,自己就有更大的可能獲得友誼和幸福。總之,男同性戀意在吸引男性伴侶,而男性在擇偶時注重身體外觀。這激發了男同性戀對身體的關注,并可能導致負面身體意象。
3.5ADIS/HIV假設
1978年,美國出現首例男同性戀感染AIDS,而隨后則引起了80年代關于男同性戀和AIDS關系的大爭論,AIDS甚至一度被認為是男同性戀的癌癥。AIDS與男同性戀的這種聯系造成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很多男同性戀具有恐懼AIDS的癥狀,由于AIDS存在艾滋消瘦癥候群(AIDS wasting syndrome),早期HIV感染會出現一系列身體上的癥狀,身體消瘦是其典型表現之一,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癥狀的關注使男同性戀更加關注自己的身體。另一方面。在男同性戀的人群和社區中,不管是不是真的生病,過于瘦弱都被認為是生病的象征。相反,有肌肉的身體就被看作是健康而有吸引力的標志。所以,兩方面的影響使得男同性戀更關注自己的身體,追求有肌肉的理想身體(Neal,2005;Strong,2005;Levesque&Vichesky,2006;Tiggemann et al.,2007)。Drummond(2005)的研究同樣支持這種假設,認為過于瘦弱被認為是不健康的表現,特別是可能被認為患有AIDS。所以,很多男同性戀為了保持體型和肌肉會去進行健身。但是Kane(2009,2010)則認為這一假設還有待考證,因為AIDS與男同性戀身體理想的聯系正好與上世紀80年代對AIDS的大討論相映,但男同性戀對身體外觀等的關注在80年代前就存在。Kane認為這樣的結果缺乏歷史一致性。總之,雖然存在部分質疑,但不可否認,當代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可能受到了ADIS/HIV因素的影響,該假設給理解男同性戀身體意象提供了一部分參考,缺乏歷史一致性的問題可能只是說明,還存在其它的相關因素會對其身體意象產生影響。
4小結與展望
男同性戀具有特殊的社會文化身份,心理學界的研究一直關注這一特殊群體,因此,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被打上了深刻的社會文化烙印。通過以上的回顧,可以發現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特點達成了初步共識之后,研究者們在努力通過各種理論假設對其特點做出解釋。與男異性戀相比,男同性戀具有更高的身體不滿意、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外觀以及更嚴謹的進食態度等;他們患進食障礙的可能性也更大;并追求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體。男同性戀在身體意象上呈現出這些特點受到了諸多因素的影響。本文總結了幾種理論假設,每種理論都有其合理性,并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這些理論假設事實上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整合的趨勢也漸漸顯現出來。未來關于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研究仍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4.1整合的和多樣性的研究取向
研究者們都試圖將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放在社會文化的范疇內進行討論,不管是哪種理論,都在強調社會和文化的作用,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每種理論都可能存在著聯系。性客觀化理論是現在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進行解釋的最被看重的理論之一,但在其理論解釋中,同樣涉及到社會文化所給予男同性戀的理想身體標準的影響,也同樣涉及內化同性戀污名的作用。Wiseman和Moradi(2010)的研究就發現,性客觀化理論所強調的身體羞恥同樣受到了內化同性戀污名的影響。Andorka(2007)的研究也試圖探討性客觀化理論和內化同性戀污名之間的聯系,雖然他的研究并沒有發現兩者的顯著聯系。但這種嘗試是有意義的。此外,AIDS/HIV假設也要得益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同性戀權益運動和80年代的AIDS討論,這些社會運動恰恰是社會文化的推動力量。所以,整合的趨勢將是未來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理論解釋的一個方向。
另一方面,每個假設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驗證和補充,比如性別角色假設的部分假設還存在爭議,如是否男同性戀人群的女子氣水平更高,女子氣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預測作用有多大。另外,如進化心理學取向的研究還不多,這個較新的角度在解釋男同性戀身體意象上還有很多可探討的議題,從擇偶繁殖(雖然男同性戀不能在伴侶之間繁殖,但這也恰恰是可以討論的地方)和競爭生存等角度,男同性戀特殊身份的進化心理學意義很大。因此,現在關于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的理論解釋研究正處于百花爭鳴的階段,體現了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性。
4.2小群體網絡調查和現象學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應用最多的方法是網絡調查和現象學的深入訪談,而且這一領域的研究被試量都不大,屬于小群體研究(Kane,2010)。一方面,這可能要歸因于男同性戀群體的特殊性使其保持著隱蔽性,很多男同性戀做不到對外暴露(劉俊,張進輔,2009),所以研究者往往不能招募到大量的男同性戀被試來參與調查或實驗。多數研究都是通過網絡調查的方式而實現的,因為網絡是男同性戀的一個重要載體,網絡調查不需要他們對外暴露身份。所以,這種方式在操作性上都比較可取。但網絡招募被試可能會存在一些偏差,如網絡招募的被試相對低齡化,可能會忽視較長年齡段的同性戀被試。所以,未來研究在招募被試時一定要考慮取樣偏差的問題,在結果推論上也要在年齡等變量上做到嚴謹。另一方面,同性戀的身份具有濃厚的社會文化色彩,加之同性戀人群的隱蔽性,現象學分析的方法得以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得以應用。通過深入訪談和分析的方式,研究者可以從個案中獲得對他人經驗的深度理解,解釋男同性戀身體意象背后的社會文化意義,并提出假設或理論。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完全摒棄實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在建立理論假設后,可行的實證研究可以為理論假設提供更有利的證據。所以,現象學分析的方法在研究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上具有很大的理論和應用可行性。但現象學的深入訪談和分析同樣需要遵循嚴格的標準,同樣要做到嚴謹,未來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網絡調查更多屬于定量研究,而現象學訪談和分析更多是定性研究,兩種研究取向都有其利弊,得到的結果也各有補充,在對男同性戀身體意象進行研究時,分別采用兩種取向或兩種取向的結合都是可取的。
4.3文化特異性的國內研究方向
同性戀行為在中國自古有之,但同性戀的身份稱呼卻是近代由西方引入的(劉俊,張進輔,2009)。所以,當代中國的男同性戀受到了中西文化交互的影響,這也就預示了在身體意象上,中國男同性戀的特點及理論解釋都可能有異于西方的研究結論。首先,中國沒有像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影響力巨大的社會文化運動發生,所以,中國民眾對男同性戀多是處于忽視狀態,這為男同性戀實現自我認同以及進一步的身體認同都造成了一定阻力,因此,內化同性戀污名對身體意象的作用可能會更大。其次,中國并不像西方那樣強調“性”,個人在對待“性”的態度上也趨于保守,這對與“性”直接相關的身體態度也會產生影響,所以,性客觀化理論對中國男同性戀的解釋所占的比重可能就沒有那么大。第三,西方文化所樹立的身體吸引力標準可能并不符合中國男同性戀,或在程度上中國男同性戀與男異性戀的差異并不顯著。Poon和Ho(2008)的研究發現,生活在白人社會的亞洲男同性戀被主導的西方文化賦予消極的刻板印象,視他們為被動角色,渴望白人成為自己的伴侶,但這些亞洲男同性戀并沒有簡單地接受主導文化所強加給他們的消極刻板印象,而是積極地抵抗這種影響,并重塑自己的身體。可見,即使是生活在白人社會,亞洲男同性戀也可能并非完全被動去接受西方同性戀文化的影響。此外,中國的媒介并沒有像西方那樣明顯傳播理想身體的標準,而且中國沒有外國的同性戀社區文化,但中國同樣存在同性戀網絡社區。西方的吸引力標準也可能通過網絡渠道傳遞給中國的男同性戀。這些因素都可能使西方研究結論在中國男同性戀人群中的推論性受到影響。
在研究方法上,鑒于前面所進行的闡述,國內研究仍將以訪談法和網絡調查法為主,這兩種方法對仍是空白的中國男同性戀身體意象研究很有益。總之,中國男同性戀的身體意象特點可能存在自己的文化特異性,該領域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