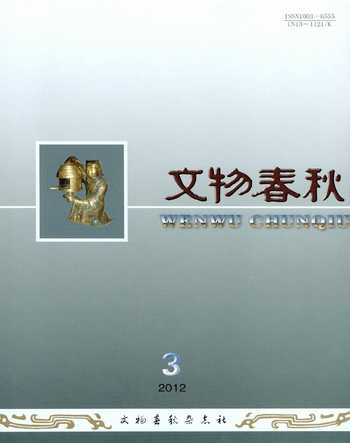二祖廟《菩提達摩碑》碑文復原及考釋
任乃宏
【關鍵詞】二祖廟;菩提達摩碑;禪宗;梁武帝
【摘要】署名梁武帝撰的菩提達摩碑文是中國佛教禪宗的重要文獻,本文以對位于河北成安縣元符寺內的菩提達摩碑的實地考察為基礎,結合傳世的佛教文獻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二祖廟菩提達摩碑的碑文進行了整理復原,考定此碑的重建時間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并就碑文的真偽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引言
署名梁武帝撰的菩提達摩碑文是中國佛教禪宗的重要文獻,對其展開的研究事關早期禪宗史和早期禪宗思想史,一向為佛教研究者所重視。近年來,日本學者小島岱山和國內學者紀華傳等均就此展開研究并取得成果。小島岱山的文章《菩提達摩石碑碑文并參考資料》[1],主要貢獻在于將分處于熊耳山、少林寺、二祖廟的三塊菩提達摩碑的碑文及有關資料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遺憾在于對二祖廟達摩碑文的識讀仍存個別錯誤。紀華傳的《菩提達摩碑文考釋》[2]一文,主要貢獻在于確定了碑文出現的下限(公元732年之前),肯定了碑文的文本價值,同時指出了熊耳山的菩提達摩碑不可能是原石原碑;遺憾在于其思路仍不能跳出胡適和陳垣所下的結論,執著地認為碑文乃偽作,故其對碑文產生時間和作者的推定也只能是“姑妄言之”。
本文以對二祖廟菩提達摩碑的實地考察為基礎,結合傳世的佛教文獻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等,對二祖廟菩提達摩碑的碑文及碑陰文進行了復原,考定二祖廟達摩碑的重建時間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五月,并就碑文的真偽等提出自己的意見。
二、二祖元符寺及達摩大師碑簡況
二祖元符寺是中國禪宗二祖慧可大師舍利安奉處,距今已有近1400年的歷史。二祖村,古名婁姑村,即佛教各典籍所載之蘆村,后以祖師靈塔所在,遂改名為二祖村。二祖村歷史上隸屬于彰德府磁州,1945年以后劃歸成安縣。河北省佛教協會秘書長高士濤居士曾專門撰文介紹過元符寺的概況:“隋開皇十三年(593年)三月十六日,禪宗二祖慧可大師以一百零七歲高齡圓寂后即葬此處。唐貞觀十六年(642年),欽命尉遲恭監工建寺。開元二十年(732年)于寺內建塔,安奉慧可大師舍利。天復二年(902年),欽賜寺名為‘廣慈禪院。宋元符三年(1100年)易名‘元符寺。明永樂及清康熙年間屢有重修。……元符寺原有山門殿、二祖舍利塔、韋陀殿、大雄寶殿、藏經樓、禪堂、鐘樓、鼓樓、背座殿等建筑。民國年間,元符寺已逐漸破敗。1938年二祖舍利塔遭土匪焚燒,塔剎跌落。1969年,塔被徹底拆除,既而發現四壁有精彩繪畫的地宮,而慧可大師舍利亦被同時發現。其舍利保存于地宮內舍利石函中。有鐵鏈將舍利函于地宮中懸空吊起,石函中又有雕飾精美的銀棺,銀棺內安放著慧可大師舍利。石函前有長明燈兩盞,其周圍又有十八尊鑄銅羅漢像。由于當時文物部門參與發掘,故二祖慧可大師舍利發現后即被文物部門收藏。”[3]
菩提達摩碑即位于今河北省邯鄲市成安縣東二祖村北的元符寺內,1935年被重新發現。該碑原淤于地面以下,碑首不知去向,碑體上部風化較重,且有局部剝落,部分字跡已無法辨認。碑殘高2.05米,寬1.02米,厚0.26米,碑陽、碑陰和左側三面刻字。碑陽陰刻楷書(間有行書)正文26行,滿行42字,落款2行,字體剛勁秀逸(圖一)。碑陰陰刻楷書22行,滿行33字。碑左側陰刻楷書6行,現殘存42字(圖二)。
三、碑陰文復原及考釋
《全唐文》卷998收錄有李朝正于唐元和十三年(時間的具體推定見下文)五月“重建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時口述的碑陰文。結合實物,筆者將碑陰文點校復原如下(括號內為復原內容,其余為現場識讀或《全唐文》所載):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重建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故敘碑陰文。
昭義軍監軍使、登仕郎、守內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朝正述。
此碑文布傳于天下久矣,未詳其本立處。頃日得之,竊玩其文,乃知梁武帝深達玄旨。若非留心此宗,則罕測其涯際。或者云:“梁武帝崩后,菩提達摩猶行化人間。”蓋或者自惑耳。考諸史籍,則梁大同二年歲在乙卯,至太清二年歲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廢于侯景。自大同單閼之歲,至我唐元和閹茂之歲,凡三百四十三年矣!朝正嘗愿于熊耳吳坂再立此碑,屬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今乃就二祖可大師塔前建之,用表真宗之所由也。
菩提達摩自西域至中國,為禪宗第一祖。內傳心印以為宗,謂意出文字外;外傳袈裟以為信,信表師資。其袈裟授可大師,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能。達摩遺言云:“我法至第六代后,傳我法者命如懸絲。”故能受付囑后猶隱遁人間,事在本傳。祖師知當來學徒,必注意謂法在衣上,不知法本無為,得之者永超三界。了斯玄旨,是達真宗。所以誡絕傳衣,令學徒得意者廣通流布,化及無窮,拯溺俗于沉沙,擢迷途于苦海者矣。
曹溪能弟子南岳惠讓,讓弟子龔公山洪州道一,洪州弟子信州鵝湖山大義。大義貞元中內道場供奉大德,每敷演妙理,萬法一如,得無所得,證無所證,開合不二,是非雙泯。夫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可謂真證真得涅宗源乎?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乃度中貴王士則,命舍官,賜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童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親承教旨,妙達真宗。
自祖師歷六代后,名流大德、學徒得意者布行天下,敷演妙理,不可殫紀。朝正但據所稟本教來處敘之,將來幸辯由戶不謬矣。今恐年代久遠,故重刊石紀之。
(將仕)郎、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祁再光、第五義和
在復原碑陰文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了以下問題:
1、李朝正重建達摩碑的時間應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而非小島岱山發布的唐元和十二年。證據來自碑陰文本身。在“考諸史籍,則梁大同二年歲在乙卯,至太清二年歲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廢于侯景,自大同單閼之歲,至我唐元和閹茂之歲,凡三百四十三年矣”這一段中,存在如下問題:一是“梁大同二年”歲在丙辰,而非“乙卯”,其與“太清二年”相去13年,亦非“一十四年”;二是“自大同單閼之歲,至我唐元和閹茂之歲”,相去只有283年,而非“三百四十三年”,誤差正好是一個甲子——60年。筆者以為,上述問題的存在,恰恰證明二祖廟達摩碑是真正的唐碑。理由有三:一是古人計算年代沒有今天方便,“掐指算來”,難免“前趕后錯”;二是年代久遠時,往往用相距幾個甲子(一個甲子60年)來推算,多算一個甲子固然令人掃興,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如果此碑為后人處心積慮的偽造,偽造者難道會低能到允許出現這樣明顯的錯誤?總而言之,李朝正的這篇碑陰文應屬急就章,而其身邊幫忙計數的人恰好又有些糊涂,因此造就了這一公案。此外,“單閼之歲”為兔年,“閹茂之歲”為狗年,查《中國歷史紀年表》,唐元和元年恰逢狗年(丙戌),下一個狗年只能是元和十三年(戊戌)。
2、“朝正嘗愿于熊耳吳坂再立此碑,屬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一語,旁證了唐代熊耳山空相寺并不存在達摩碑。考慮到溫玉成在《傳為達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記》一文中也認為“《菩提達摩大師頌并序》,約作于明萬歷間。該碑顯系利用宋金舊碑重刊”[4],所以日本學者鐮田茂雄認為熊耳山空相寺的達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的結論應該是無法成立的。
3、二祖廟的達摩碑重建于唐代,少林寺的達摩碑重建于元代,空相寺的達摩碑重建于明代。在現存的三塊達摩碑中,二祖廟達摩碑的年代最早,以常理論,其內容應該與原碑最為接近。
4、唐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秩從九品下,文散官階為將仕郎。以常識推測,祁再光與第五義和應為李朝正口述碑陰文的記錄者和書寫者。
5、據菩提達摩碑文落款,李朝正官銜中有“興元元從(功臣)”一項,說明其曾于興元元年(784年)跟隨唐德宗出奔梁州,與朝中宦官有很深的淵源,故其敘述的“大義貞元(785—805年)中內道場供奉大德”一事必有根據,絕非空穴來風。
6、碑陰文所述之“慧能—惠讓(懷讓)—道一(馬祖)—大義”的傳承法系,說明李朝正信奉的是南宗(洪州宗)。因此,紀華傳認為達摩碑為北宗門人所偽造的推論可不攻自破。
四、達摩碑文復原及考釋
以現場識讀為基礎,參照小島岱山公布的資料,筆者將二祖廟達摩碑文點校復原如下(括號內為復原內容,其余為現場識讀):
(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并序
梁武帝撰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毫色,天莫見,人不識,則我大師得之矣。大師諱達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詳其姓氏。大師以精靈為骨,陰陽為器,性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岳之秀,抱凌云之氣,類鄔身子之聰辯,若(曇磨弗利之)博聞。總三藏于心河,蘊五乘于口海。為玉久灰,金言未普,誓傳法化。天竺東來,杖錫于秦,說無(說法),(如)室之煬炬,若明月之開云,聲震夷夏,道邁今古。群后聞名,欽若昊天。于是躍鱗惠海,振羽禪河,法梁(橫天,佛)日高照。示其育物也,注無雨雨,灑潤身田;說無法法,證開明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以(泯相,身)離眾生。實哉空哉,凡哉圣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之則無內。積之于無,成之于有。其教示乎,于時奔如云,學如雨,果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禪師矣。大師舒容而嘆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長流法(海,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滌煩籠而)無盡。豈唯積善不,皇天何辜!月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惠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圖不,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貌如常。其時則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悲鳴,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終于洛州禹門山,未測其報齡(也。遂塋葬于熊耳吳坂矣。于是門人悲)感,號(動天地),泣流遍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喪妣焉。生途眼滅,傷如之何。(嗟乎!法身匪一,示現無方,骸葬)茲墳,形游西域。亦為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圣智者安得而知之乎?
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勤,旰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于后。未獲現生之得),冀有(當來之)因。不以刻石銘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大教之不聞,(式建鴻碑,以示來見。乃作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形同大地體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匪磨匪瑩恒凈明,(披云卷霧)心且(徹。芬)陀利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哉離生滅,大之小之眾緣絕。剎那而登妙覺心,躍鱗惠海超先哲。理應法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暫竭。驪龍珠內落心燈,白毫惠刃當鋒缺。生徒忽焉惠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住焉去焉皆歸寂,寂內何曾存哽咽。付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有能志誠心不疑,劫火燃燈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悟迷途茲是謁。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昭義軍監軍使,興元元從,登仕郎、守內侍省奚官局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朝正重建
(中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澤潞磁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辛秘
在復原碑文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了以下三個問題:
1、據《廣平府志?金石略上》達摩大師碑:“末行有中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等字”[5],可確定碑文的書丹者為時任昭義軍節度使的辛秘,進一步確證該碑的建立時間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
據《舊唐書?辛秘傳》:“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元和初,拜湖州刺史。……九年,征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為河南尹。蒞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郗士美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糇糧器械稱是。……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6]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以河南尹辛秘為潞府長史、昭義軍節度使,代郗士美。”元和十三年“秋七月,己酉,詔諸道節度使先帶度支營田使名者,并罷之。”[7]
顯然,由于辛秘元和十二年八月始任昭義軍節度使,該碑不可能立于元和十二年五月;又由于元和十三年七月以后,節度使不再兼任“度支營田使”,而辛秘落款中恰恰有此兼職,證明這一落款是確定無疑的。因此,二祖廟達摩碑屬于唐碑的真實性是不存在問題的。
2、與少林寺、空相寺的達摩碑文相校,在形容達摩大師的法力廣大時,二祖廟達摩碑文與之最明顯的區別有兩處:一是二祖廟碑為“聲震夷夏”,其余二碑皆為“聲震華夏”;二是二祖廟碑為“群后聞名,欽若昊天”,其余二碑皆為“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很明顯,使用“聲震夷夏”、“群后聞名”之語,才符合梁武帝的帝王身份。須知,達摩為“番僧”,自然是“聲震夷夏”;“群后”者,各路諸侯也。由此可知,探究達摩碑文,二祖廟碑要比其它兩碑可靠得多。
3、由于少林寺和空相寺的達摩碑靠不住,而重建二祖廟達摩碑的李朝正又說“未詳其本立處”,真正的原碑原石是否曾經存在,恐怕也很成問題。
五、關于達摩碑文是否為梁武帝所撰的討論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后》二文中,以唐道宣《續高僧傳》和凈覺的《楞伽師資記》未記達摩見梁武帝事為主要依據,斷言一切有關達摩與梁武帝晤談的記載,統統都是“謬說”和“偽造”,實為此一公案的始作俑者。由于胡適的弟子眾多、影響很大,在很長的時期內,梁武帝從未見過菩提達摩幾乎成了定論。其實,正如胡適的得意弟子顧頡剛懷疑“大禹是一條蟲”一樣,胡適本人對梁武帝與達摩關系的懷疑也是站不住腳的。
孫述圻曾對胡適的論點和論據進行過系統批判,得出了菩提達摩初抵廣州“來游中土”的時間正好在梁普通年間(520—527年)的結論[8]。他的結論和歷代禪宗門人對達摩來華時間的記述是一致的。筆者以為,無論如何,關于達摩來華的時間,禪宗門人是沒有必要撒謊的。而只要達摩來華的時間是在梁普通年間,其首先經過的地方又隸屬于南朝,極度崇佛的梁武帝就沒有不見他的道理。而一見之后,話不投機,菩提達摩遂飄然北渡,則非常符合情理。
胡適搞學問最著名的原則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們不妨依樣畫葫蘆地再來一遍。我們的假設是:菩提達摩碑文就是梁武帝親撰的。推定過程如下:
首先,我們認為,在達摩來華時間和來華路線上,其弟子們沒有必要撒謊,因此,諸如宋道原著《景德傳燈錄》、明刊本《新鍥全像達摩出身傳燈傳》等記載的達摩于梁普通八年(527年)或普通七年(526年)到達南海(今廣州)是可以作為依據的。其次,達摩到達廣州,地方官是應該知道的,而且地方官知道梁武帝崇佛。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出于責任心,還是想拍皇帝的馬屁,及時報告并迎請是沒有問題的。至于是不是果真在十天之內就到達了南京,倒沒有必要較真兒。其三,南京是南朝(梁)的首都,即使廣州的地方官不理會達摩,達摩也會設法到南京一游。其四,只要到了南京,依梁武帝的做派,不予接見是不可能的;即使梁武帝忙于公務,無法及時安排會晤,達摩也會耐心等待。總之,梁武帝與達摩的晤談是必然要發生的。其五,達摩本來寄希望于梁武帝幫助其弘法,結果發現話不投機,“道不同不相為謀”,遂飄然北去,繼續游歷。當時的梁武帝對達摩的離去似乎也未太在意。其六,達摩至北魏后,面壁九年,終于掌握了弘揚佛法的訣竅,創造了禪宗,并吸引了眾多弟子,影響日大。梁武帝聽說后,難免懊悔,怎么這樣的人才居然沒有留住?其七,由于達摩在北魏也未受到更高的禮遇,其對梁武帝最初的挽留必定也心存暖意。達摩涅后,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弟子們及時向梁武帝通報了信息。其八,故人逝去,難免引起溫情的回憶,文采風流又篤信佛教的梁武帝遂起草了這篇《菩提達摩大師頌并序》。“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表達的正是梁武帝對與達摩失之交臂的一種復雜情緒。
當然,歷史考據畢竟不能等同于玩推理,但是當由于歷史久遠、資料缺乏,一些重要的真相無法定論時,人之常情應該成為可以容忍的坐標系。總之,筆者以為在新的、更為可靠的證據出現之前,對于“達摩碑文是否由梁武帝親撰”這一課題,最好的辦法是存疑。
[1]小島岱山:《菩提達摩石碑碑文并參考資料》,《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1期。小島岱山生于1947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印度哲學印度文學科,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華嚴學研究所所長。
[2]紀華傳:《菩提達摩碑文考釋》,《曹溪禪研究》2003年2期。
[3]高士濤:《中國禪宗第一人——慧可大師》(下),《禪》2001年2期。
[4]溫玉成:《傳為達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記》,《中國文物報》1994年11月13日。
[5]清光緒《廣平府志》卷35《金石略上》。
[6]《舊唐書》卷157《辛秘傳》。
[7]同[6],卷15《憲宗紀》。
[8]孫述圻:《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3期。
〔責任編輯:許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