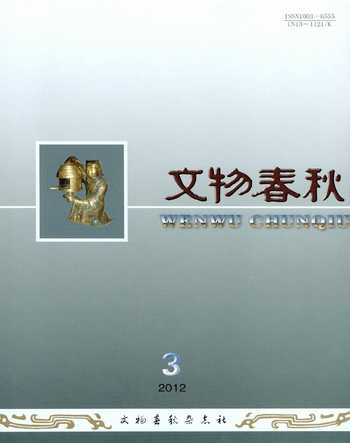懷念良師蘇秉琦先生
鄭振香
【關(guān)鍵詞】蘇秉琦先生;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教研室
【摘要】1952年,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設(shè)考古專業(yè),聘請(qǐng)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蘇先生在北京大學(xué)任教、承擔(dān)考古教研室的重任達(dá)30年之久,培養(yǎng)出一支具有專長(zhǎng),有較高研究水平的教師隊(duì)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為北京大學(xué)考古教學(xué)與科研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新中國(guó)建立后,各項(xiàng)建設(shè)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到處出現(xiàn)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考古事業(yè)的興起。在舊中國(guó),只有少數(shù)考古學(xué)家在研究機(jī)構(gòu)中從事研究,而新中國(guó)的建設(shè)事業(yè),需要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考古人員到田野配合建設(shè)工地進(jìn)行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需要對(duì)考古學(xué)界提出了培養(yǎng)干部的要求,經(jīng)過(guò)老一輩考古學(xué)家的醞釀和討論,1952年,在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設(shè)考古專業(yè),由此考古學(xué)這門(mén)20世紀(jì)初在中國(guó)出現(xiàn)的新興學(xué)科,登上了大學(xué)的殿堂。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隨著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考古專業(yè)改為考古系,如此更有利于學(xué)科的獨(dú)立發(fā)展。與考古事業(yè)不斷發(fā)展的同時(shí),博物館事業(yè)也在全國(guó)各地日漸興旺,根據(jù)需要,北大考古系又?jǐn)U建為考古文博學(xué)院,分設(shè)考古系與博物館學(xué)系。任何事業(yè)總是逐步發(fā)展的,由初創(chuàng)到逐步發(fā)展壯大,進(jìn)而臻于完善。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達(dá)到今天的繁榮、輝煌是經(jīng)過(guò)半個(gè)多世紀(jì)的歲月,幾代人的努力。俗語(yǔ)說(shuō),萬(wàn)事開(kāi)頭難,也說(shuō)創(chuàng)業(yè)維艱,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是如此。現(xiàn)在北大考古系已有了龐大的教師隊(duì)伍,諸多著名考古學(xué)家,各門(mén)課程的體系與內(nèi)涵日趨完善,且與時(shí)俱進(jìn),增添了新的科技部門(mén)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這是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不懈奮斗的結(jié)果,令人欽佩。
回首當(dāng)年初建考古專業(yè)時(shí),可以說(shuō)是白手起家,教師只有閻文儒和宿白二位先生,他們是從北大文科研究所過(guò)來(lái)的,經(jīng)與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協(xié)商,聘請(qǐng)?zhí)K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此蘇先生成為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蘇先生認(rèn)真負(fù)責(zé),他與宿白先生主持教研室的各項(xiàng)工作,如課程設(shè)置,設(shè)中國(guó)考古學(xué)課程,以及各不同歷史階段與主要課程相關(guān)的輔助課程進(jìn)行配合,使同學(xué)們擴(kuò)大知識(shí)面,開(kāi)拓視野。例如,為攻讀商周考古的同學(xué)開(kāi)設(shè)古文字學(xué)、古器物學(xué)、古文獻(xiàn)學(xué)等,同樣,學(xué)習(xí)秦漢、隋唐時(shí)期考古的同學(xué),也有相關(guān)的選修課程,如石窟寺、繪畫(huà)、陶瓷等,使同學(xué)們能夠得到多方面的相關(guān)知識(shí)。配合教學(xué)還經(jīng)常組織同學(xué)去故宮博物院、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參觀,通過(guò)參觀,同學(xué)們對(duì)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文化遺物有了感性認(rèn)識(shí),鞏固并加深了對(duì)所學(xué)課程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
安排歷屆田野實(shí)習(xí)是教研室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上世紀(jì)50年代初,主要在考古研究所各工地實(shí)習(xí),如洛陽(yáng)中州路發(fā)掘工地、西安半坡遺址發(fā)掘工地等,都曾有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的學(xué)生參加實(shí)習(xí)。隨著師資力量的加強(qiáng),北大考古教研室也單獨(dú)承擔(dān)一個(gè)遺址的發(fā)掘,并負(fù)責(zé)完成發(fā)掘報(bào)告,如洛陽(yáng)澗西王灣遺址,就是由北大考古專業(yè)師生進(jìn)行發(fā)掘的。學(xué)生實(shí)習(xí)發(fā)掘工作告一段落,要進(jìn)行室內(nèi)整理,利用發(fā)掘資料編寫(xiě)實(shí)習(xí)報(bào)告。如此可以對(duì)田野發(fā)掘、整理、寫(xiě)出報(bào)告的全過(guò)程有個(gè)基本的了解,為日后從事考古工作奠定基礎(chǔ)。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是深有體會(huì)的。由于我曾參加由文化部國(guó)家文物局、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聯(lián)合主辦的考古訓(xùn)練班,聽(tīng)過(guò)中國(guó)考古學(xué)課程,所以我免修中國(guó)考古學(xué),因此在北大本科讀書(shū)時(shí)并未聽(tīng)蘇先生授課。我有幸聆聽(tīng)先生的教誨,是1954年畢業(yè)后被分配留校任助教。那年秋季,1951級(jí)北大考古專業(yè)的同學(xué)在考古研究所洛陽(yáng)考古隊(duì)進(jìn)行田野考古實(shí)習(xí),大約在11月間,要由田野發(fā)掘轉(zhuǎn)入室內(nèi)整理,編寫(xiě)實(shí)習(xí)報(bào)告,當(dāng)時(shí)是配合基建工程,發(fā)掘工作很緊張,隊(duì)里抽不出人來(lái)輔導(dǎo)同學(xué)實(shí)習(xí), 希望北大考古教研室派一同志輔導(dǎo)同學(xué)實(shí)習(xí),教研室決定派我去,我欣然接受。因?yàn)槲覅⒓涌脊庞?xùn)練班學(xué)習(xí)時(shí),曾在洛陽(yáng)實(shí)習(xí),參加發(fā)掘洛陽(yáng)燒溝戰(zhàn)國(guó)墓,畢業(yè)實(shí)習(xí)時(shí)是在郭寶鈞先生指導(dǎo)下調(diào)查、試掘,尋找西周“王城”,對(duì)洛陽(yáng)澗東一帶比較熟悉。而這次同學(xué)實(shí)習(xí)整理的是當(dāng)時(shí)在洛陽(yáng)中州路工地發(fā)掘出的一部分東周墓葬,有少數(shù)是春秋時(shí)期的,大多數(shù)是戰(zhàn)國(guó)墓,一般為中小型墓葬,適合同學(xué)實(shí)習(xí)。整理工作是在蘇秉琦先生指導(dǎo)下進(jìn)行的,蘇先生對(duì)整理資料有系統(tǒng)的工作程序,首先依據(jù)文化層和墓葬之間的打破關(guān)系,選出保存比較好,又有早晚關(guān)系的墓葬,如春秋時(shí)期的選出幾座,并盡量選出土器物組合不同的,如單一件鬲的,戰(zhàn)國(guó)墓絕大多數(shù)是鼎、豆、壺,另有小部分出鼎、盒、壺。挑選出比較典型的墓葬之后,要求同學(xué)自己觀察,分析早、晚時(shí)期在組合和器形上的變化。蘇先生循循善誘,同學(xué)們雖然領(lǐng)會(huì)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數(shù)同學(xué)都能觀察出共同點(diǎn)和不同特點(diǎn)。如同學(xué)們注意到一件春秋時(shí)期的陶鼎深腹、直耳、無(wú)蓋,豆體較瘦高,個(gè)別墓出土陶鬲;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鼎腹較淺、耳略外侈、有蓋,豆體較矮、腹較肥碩,壺制作多較精致,罕見(jiàn)鬲,戰(zhàn)國(guó)墓出現(xiàn)鼎、盒、壺的組合尤為同學(xué)所關(guān)注。通過(guò)對(duì)墓葬出土陶器組合和器物形制的變化,同學(xué)們學(xué)到了整理資料的基本方法。大家都說(shuō),這個(gè)階段學(xué)到不少知識(shí),初步掌握了整理資料的基本方法。
參加這次同學(xué)實(shí)習(xí),對(duì)我自己是一次難得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我感到首先觀察器物整體組合,然后分析不同發(fā)展階段器形的變化,這種整理方法較沿用按照金石學(xué)的路子分類研究要好。如分類別排隊(duì),即是采用類型學(xué)對(duì)器物進(jìn)行排比,從縱向演變區(qū)分早晚,而所選排比的器物要求用造型比較好的,這樣往往將典型單位的器物拆散,選用甲墓的鼎,乙墓的豆,雖然兩墓可能是同一時(shí)期的,但也可能略有早晚,這樣做的結(jié)果讀者只能相信作者的結(jié)論,不利于自己進(jìn)行判斷。當(dāng)然,大量器物分型分式報(bào)導(dǎo)也是必要的,但盡量多發(fā)表一部分典型單位的成組標(biāo)本,以便讀者看到更多的原始材料。蘇先生整理考古資料的方法超越了金石學(xué)分類研究的方法,在運(yùn)用類型學(xué)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我通過(guò)這次實(shí)踐受益匪淺。
另一次直接得到蘇秉琦先生的教誨是1959年,我在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之后,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當(dāng)年秋季到考古所洛陽(yáng)發(fā)掘隊(duì)。那年北大考古專業(yè)1955級(jí)同學(xué)到洛陽(yáng)實(shí)習(xí),由鄒衡先生帶隊(duì),夏超雄同志參加,我與夏超雄協(xié)助鄒先生做同學(xué)實(shí)習(xí)的輔導(dǎo)工作。實(shí)習(xí)地點(diǎn)在洛陽(yáng)澗西王灣遺址,遺址內(nèi)涵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shí)期的堆積。蘇先生對(duì)同學(xué)實(shí)習(xí)很重視,親自到工地指導(dǎo)工作,并較長(zhǎng)時(shí)期住在工地附近的窯洞里。蘇先生來(lái)工地時(shí)已開(kāi)工一段時(shí)間,已發(fā)掘到一座仰韶文化時(shí)期的灰坑,出土大量的彩陶片,對(duì)出部分陶器鄒先生高興地說(shuō):“真是一個(gè)寶坑。”蘇先生看過(guò)之后說(shuō),要認(rèn)真對(duì)陶片,將陶片摸熟,小片對(duì)成大片也好,教同學(xué)們掌握基本的整理方法,要把一個(gè)坑的陶片摸熟,能復(fù)原的復(fù)原,殘片如紋飾有特點(diǎn)也要作為標(biāo)本保存。蘇先生提出的要求很具體,便于操作,同學(xué)們也很認(rèn)真,在鄒先生具體指導(dǎo)下,對(duì)各單位的陶片首先分類統(tǒng)計(jì),然后對(duì)陶片。同學(xué)們初次參加整理,每對(duì)起一件陶器都很高興。鄒衡先生對(duì)同學(xué)實(shí)習(xí)抓得很緊,經(jīng)常了解各組同學(xué)的學(xué)習(xí)情況,同學(xué)們積極性也很高,工作認(rèn)真,最后通過(guò)室內(nèi)整理,復(fù)原了大量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shí)期的陶器。實(shí)習(xí)結(jié)束后,將復(fù)原的器物在考古所洛陽(yáng)工作站內(nèi)上架存放,擺滿了一間屋子。這次實(shí)習(xí)取得豐碩成果,在當(dāng)時(shí)是豫西地區(qū)仰韶、龍山文化的一次重要發(fā)現(xiàn),不少學(xué)者前往參觀。
我有幸參加了這次發(fā)掘工作,再一次聆聽(tīng)了蘇先生關(guān)于資料整理的論述,有了新的體驗(yàn)。整理遺址與墓葬不同,墓內(nèi)器物對(duì)合比較簡(jiǎn)單,遺址不僅發(fā)掘時(shí)現(xiàn)象比較復(fù)雜,整理也較困難,因?yàn)榛铱印⒔蜒▋?nèi)的文化遺物是逐步填入,大多是殘破的陶片,而且有的灰坑往往出土十幾筐陶片,要分別對(duì)合出各種類別的器物必須下工夫,如先生所言將陶片摸熟對(duì)透,要做到這一點(diǎn),必須認(rèn)識(shí)這項(xiàng)工作對(duì)研究考古文化的重要意義,是研究一種文化面貌的基礎(chǔ)工作。
我有幸兩次在蘇先生指導(dǎo)下,參加同學(xué)實(shí)習(xí)、整理資料,受益匪淺,對(duì)日后從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chǔ)。1962年5月,我到考古所安陽(yáng)隊(duì)工作,將安陽(yáng)殷墟文化分期斷代作為研究工作的切入點(diǎn)。那年秋季,北大考古專業(yè)1956級(jí)同學(xué)到安陽(yáng)實(shí)習(xí),地點(diǎn)選在大司空村。這年同學(xué)人數(shù)較多,教師陣容也較強(qiáng),帶領(lǐng)實(shí)習(xí)的老師是高明、嚴(yán)文明和李伯謙三位先生。考古所安陽(yáng)隊(duì)由我和楊錫璋、戴復(fù)漢3人協(xié)助做同學(xué)實(shí)習(xí)的輔導(dǎo)工作。這次發(fā)掘?qū)τ趯?shí)習(xí)來(lái)說(shuō)還不錯(cuò),發(fā)掘到50多座殷代灰坑和50多座殷代小型墓葬。發(fā)掘工作告一段落,按照教學(xué)計(jì)劃進(jìn)入室內(nèi)整理、編寫(xiě)實(shí)習(xí)報(bào)告,我和楊錫璋同志與北大老師共同參與指導(dǎo)同學(xué)整理發(fā)掘資料。遺址、墓葬分別按單位整理,經(jīng)整理確定所發(fā)掘到的遺址和墓葬,大致是屬于三個(g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未發(fā)掘到已被確定的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僅有一座較早的灰坑,但所出陶片晚于第一期,便將其劃為第二期,較晚的灰坑出土陶片比較多,復(fù)原了不少陶器,墓葬所出陶器基本上都能復(fù)原。依據(jù)文化層和陶器形制,遺址和墓葬都可分為兩個(gè)階段,列為第三期和第四期。通過(guò)這一季度的發(fā)掘,經(jīng)共同整理,基本確定了殷墟文化分為四期的框架。能夠取得這一成果,就我個(gè)人而言,得力于1954年在洛陽(yáng)參加整理東周墓葬,得到蘇先生的教誨,得以基本掌握整理資料的方法。
這次實(shí)習(xí)效果比較好,所發(fā)掘到的居住遺址和墓葬都能區(qū)分早晚,這是有利的客觀條件,再者北大的三位教師和我都曾受到蘇先生的教導(dǎo),認(rèn)識(shí)比較接近。在整理過(guò)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選出各不同階段的分期標(biāo)準(zhǔn)器鬲、簋、豆等,觀察器物組合的變化,如陶豆在第三期很常見(jiàn),而第四期卻少見(jiàn),是明顯的變化;第三期鬲有實(shí)足跟,第四期較大的鬲多是襠近平的,無(wú)足跟;第三期簋多是侈口飾弦紋的,到第四期此式簋已消失,為飾三角繩紋的陶簋所取代。如此分別尋找出第三期和第四期的不同特點(diǎn),這種具體操作過(guò)程,是經(jīng)蘇先生的指導(dǎo)學(xué)到的。
關(guān)于所分四個(gè)發(fā)展階段的年代,依據(jù)當(dāng)時(shí)已有的資料,第一期約相當(dāng)武丁時(shí)代;第二期與第一期比較接近,但無(wú)可供斷定王年的資料;第三期依據(jù)過(guò)去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隊(duì)發(fā)掘的一座灰坑出有陶器與刻字卜骨,得知其年代約相當(dāng)康丁至武乙時(shí)期;第四期的年代據(jù)后岡圓形祭祀坑所出“戌嗣子鼎”銘文的文字結(jié)構(gòu)觀察,約當(dāng)?shù)垡摇⒌坌習(xí)r期。一個(gè)跨越時(shí)間比較長(zhǎng)的課題,不可能通過(guò)一次發(fā)掘得到解決,但這是在安陽(yáng)殷墟按照蘇先生的思路所進(jìn)行的一次實(shí)踐,為研究殷墟文化的分期斷代奠定了基礎(chǔ)。
蘇秉琦先生思維能力強(qiáng),且勤于思考,并善于解決實(shí)際問(wèn)題。如1955年以來(lái),編寫(xiě)中國(guó)考古學(xué)教材成為考古教研室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對(duì)于劃分階段容易取得共識(shí),但各階段如何編寫(xiě)都值得探討。記得討論西周與東周時(shí),提出縱向與橫向的問(wèn)題,蘇先生講,郭沫若寫(xiě)《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西周按年代分,東周按國(guó)別分是有道理的,可考古學(xué)不像一件件器物,不能一國(guó)一國(guó)地寫(xiě),但可以將國(guó)別與區(qū)域結(jié)合,如三晉是一片,但資料很少,過(guò)去臨淄與燕下都做過(guò)工作,資料也很零散,目前只有東周近年所做系統(tǒng)發(fā)掘比較多,積累資料豐富,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墓葬為數(shù)相當(dāng)多。目前可以東周為重點(diǎn),將中原地區(qū)墓葬所出陶器的發(fā)展序列弄清,以便今后與其他地區(qū)進(jìn)行比較研究。考古工作發(fā)展不平衡是客觀存在,但有了中原地區(qū)的分期與年代作為標(biāo)準(zhǔn),有利于對(duì)其他地區(qū)進(jìn)行研究,不斷補(bǔ)充其他地區(qū)的資料,闡明其基本特點(diǎn)和大致年代。當(dāng)時(shí)尚無(wú)可供參考的考古教科書(shū),能夠提出各時(shí)期一個(gè)比較清楚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實(shí)屬不易。
教師隊(duì)伍的不斷成長(zhǎng),全國(guó)各地田野考古發(fā)掘的進(jìn)展,各不同時(shí)期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為編寫(xiě)教材提供了有利條件。在蘇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的領(lǐng)導(dǎo)和組織下,根據(jù)各位教師的研究方向,對(duì)各時(shí)期的編寫(xiě)工作進(jìn)行分工,然后分頭編寫(xiě)。這是一個(gè)比較大的系統(tǒng)工程,教材的內(nèi)容接觸面廣,需要一定的知識(shí)積累,這樣一個(gè)開(kāi)創(chuàng)性的工作,對(duì)于建立專業(yè)不久的教師隊(duì)伍,承擔(dān)這項(xiàng)任務(wù)是相當(dāng)繁重的,但教研室的各位同志都熱情積極地投入編寫(xiě)工作,經(jīng)過(guò)數(shù)年的不懈奮斗,終于在20世紀(jì)60年代初,新編教材先后完成。這是新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教材。通過(guò)編寫(xiě)教材,培養(yǎng)了人才,提高了教學(xué)質(zhì)量,雖然出于慎重和質(zhì)量保證未正式出版,但其影響仍是相當(dāng)大的。這是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建立以來(lái)的一項(xiàng)重要成果,領(lǐng)導(dǎo)編寫(xiě)教材的前輩蘇先生和宿白先生付出了心血和辛勤勞動(dòng),是我們晚輩應(yīng)該銘記的。1952年建立考古專業(yè)之后的10多年,是工作最繁忙的時(shí)期,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文革”期間考古工作處于停滯狀態(tài),教學(xué)工作也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破壞。十年動(dòng)亂結(jié)束之后,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各項(xiàng)工作逐步走向正軌,迎來(lái)了科學(xué)的春天,考古工作也欣欣向榮,重新投入工作的考古工作者積極性很高,考古戰(zhàn)線上不斷傳出捷報(bào)。沉寂多年的良渚文化,突然在草鞋山遺址有了突破性的發(fā)現(xiàn),這一發(fā)現(xiàn)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給從事發(fā)掘工作的人們以重要啟迪,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了良渚文化的分布規(guī)律及其重要意義,為日后江浙地區(qū)良渚文化的重大發(fā)現(xiàn)揭開(kāi)了序幕。其后是紅山文化的驚人發(fā)現(xiàn),規(guī)模宏偉的積石冢、女神頭像等,無(wú)不發(fā)人深思,蘇秉琦先生給以高度重視,譽(yù)之為“文明的曙光”。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先后發(fā)現(xiàn)重要建筑基址或墓葬,為考古研究和教學(xué)工作提供了新資料,拓寬了視野,教學(xué)工作與時(shí)俱進(jìn),北大考古專業(yè)的教師分別為自己所負(fù)責(zé)編寫(xiě)的教材進(jìn)行修改,不僅補(bǔ)充了新資料,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上也有了明顯提高,已是一部?jī)?yōu)秀的考古著作。但人們總是在追求完美,不滿足已有的成果。
蘇秉琦先生對(duì)培養(yǎng)考古事業(yè)接班人也極為重視,20世紀(jì)50年代,北大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招收研究生之后,考古教研室立即行動(dòng),在上世紀(jì)60年代已培養(yǎng)出數(shù)位研究生,分配到各地區(qū)任教,或從事科研工作,促進(jìn)了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文革”期間停止招收研究生10余年,改革開(kāi)放以后,人們的視野更為開(kāi)闊,放眼世界,培養(yǎng)研究生、博士生成為各學(xué)科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蘇先生雖不再親自指導(dǎo)研究生,但對(duì)這項(xiàng)任務(wù)十分關(guān)心,重視研究生的論文選題,給予指導(dǎo)老師和研究生以有益的啟示,以利于論文的順利完成。多位研究生的論文答辯都請(qǐng)?zhí)K先生參加,蘇先生很認(rèn)真,在仔細(xì)閱讀論文之后,答辯時(shí),在肯定研究成果的同時(shí),往往指出應(yīng)注意的問(wèn)題,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使同學(xué)們得到教益。
蘇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學(xué)任教,承擔(dān)考古教研室的重任達(dá)30年之久,領(lǐng)導(dǎo)完成了編寫(xiě)教材的任務(wù),培養(yǎng)出一支具有專長(zhǎng)、有較高研究水平的教師隊(duì)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為北京大學(xué)考古教學(xué)與科研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考古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各地區(qū)出土文物日漸增多,博物館事業(yè)隨之興起。自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不少省、市擴(kuò)建或新建了博物館,不僅展出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物,還展示了一些重要遺跡和墓葬,使考古文物事業(yè)為廣大群眾服務(wù),博物館成為宣傳歷史文化教育的平臺(tái),也為學(xué)者進(jìn)行研究提供了方便。博物館事業(yè)的大發(fā)展,需要培養(yǎng)從事博物館工作的專家學(xué)者,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的成立,設(shè)立博物館學(xué)系,適應(yīng)了時(shí)代的呼喚。
北大文博學(xué)院建立后,考古系提出編著多卷本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任務(wù),通過(guò)多位教師的辛勤勞動(dòng),必將寫(xiě)出高質(zhì)量的考古學(xué)專著,既為教學(xué)所需,也為考古工作者提供高質(zhì)量的學(xué)術(shù)成果,促進(jìn)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我們企盼著這部凝聚著幾代人的心血和精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早日面世。
〔責(zé)任編輯:張金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