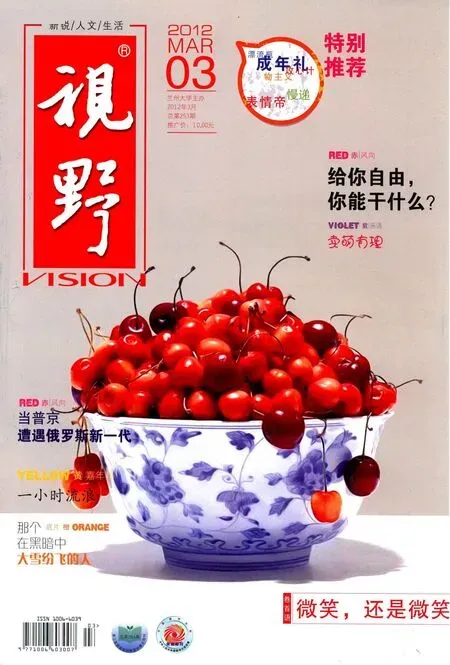先生淡然
王涵
岡比先生是我在法國讀博士預科(國內的碩士學歷)時的導師。他滿頭銀發,面目慈祥,雖然有些不修邊幅,但那種大學者的氣度卻是不言自明。聽同門的一位師兄說,老岡比是歐洲乃至世界彈性力學方面的權威人士,法國國家一級教授(這個頭銜不同尋常,即使在歐洲的科教大國——法國,也不過寥寥數百人)。我沒有驚訝,因為僅從氣度而言,老人家絕對是當之無愧的。
能拜在岡比先生門下做他的學生,純屬偶然。記得那時我剛讀完一個學位,想再接再厲,再拿一個文憑,于是開始漫游法國,奔波于各大學間的面試,但得到的答復大都模棱兩可。我不敢高枕無憂,偶然聽說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有一所名叫法國航空技術學院的大學,于是想到那里碰碰運氣。
我在國內的專業是建筑學,而法國的教育體系和中國的差別極大,特別是在建筑和醫科這兩個事關人命的領域,學生必須從大學一年級開始接受專業教育。這種不兼容性使得本專業的學生想轉換門庭極為困難,而外專業的學生想半路出家往里面擠也幾乎不可能,更何況對我這樣一名外國學生來說,想在法國插班建筑專業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專業的選擇上,我只有放棄從一而終的念頭,于是便有了到法國航空技術學院碰運氣的經歷,有了我與岡比先生的相識。
面試是在一種毫無預見的情況下進行的。與其說是一場面試,不如說是一次閑談或咨詢。岡比先生略覽了我的簡歷,簡單地問了我幾個問題,我的回答從容得體。結束的時候,他淡然地說了一句,我很希望和你這樣優秀的年輕人一起工作、學習。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詞來形容老先生的話,那就是酷。這位幾乎一年四季不穿襪子的小個子教授,在你和他討論問題的時候,那種凌厲的眼神,讓你感覺到他在投入地思考。岡比先生的話很少,惜字如金,即便在學校里遇見他,我向他畢恭畢敬地問候后,他也不作答,只是用他那種很酷的眼神看著我,算是回禮。
法國的博士預科學習只有一年,半年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在老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做我的論文。
一般情況下,選擇讀博士預科是一種冒險,因為在博士預科時所學的東西太理論化,不容易給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我唯一的目標只能是繼續讀博士,而政府和企業提供的博士獎學金名額又有限,且對外國人的限制很多,于是班里同學間的競爭,尤其是外國學生之間的競爭空前慘烈。由于我屬半路出家,且有語言障礙(同學大都來自拉丁語系國家或北非法語系國家),所以盡管很努力,成績也只是中下等。看到前景渺茫,我不免有些沮喪。
岡比先生看到我有些沮喪后,便告訴我,其實論文也占總成績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論文寫得好,可以彌補理論課成績的不足。那一刻,我對他既驚訝又感動。
于是我開始瘋狂地學習,每天在實驗室里呆上十多個小時。對岡比教授,也是早請示,晚匯報。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第一批得到博士獎學金的人員名單下來了,但名單上沒有我。我的信念幾乎崩潰了,再也無力繼續我的論文。然而,岡比先生找到了我,很“冷漠”地對我說,如果我再這樣頹廢下去,他會向學校申請拒絕安排我答辯,也就是說,讓我肄業。沉默良久,他又告訴我,其實還有不少相關的實驗室需要招我這個專業的博士生,只要做好論文,還是有機會的。
我收起沮喪的情緒,打起精神繼續學習。直到論文答辯臨近,岡比先生再次讓我看到了他讓人感動的一面。他患了重感冒,還是擠出時間,為我安排了幾次答辯預演,告訴我應該如何在論文答辯會上解釋自己的科研成果,讓任何一個非本專業的人士理解這個課題。后來我才知道,全班近30人,只有我做了論文答辯預演。
答辯結束,公布了成績,滿分為20分,我得了全班最高分17分。當答辯委員會人員退場后,岡比先生走到我面前,很嚴肅地對我說,你是一個很適合搞科研的人,一個半路改專業的人能將如此復雜的論文課題做得這么好,你真的很棒。最后先生給我一個忠告,在任何時候,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持之以恒。言畢,先生握了握我的手,一如從前地酷。
后來我到了另外的一個大學讀博士,那年圣誕節,我給岡比教授寄了張卡片,上面寫了很多感謝的話,最后,我還附上了一句中國的古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先生給我回了一封電子郵件,寥寥數行,大意是,不必感謝,這是一個老師對學生應該做的。
(韓世平摘自《世界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