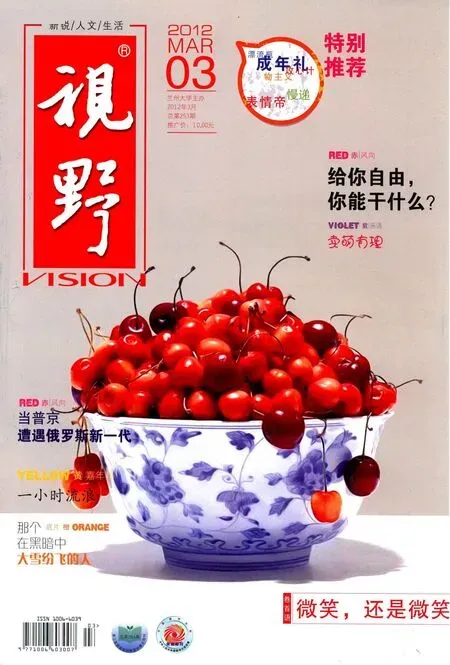那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
林衍
伴著莫扎特與巴赫的鋼琴曲,穿著黑色呢子大衣、戴著格子圍巾的木心躺在鮮花中,與這個世界告別。
陳丹青將一盒紅色中華煙放在木心的枕邊。“先生一輩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兒高貴地離開。”陳丹青說。
這位并不為人所熟知的老人,六年前離開美國,隱居在家鄉(xiāng)烏鎮(zhèn)的“晚晴小筑”里。同年,其散文集《哥倫比亞的倒影》在國內出版。那時,這位在大陸的“新作者”已經79歲了。
事實上,早在1984年,臺灣《聯(lián)合文學》創(chuàng)刊號便為木心特設“散文展覽”專號,題名《木心,一個文學的魯濱遜》。而那時木心的部分散文與小說也已經被翻譯成英語,成為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范本讀物,與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編在同一教材中。
也正是在紐約的地鐵上,上世紀80年代初赴美留學的陳丹青結識了日后被他稱為“師尊”的木心。
“在我與木心先生相處的29年里,我親眼目擊他如何摯愛藝術,如他自己所說:人不能辜負藝術的教養(yǎng)。”陳丹青在悼詞中寫道。
上世紀80年代是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他在的士里寫,巴士站上寫,廚房里一邊煮食一邊寫,最喜歡在咖啡店的一角寫,寫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臺子上,還要來兩句:“即使我現(xiàn)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個顧客了。”
他清晨六點起床寫作,一天通常要寫七千字,要反復修改,五稿六稿,過一周再看再改。木心常說,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讀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窩囊。
中國美院教授曹立偉還記得,木心很喜歡《詩經》,說如果別人拿《荷馬史詩》和我換《詩經》的話,我是不換的。他鼓勵年輕人讀尼采,說尼采是“鈣”,可以使骨頭硬起來。講到福樓拜時,他的眼睛會濕潤起來。一次聽木心的開場白,他說:“在一個萬國交界的地方,有一個房屋,里面有一個老人,這個老人接待路過的所有類型的朋友,有強盜,有英雄,有商人,有學生,有流浪漢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請進來,都可以長談,這個老人就是文學。”
生于80年代的書評人顧文豪曾去探訪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坐定,點煙,即談文學藝術。聊到興起處,點煙時煙頭竟反了,點了煙屁股,一吸差點兒燒到自己,忙說“這就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木心還為顧文豪取來美國原版畫冊觀賞,講畫時話不多,只說:“你們看畫,我看你們的眼睛。”臨行時,顧文豪曾請木心簽名留念,木心笑拒,答說:“今天要讓你一無所獲,滿載而歸。”
“先生是有貴族氣質的,把自我也當作藝術品在雕刻。”顧文豪說。
他眼前的木心,穿花色襯衫,外著一白色馬甲,穿牛仔褲,戴著精致的戒指,笑起來眼睛里“很清澈”,像一個“滿頭銀發(fā)的大男孩”。
1927年的冬天,一個名叫孫璞,號木心的男孩子生于烏鎮(zhèn),是大戶人家的少爺。
孫家花園距茅盾家不遠,木心幼時常到沈家借書,讀破了,修補好了再去歸還。而他的私塾先生便是著名詞人夏承燾。
他歡喜《詩經》就是“我要的文體”,也在十四五歲之際就知道“瓦格納跟尼采的那場爭論”。他學張愛玲寫農村,也學瓦格納寫悲劇,寫到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寫鬼魂出場”。
木心曾笑談,自己的祖先在紹興,精神傳統(tǒng)在古希臘。
陳丹青稱其為‘五四文化的“遺腹子”,“先生可能是我們時代唯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tǒng)與“五四”傳統(tǒng)的文學作者”。
然而,木心本人卻從未與任何文學團體結緣,始終自稱為“文學的個體戶”。
1946年,他考入上海美專學習油畫,不久后轉入杭州國立藝專研習中西繪畫。20歲出頭時,這位貴公子還曾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白天上街游行,傍晚則點上一根蠟燭彈奏肖邦。
新中國成立后,他仍舊長于繪畫,熱愛寫作,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
“文革”爆發(fā)后,從14歲起創(chuàng)作的20本小冊子悉數(shù)被抄沒,木心也被關入防空洞。
在獄中,他用白紙畫了鋼琴的琴鍵,無聲彈奏莫扎特與巴赫。他還在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散文、詩歌。墨水快要用光了便摻點水進去故意打翻在飯里,以寫檢查為由向看守要墨水。他寫滿了66張白紙的《獄中札記》,藏在棉襖夾層里。他還為此創(chuàng)作了一首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
“文革”后,木心被任命為上海工藝美術家協(xié)會秘書長,本可過上安穩(wěn)的日子,但他卻決定自費留學到紐約。
80年代末,曹立偉夫婦在紐約買了新房,并邀請木心入住。
他喜歡吃甜食,愛逛古董店,常在地鐵口迷路。他愛看報紙,但從不看文藝界的新聞。他也很少打開電視,偶爾破例是因為邁克爾·杰克遜的巡回演唱會。
他穿著講究。他曾親手把一條細燈芯絨直筒褲細細密密地縫成馬褲,釘上一排五顆扣子,用來搭配皮靴。他會戴著眼鏡裁剪襯衫,并贊賞托爾斯泰是會自己做靴子的人。
“他太干凈了。”曹立偉說,“這種干凈是從內而外的。”
2006年,他的作品被引入大陸,他本人也被陳丹青接回中國。陳丹青說,先生像小孩子一樣,他說飛機降落怎么這么慢,蒼蠅一停就停住了。
雖然姍姍來遲,但畢竟還是來了。陳丹青曾數(shù)次告訴讀者,要去閱讀木心,理解木心,因為在漢語書寫持續(xù)荒敗的年代,是他在獨自守衛(wèi)漢語的富麗、漢語的尊嚴。
在木心深度昏迷的時候,十幾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讀者在病床前照顧先生。陳丹青曾把他們叫到先生的病房,為他們拍了合照,回去一看覺得都像孤兒一樣。
這些年輕人會在木心的床前低聲念起那首叫《我》的小詩:我是那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馬坤摘自《中國青年報》,本刊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