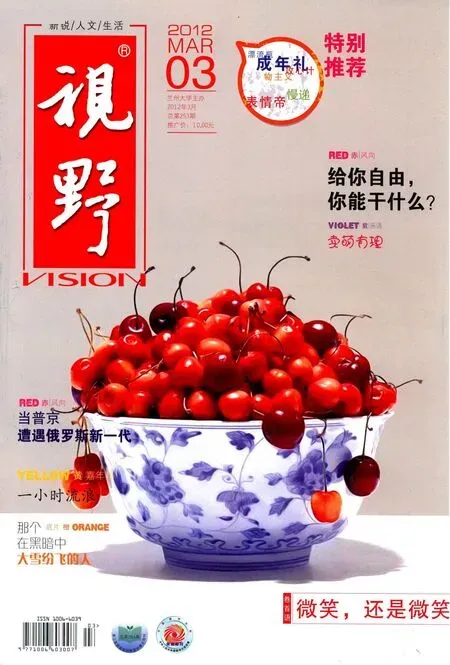上海姑娘結婚記
Flora
既然要說結婚,那么還得先從擇偶開始說起。
2004年我畢業(yè)后幸運地在上海找到工作,也就此在“魔都”扎根奮斗。上海姑娘M就是初入職場時同一天同一部門報到的同事,也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M身上,我對于上海人既有的印象一次次被打破,也對身為外地人所不了解的上海文化有了新的理解。
M成長在上海的黃金地區(qū)黃浦區(qū),有著與生俱來的優(yōu)越感。如果不是因為上班在浦東,我想她大概不會跨過黃浦江吧。門檻精、嘴巴甜,上海姑娘的鮮明特征也在她身上充分體現。會在七浦路淘些東西,再搭配上南京西路買來的名牌大衣;吃飯會去經濟實惠的小店;看懷孕的朋友會謹記不買食品當禮物,理由是“萬一吃壞肚子算誰的責任”。但作為好朋友,你又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善良,甚至是義氣。會給你講人情世故,會為你打抱不平,甚至會早晨五點起來幫你去醫(yī)院排號,只因為她家住得更近。
就是這么一個上海姑娘,在認識她的七年時間里,眼瞅著她在感情道路上跌跌撞撞、反反復復,最終在30歲“大限”來臨之際,把自己嫁了出去。上海姑娘的擇偶標準高,估計全國人民都略有耳聞。有房子伐?有鈔票伐?賣相好伐?幾乎每個上海阿姨最關心的都是這幾個問題。M的母親以及她自己也不例外。
房子是相親的起碼條件,只是從最初的“有房無貸”慢慢過渡到了“一起還貸”。大富大貴的人家畢竟是少數,所以“鈔票”這一條最終演化為“職業(yè)前景可期”。至于賣相,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比不過王力宏,但至少也得看起來順眼。M還有一個硬性條件,即只要上海人。剛開始聽起來覺得刺耳,后來時間長了,覺得也能理解,同樣的文化結合在一起,會少了很多摩擦。眼前最實惠的就是,過年不必為去哪里過而糾結。
好了,找來找去、談來談去,找到了所謂“合適的人”,談出了所謂的“愛”,倆人終于把結婚擺上了日程,好戲這才開始。
鉆戒81分大小,品質優(yōu)良,價值3.7萬元;對戒也是必需的,不帶鉆的也要4000塊。婚禮選在了冬天,那再來一件貂皮大衣吧,這又是兩萬元。婚車、婚禮現場布置、酒席、酒水、婚紗、化妝、蛋糕、親友團大巴……(項目太多,此處省略若干字)零零碎碎加起來,又是幾萬塊。新郎乃一介普通白領,薪水中等,存款有限,經過這番大手筆花費,早已捉襟見肘,大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趨勢,仿佛一夜之間經濟水平從小康回到了解放前,好在身邊多了一個美嬌娘。我問新娘:“你們倆要一起過日子的,干嗎要把他榨干啊?”新娘曰:“積蓄留著也都是他的婚前財產,還是變成共同財產讓我安心。”
婚禮當天,我陪著M姑娘在娘家化妝換裝。這時,一句“儂鉆戒把吾看看”的話在耳邊響起。好在我聽懂了,趕緊把新娘的鉆戒捧上。來者乃小區(qū)鄰居,是一位50歲上下的上海阿姨,氣質精明、精干。“81分看起來不是很大嘛。阿拉小囡明年也要結婚,看來還得買一克拉的。”“哎喲,儂的貂皮大衣不要太好看啊!”……贊美、奉承與自抬身價剎那間在耳邊齊飛,上海人也許是習慣了這樣的交際方式,看不出絲毫的不滿與不屑。
依舊是鞭炮、紅包等等禮儀,全國各地的婚禮在這些環(huán)節(jié)大體相同。把新人接到了婆家,奉茶改口叫聲“媽”,公婆二人遞上一個一萬塊的紅包外加一個一兩重的千足金鐲子,歡歡喜喜成為一家人。
婚禮現場,雙方的母親從服裝、酒席位置開始別苗頭。新郎的母親要化妝,新娘的母親也絕不落后。酒過三巡,裝換三套,客套、寒暄、祝福以及些許“調戲”之后,新娘新郎早已累趴下,娛人娛己,悅己亦悅人,偉大的任務算是徹底完成。晚上洞房花燭當然要回新房過,所以酒席臨散場之際,新娘的母親不忘交代女兒,“晚上回去把紅包數數清楚再睡覺”。
M姑娘說:“嫁人吧,關鍵還是他對你好,你和他能有話說、有錢花,其他的條件是錦上添花而已。”看來這位上海姑娘心里早就有桿秤,真正的“精明”在婚姻觀上徹底展現。
(李佳寧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