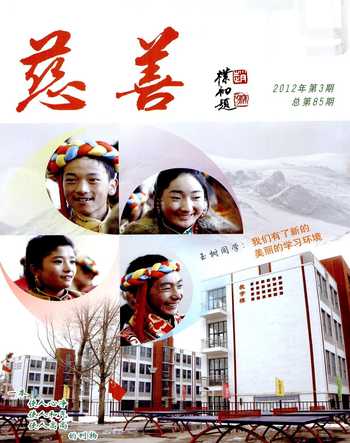20世紀30年代的天津婦女救濟院
章用秀
鑒于婦女無政治、經(jīng)濟和法律地位,1929年2月,天津婦女協(xié)會受天津特別市社會局委托,成立婦女救濟院,院長張人瑞。該院主要收容被遺棄女子、被虐待侍女及童養(yǎng)媳、不愿為娼的妓女等。收容后組織她們生產(chǎn)和學(xué)習(xí)技術(shù),并為之介紹職業(yè),亦可擇配出院。
婦女救濟院坐落在天緯路西窯洼,原為張調(diào)辰舊宅,坐南朝北,共有兩個院落,面積較大、設(shè)備較佳。進入大門,東院為宿舍,西院為一小院落,中有傳達室、職員辦公室和接待室。院落北有一門、西有一門。通過北門進入一處三合院,該院除少數(shù)職員宿舍外,其余為婦女補習(xí)教室和刺繡室。通過西門進入的四合院,為案情尚未完結(jié)的婦女居住之所,院門緊鎖且院內(nèi)沒有宿舍、教室和工作室,其空間和管理的封閉性也可見一斑。
1935年1月15日至20日,天津《益世報》發(fā)表了5篇紀實性文章,凸顯了入院婦女的生活與學(xué)習(xí)狀況:
“院生的待遇,凡是進院以后,穿著,鋪蓋,食用,完全官備”,“白色的單褲褂,是夏天服用,每人發(fā)給兩套;粗淺白布的褲褂,是冬天的襯衣,每人也是兩套;紫色線呢的薄襖,是現(xiàn)在穿著,不過穿的時節(jié),外面要罩一件藍長衫”,“院生在院每日的工作,讀書以外,要算學(xué)習(xí)技能是最重要的。目前讀書一層,分為一二三年級,課程科目,和普通小學(xué)相仿。新入院的婦女,視其程度,分編在她程度相當?shù)陌啻卫铮蛔R字和根本沒受過小學(xué)教育的,則以年歲來分,年歲小者,編入一年級”。
“另外設(shè)有婦女補習(xí)班,課程教本,悉如民眾學(xué)校,半路讀書的婦女,所以不感怎樣困難。技能一層,分作縫紉、刺繡和糊紙盒三種。縫紉刺繡兩種,年長一些院生,差不多都是一人兼擅二技。糊紙盒則是專為年幼的院生特辟的工作。以外的事,就是洗浣衣服被褥等項,年長的院生,自己照應(yīng)自己,年幼的,由年長一些的代為照應(yīng)。”
“院生的作業(yè)室,是在一所小小院落里,舊式的四合房,正房三大間,東西配房各兩間,一踏進小院天井,首先望得見正房明間里,一列隔扇門敞開著,許多女孩子,穿著白布鑲紅邊的圍裙,一排一排坐在矮凳前,目送手揮的忙碌。”
文章作者在婦女救濟院見到兩名極小的院生活潑憨跳和普通人家子女一般,一名才六歲,一名八歲,問她們想媽媽不,她們總在憨笑。一旁的李主任拉過那六歲的孩子,掀起她的衣服說,這孩子受繼母虐待,乍進院來,周身滿是傷痕,現(xiàn)在雖養(yǎng)好了,還可以辨出她那傷痕。
在正房,作者看到一些正在糊洋火盒的院生:
“這些女孩子,最大不過十二三歲,每個均充滿著生命之素的活潑,在她們心靈里,她們似乎忘了她是無父無母,或是遭人群拋棄的孤苦者,大家快樂的工作如同在她們自己家里,在她們父母跟前一般。糊洋火盒的敏捷,似乎一個快過一個,我悶站在那廂一晌,只聽得二百四百的報數(shù)。聽說她們所糊的紙盒是9角錢1萬個,承接丹華火柴公司的活計,得來的代價,由她們?nèi)w工作的院生均分,每一名雖然一天僅得著幾枚,但已足以鼓勵她們幼小的心靈,興奮她們的工作。這里雖然沒有教師監(jiān)導(dǎo),而秩序和工作并不見紊亂和呆滯。院方為使她們有自治能力,準她們互推兩名班長,這也可以稱得起是她們所公認的小首領(lǐng)了。”
文章提到,院生進院以后,照例是不許自由出入的。如果到外面去,必得院長的許可。家屬親友接見,規(guī)定在每周三、日,上午八時起,下午四時止。在這時間內(nèi),凡是院生的親屬友朋求見,經(jīng)過掛號手續(xù)即可在院生接待室會晤。如果涉及擇配問題,手續(xù)是這樣的:男方先得到該院請求,經(jīng)過院方審查可行,將雙方的身世互為傳述一下,彼此均無問題,院方亦覺求配的男人可靠,然后指定一天,雙方面談,這層手續(xù)過去,再議及訂婚或迎娶等事,如果會談的結(jié)果不佳,即日罷論。另外最重要的是,院生婚配絕對得一夫一妻,求配偶的男人,也必得娶院生為家主婦,不能在這里求妾婢。空口說話是不妥當,必得在領(lǐng)院生出院前,覓得兩家鋪保,簽訂類似一種誓約,方算完成一切手續(xù)。
作為官設(shè)機構(gòu),婦女救濟院雖然收養(yǎng)人數(shù)有限,但經(jīng)費有所保證。1936年在擴大救濟事業(yè)的規(guī)劃中,婦女救濟院被歸并到天津市救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