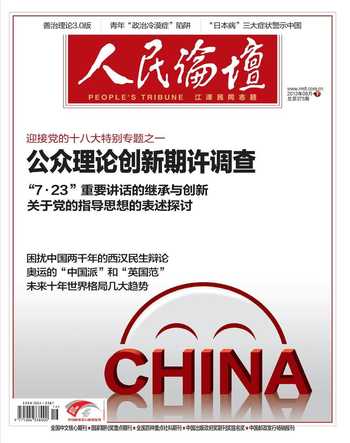美國霸權(quán)戰(zhàn)爭下一站或在亞太
龐中英
未來若干年,中國面對的頭號地緣戰(zhàn)略挑戰(zhàn)仍然是美國。目前的美國,在廣義的精英層面,許多人逐漸地在不同程度上承認了“美國衰落”的現(xiàn)實。這一過程耗費了將近10年的時間。21世紀(jì)初,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美國對它在20世紀(jì)末取得的世界任何力量無法匹敵的“超一流國力”的使用,這盡管達成了一些戰(zhàn)略目標(biāo),卻不幸被證明是極度濫用。這一濫用正好發(fā)生在支撐美國在全球范圍內(nèi)實力擴張的金融體系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性的,短期內(nèi)難以修復(fù)的危機時期。
如何解決美國霸權(quán)的危機,不僅是現(xiàn)在的美國政府,而且是未來的美國政府要面對的頭號外交政策挑戰(zhàn)。當(dāng)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美國的兩種解決霸權(quán)危機的方式可能交替和結(jié)合使用:
第一種,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新保守主義和正統(tǒng)的軍事主義者,不管是接受還是否定“美國衰落”的現(xiàn)實,都認為美國要通過“再平衡”等強化國防的力量“恢復(fù)美國的世界領(lǐng)導(dǎo)地位”,“扭轉(zhuǎn)”因為在中東的不成功和金融危機帶來的美國頹勢,他們自信心很足。其選擇的突破口并非“跨大西洋”的歐洲盟友,而是“跨太平洋”的亞洲盟友。因為,他們認識到,美國的亞洲盟友更加需要美國來滿足自己的民族主義地緣戰(zhàn)略野心,美國可以與這些盟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chǔ)上強化同盟關(guān)系。因為“擔(dān)心中國”,日韓以及東盟在可預(yù)期的未來,不會與中國一起搞東亞一體化,而是轉(zhuǎn)向早在冷戰(zhàn)時代就已經(jīng)奠定了基礎(chǔ)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架構(gòu)”;而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由于在自身的一體化上走得太遠,偏離了美國的戰(zhàn)略控制,且因為不再有歐洲內(nèi)外的迫在眉睫的傳統(tǒng)戰(zhàn)爭威脅,在戰(zhàn)略上并不急需美國。
美國在未來幾年,仍然會以“再平衡”為借口,扭轉(zhuǎn)美國戰(zhàn)略規(guī)劃者所說的因“中國崛起”而造成的暫時被動局面。在這一改頭換面的進攻主義戰(zhàn)略下,任何抵制或者不配合,甚至漠視美國戰(zhàn)略的力量,不管是國家的還是非國家的,正好為美國提供了戰(zhàn)爭借口。每一個戰(zhàn)略十年,美國都有一場,甚至多場戰(zhàn)爭,下一個十年由美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很有可能在亞太地區(qū)。
第二種,美國汲取獨往獨來即“單邊主義”或者僅僅依靠“意愿者和能力者聯(lián)盟”的教訓(xùn),仍然需要“多邊主義”或者“伙伴關(guān)系”。如果經(jīng)常與這類主張多邊主義與國際合作的美國人打交道,人們可能會以為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回到正確的方向”上。確實,主張通過全球和區(qū)域的“伙伴關(guān)系”,對付“共同挑戰(zhàn)”,聽起來不錯,做起來也可以。
但是問題在于,對待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美國的長期立場眾所周知,它們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借助安理會來合理化和合法化美國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通過二十國集團或者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機制等整合對付美國面對的全球挑戰(zhàn)而迫切需要的全球資源。所以,“多邊主義”和“伙伴關(guān)系”之下的美國,對于中國等來說,恰恰是一種巨大的挑戰(zhàn),而并非等同于中美合作的機會。
如果中國等國家在聯(lián)合國不支持美國提出的動議,或與其保持默契,美國自然暴跳如雷,而選擇“意愿者和能力者聯(lián)盟”;如果中國不能在號稱是“全球治理”的機構(gòu)或論壇配合美國,美國就會給中國扣上不愿承擔(dān)“更大國際責(zé)任”的帽子;更有甚者,美國敵視任何不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地區(qū)合作,如上海合作組織等。
美國霸權(quán)的危機和美國為解決這一危機而采取的戰(zhàn)略和政策,都與中國息息相關(guān),是現(xiàn)在更是未來影響中國外交戰(zhàn)略決策的無法回避的頭號國際因素。中國未來的任何外交政策成敗在于如何認識和對付美國挑戰(zhàn)。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責(zé)編/劉建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