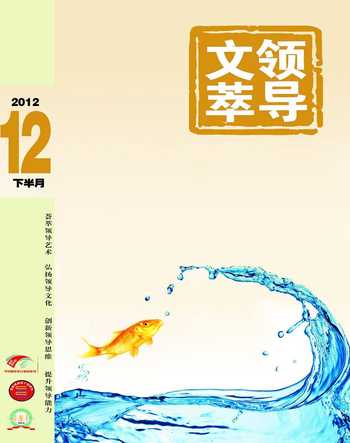當前中國企業家問題
蘇小和
問題一:企業家與開放社會的關系
企業家與開放社會,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一個健全的開放社會必然催生出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企業家反過來也必然促進開放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對中國企業家的觀察,當然也能沿用上述分析方法。事實上,這些年幾乎重大的企業家新聞,都能在開放社會與企業家關系的維度找到內因。幾年前風起云涌的《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案件,在筆者看來,事情的主要性質就是上市公司與公權力結合,在公眾知情權的層面,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演進。必須指出,這是企業管理層主導、公權力推動的行為,它使得開放社會形成一種醒目的倒退。
一個簡單的常識在這里被忽略:企業家得益于開放社會,得益于改革開放。但到了今天,因為自身利益的變化,企業家似乎對開放社會有了不同看法。
沒有自由,沒有開放,怎么會有今天豐富的生活呢?這是常識。由此,開放社會成為必然,尤其是當我們把中國當下的經濟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閱讀時,開放社會成為我們必須守住的第一范式。
中國的企業家們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呢?在新經濟領域,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對信息封鎖不僅不抵制,反而助紂為虐,幻想自己的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后,自己可以獨占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對開放社會的遮蔽;而任何對開放社會的抵制,最終必然導致企業的式微。簡言之,當企業家們都不促進開放,甚至甘愿與開放社會為敵,那些耀眼的財富、光鮮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
問題二:當年的“游牧精神”哪里去了?
當然,我們的企業家中也有思考者,比如馮侖、任志強、王石、柳傳志。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們關注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令人羨慕的財富,而是他們在財富背后不倦的思考,以及他們所思考的獨特問題。比如馮侖看上去插科打渾,其實他一直在呼喚一個可以展開自由競爭的秩序。比如任志強,雖然口沒遮攔,大話連篇,但他的趣味,在于法治的市場經濟,在于尊重那只“看不見的手”。而素有“企業家教父”之稱的柳傳志,可以說他一輩子思考的,就是一家真正的國有企業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改革。
企業家的思想體系通常應該鎖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爾·蓋茨只是一名互聯網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資大師,而谷歌創始人年輕的佩奇和布林也僅僅只是網絡搜索的發明人。他們的工作可能不關心價值體系,盡管他們有著自己最為清晰的價值底線。他們也不太關心制度設計,一個最不壞的國家制度陳列在那里,為他們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夠大的制度性保障。但中國的企業家不一樣,大多數人會認真思考他擁有哪些看上去不錯的政府資源,而一個制造業的企業家會思考他的產業結構是否與政府利益沖突,一個做網絡門戶的企業家會思考怎么繞開那些敏感詞。當然,還有一部分企業家在勞碌的管理之余,思考一些與價值理性有關的課題。
企業家既是市場分工的原動力,也是市場分工的結果。這種普適性的經濟學價值觀所帶來的經濟現象就是,越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企業家越醒目;越是企業家輩出的國家,市場經濟越發達。
不過,關于企業家的發生和發展,并不像理論推導的那樣單純。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認為,這個世界上有兩類企業家,一類是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家”,一類是官僚體系中的“經理”——前者是市場的產物,后者則是政府的食客。
筆者堅定地認為,企業家問題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中國問題”。這既是一個復雜的分工命題,也是一個復雜的制度改進問題。按照米塞斯的分析框架,當眼下中國大量的官僚經理和大量的市場企業家并存時,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兩個企業家隊伍之間的自由競爭,而是一種互為牽制的倒退。
黃光裕本可以沿著家電經銷商的戰略去發展,這個行業干凈、透明、自由競爭,缺點是不好渾水摸魚。所謂“水至清則無魚”的庸俗哲理,終于害了黃光裕,他用盡全部身家都要進入黑色地帶。黃光裕以為這樣可以發橫財,以為再也不用守著家電零售行業苦度時日了。
難道家電零售行業永遠只能小打小鬧嗎?事實上這是非常短視的判斷。沃爾瑪就是靠著零售,多年來穩居全球500強的頭把交椅。但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似乎不信這一套。即使當年曾經靠著滿世界闖蕩起家的溫州企業家們,如今也是擠破腦袋,要成為權力的座上賓。如此一來,既可以給自己撈一個主流的名分,還可以在一些新型商業資源里分一杯羹——在他們身上,已經找不到當年的“游牧精神”了。
問題三:經濟學家不應把棍子打在企業家身上
需要提出一個事實——真正的企業家天生就是善于妥協的人。為了利潤,企業家首先要與市場妥協,一個和市場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創新而是愚蠢;其次要與制度妥協,一個和政府管理方式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業家分工的命題上,經濟學家不應該把棍子打在企業家身上。這個國家顯然才開始顯得有點財富,但是創造財富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這個時代剛對市場經濟有一點懵懂的認識,但在市場上進行資源配置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要命的是,民眾對這樣的經濟態勢居然熱烈歡呼。民粹主義和均貧富主義以一種道德的姿態出場,它們首先找到的敵人,竟然是市場和企業家,以及為市場和企業家說話的知識分子。人們似乎永遠不會懂得一個道理:如果企業家沒落了,如果市場停滯了,民眾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現在有些國企似乎越來越不考慮企業的投入產出比,它們關心的是怎樣把海量的資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標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資,而不是實現了多少利潤。這種情況如果放在歷史里看,可能并不那么美妙。因為有些歷史已經顯現它的結果,雖然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正視歷史。
2011年末,胡錦濤主席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周年的高層論壇上曾這樣演說:“中國將進一步營造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這顯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市場利好消息。我們對中國市場經濟的信心,也有理由因此而增添。
(摘自《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