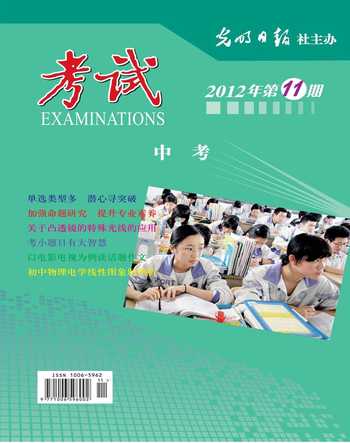兩個人的村莊
雍興中

編者按:
2012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對具有數千年農耕傳統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歷史分水嶺和大變局。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以城市生產和生活方式為主導的現代發展模式將逐漸取代寧靜、緩進的鄉村傳統,繼續推動國家和時代的進步。
在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和布局重組中,作為新城市人輸出的起點,當今鄉村社會從外觀到內里都處于巨大的嬗變之中。記者走進四川達縣一個只剩兩位老人留守的村子,管窺時代洪流中鄉村的變遷、堅守和希望。
不久前的中秋節,69歲的湯明孝哪兒也沒去,他這樣解釋——“月餅得去鄉里買。”這并不意味著湯明孝嫌麻煩,而是在這個僅剩他們夫婦兩人的深山小村里,為一個團聚的節日而刻意奔波,實在不那么必要。
四川農民湯明孝和老伴李仕芬生活在達縣金石鄉柳潭村六社桐子園,西距成都450多公里。清澈的小河劃村而過,雖無沃野千里,但也山清水秀。這個可能始建于明朝萬歷年間的山村,鼎盛時有140多口人。
但從1980年代開始,和國內千萬個村莊一樣,桐子園也遇到了城市化浪潮的沖擊。村里的青壯年先行一步,擠入城市,老人們則逐一被時光消磨。2012年年初,隨著鄰居湯正吉被兒子接到了廣州,整個村子僅剩下湯明孝夫婦兩位老人留守。
這座兩個人的村莊,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一個縮影。2012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宏大的時代背景里有大國崛起,有三十多年經濟高增長,也有農二代進城,以及留守老人的守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說,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二是中國的城市化。在這場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人口布局轉移和重組中,數千年的農耕傳統與生活方式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改變。
在世界范圍內,城市化進程從來都是推進人類文明發展最深刻的階段。湯明孝和老伴李仕芬的村莊,便是當下農耕文明深植中國的一個小小根管,當歷史車輪轟隆而來,它走到一個新的關口,有陣痛、有迷茫,也孕育希望。
“銀發”集市
2011年春節,桐子園還有四位老人——湯明孝夫婦、湯正珍老人和湯正吉。但節后隨著湯正珍和湯正吉分別被兒女接到北京和廣州,就只剩下了湯明孝夫婦倆。
被接入城,或留守故土,成為桐子園大多數老人的出路。湯明孝有四個兒子,但他不愿意到任何一個兒子那兒去。“我們走了,這村子就沒了。”
村子確實正在消失,在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顧的土房里,有些已瓦面破落,雨水侵蝕。早年熱火朝天的田地已歸還山野,湯明孝現在一人打理著800棵梨樹和300棵柑橘,養了四條狗和兩頭牛,平日里,只有牛鈴響在田間,房前屋后難聞幾次犬吠。
“有時候也能看到人。”湯明孝并不太在乎,對岸寧家村留下的人多一些,他們就過來把桐子園的地種上,從春種到秋收,人們總還能在田間地頭遇見。可半月前秋收一結束,又只剩下湯明孝和老伴了。
2012年9月27日早上,離中秋節還有三天,湯明孝穿好雨靴,背上背簍,準備去金石鄉趕場。
天并沒有下雨,桐子園的山坳卻被云霧籠罩。通向外面的小徑有兩條,一條因為久無人走已被灌木掩蓋無蹤,另一條也是雜草叢生。一段20分鐘的山路后,湯明孝來到硬化過的村級公路上,幾個老人在此候車,看見他,吼道:“真新鮮!我們村趕場,哪個讓你來的?”
湯明孝聽到反而高興起來:“你說不讓來就不來?我偏來。”這些年齡相仿的老哥們像多年未見一樣,相互開起玩笑。
在現場的還有老人朱華忠和何惠玲,后者66歲,已經是在場老人里年齡最小的了。他們每人都養育了至少兩個兒女,兒女們也都無一例外在外面打工。他們自認跟有四個兒子的湯明孝境遇差不多,“但他要典型一些”。
說起中秋節,老人們笑起來:“農村人過個啥中秋嘛。”在偏僻窮困的山村,中秋歷來不算重大的節日。老人許光仁說:“月餅?我敢說好多人都沒吃過,城里人才吃那個。”15里外,在金石鄉的集市上,月餅極為樸素地包裝成長筒狀,放在紅糖和洗衣粉同擺的攤鋪上,很難與普通糕餅區分開來。
屬于他們的中秋食品是酒米糍粑。以往的中秋,一家人割點肉,弄上一盤酒米糍粑便是過節。如今,肉倒是經常吃了,酒米糍粑倒是沒人愿意弄了。湯明孝也沒有打算弄,今年他甚至沒有預備酒米。這天他在集市上買了4塊錢豆芽,5塊錢豆腐,3斤豬肉,還有20斤復合肥。裝得滿當當的背簍里,沒有一個月餅。
進城的誘惑
湯明孝養育了四個兒子,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這意味著福氣、壯勞力以及財富。
現在,兄弟四人分別在河北、福建和達縣雙龍鎮務工,但只有老二湯輝政和老四湯健成家了。
“村里窮,交通又不好,女孩子都不愿意來。”如今在福建石獅打拼的老三湯銀輝已經37歲了,談過幾個女朋友,每次帶回家,回頭就和他分手了。
貧窮很長時間都是這里的底色,百余口人擠在狹小的山坳里,土里刨食的年月,沒人可能致富。六社社長寧升哲回憶早年說:“沒好技術,沒好種子,產量不行。”
1978年,改革開放來了,人們很快就吃飽了飯,但交通的閉塞仍然制約著山村。在湯銀輝的印象中,故鄉就像一個偏僻的孤島,即使是現在,從達縣換乘各種交通工具到村里也要3個小時。
現在已沒人能說清最早走出山村的后生是誰了,但普遍的看法是,桐子園事實上是錯過了第一波打工潮。上世紀80年代,只有零星幾個為躲避計劃生育的人出走去了海南,直到上世紀90年代,桐子園才聽到了城市化魔笛的召喚。
1991年,還在讀初一的湯輝政輟學投奔了海南屯昌縣農場割膠的舅舅,那時海南剛建省沒幾年,還是開放的熱土。后生們幾乎是不帶任何留戀地奔向了湖南、廣州、北京、福建……“年輕人沒有哪個愿意待在家里。”如今居住在金石鄉的后生湯洪濤說,可是那個時候出去已經掙不到什么錢了。
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正承接大量的產業轉移,最大的資本就是廉價勞動力。盡管從事著低端的工作,盡管挫折重重,之后的二十年間,沒人愿意回到農村,他們成了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一部分。
事實上,在這片土地上,從來不缺乏出走的沖動。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湯明孝隨父親到了達縣鐵山煉鋼,后來湯明孝送腳疼的父親回家后就再沒去了。“那之后就成立了達鋼,我要是不走,現在也是老工人。”湯明孝回憶起來很遺憾。
等到1967年,湯明孝本有機會穿上軍裝,又因年齡超了半歲而無緣城市。到了1995年,湯明孝正兒八經地與城市發生了邂逅。在北京朝陽區做木工的表親邀他去玩,他去了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他在朝陽區的大街上逛了一天,卻很遺憾地沒能去長城。
但湯明孝沒有留在北京,當時他已經50歲了,雙親尚在,故土難離。等到他了無牽掛時,年齡卻已不適合他再出去了。“可能我運氣不太好。”他笑笑。
63歲的“年輕人”
如果讓狄更斯來描述現在的中國,他或許會用經典的句式說道:這是最驚人的時代,也是最快的時代。
現在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1.27%。可資對比的是,近似的城鎮化率增幅,英國用了120年,法國用了100年,美國用了40年,而中國僅花費了22年。
這意味著,中國不僅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城鎮化規模,更有著世界上最快的城鎮化速度。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任何一個農業人口占到多數的國家都難稱現代。一生奉獻于農業的著名科學家袁隆平談起城鎮化時說,他有一個更大的希望,就是將農民從土地上徹底解脫出來,“農民越少越好”。
這也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當巨量規模和驚人速度共同作用,城市與鄉村都被這一變化深刻改變時,對于桐子園來說,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村里人越來越少了。
不論是湯明孝,還是湯輝政,都不記得最后一次四兄弟團聚在父母膝下是什么時候了。“去年到得比較齊吧,就老三不在。”湯輝政說。在每年一遍遍歸家離家的輪回中,后生們越來越靠近城市。四五年前,就連過年村子也變得熱鬧不起來了。
人們一戶戶走出山村,2004年左右,湯洪濤發現,村里就連殺年豬也找不到壯勞力了。
今年40歲的湯洪濤上世紀90年代末到鄉上做生意,2000年時已經在鄉上建房定居。他的兩個兄弟都是教師,如今都在達州市生活。在出走的農家子弟中,那些擁有知識、技術和膽識的年輕人總是獲得更好的發展,而農村的優秀子弟,也是最早離開農村的。
另一個被公認的事實是,農村也確實要比以前好過多了。取消農業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義務教育全免、村村通工程、家電下鄉補貼、新農村建設……在新世紀里,國家不停地反哺農村,這里有了冰箱等電器,但真正的現代化還只單純停留在器物上,富含思想創造力的年輕人都出去了。
湯輝政對城市直觀的感受是:經濟條件要好,交通便利,老家的路連自行車都走不了,城里卻可以開摩托車。生急病了還可以叫救護車。“我想讓我的孩子在更好的環境中長大。”湯銀輝說。
可是與城市相比,桐子園依然落后,原因何在?2011年剛選上的村長寧升哲問自己,是交通不便,是底子太薄,還是領導干部不得力?環顧四周,63歲的他已經算是村里的“年輕人”了。
守望鄉土
事實上,兒女們并非沒想過把湯明孝夫婦接過去。
7月份,李仕芬經歷了一次危機,她半夜里突然中暑發作,住在雙龍鎮的湯健騎了1個小時的摩托車趕回家里,所幸沒有大礙。湯健力勸父母過去住,湯明孝卻不愿意。
“氣費、水費、電費……城市里沒經濟實力生活不了。”湯明孝現在滿足于在農村里侍弄他的果樹,種糧食、種菜、種煙葉給自己,每到雨后,他會到松林揀城里人不曾見過的菌子,給晚飯加道菜。
兒子們還在城市和鄉村間游移,既渴望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也希望家鄉能讓人安身立命。此外,他們更愿意把父母接出來,而不是自己住回去。
湯明孝心里明白,讓兒子們回到農村并不現實。數據顯示,2010年,達縣勞務輸出高達四十余萬人,相當于全縣人口的1/3,而返鄉的卻屈指可數。被監測的100家農戶中,無一人返鄉創業。
達縣地處山區,一輩輩農民在高山丘陵間開墾出一片片梯田。秋收后,梯田落下等高線般齊整的片片金黃,晴日里,朵朵白云在山間投下水墨般的影跡,風吹云動,大地上的云墨就這么團聚,洇開,消散。
那是什么時候的梯田?后生們不知道,湯明孝知道:“毛主席那時就有了啊。”如今,在梯田上勞作的還是毛主席那時的人。
山風中,何惠玲攤開手掌,秋收時鐮刀的割痕嵌滿泥土,深刻得分不清哪兒才是指關節的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