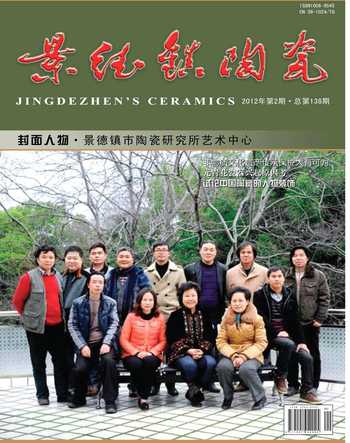元青花瓷器興起原因考
趙宏
一
有關青花瓷器的起源,歷來爭論頗多。或有觀點認為青花瓷器起源于唐代,或有觀點反對這一判斷。而人們對于青花瓷器成型和初興于元代,則是沒有異議的。
二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而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始于成吉思汗時期。成吉思汗在征服土蕃一部時,曾對藏教喇嘛表示信奉,由此他順利地征服了土蕃較大一片區域,此舉奠定了蒙古貴族與藏地貴族的密切聯系,也奠定了蒙古貴族信奉藏傳佛教的基礎。
繼成吉思汗之后,闊瑞王子實行宗教統管西藏的策略。他寫信邀請薩迦派法王薩班到涼州會晤。“薩班遂并以當時藏傳佛教各派中實力最強大的薩迦派為聯系對象。率其侄八思巴與恰那多吉前往。在這次會晤中,薩班代表西藏地方勢力與蒙古王室達成協議。從此西藏歸順了蒙古。”忽必烈繼位以后,不僅主持佛道辯論,還封八思巴為國師。
《元史·釋老傳》載:“帝師八思巴者,土蕃薩斯嘉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宇。”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領總制院事,管理佛教和藏族地區事務。至元七年(1271年)受封“大寶法王”。
在藏傳佛教修習活動的法器中,無論是佛身還是曼荼羅,本身是飾有顏色的,而且這種顏色對于佛身和曼荼羅的境界有直接的意義。法器的制作需要工藝制作的功夫,這種功夫就是要使工藝形象以及上面的色調為藏傳佛教的精神境界服務,這樣顏色本身的含義就是深刻的。
如法王周加蒼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師傳》中的詩文說:“未經多日,有一天他明顯地真實看見有一座面積適中的曼荼羅,中心的顏色如用上好的靛青涂抹而出的那樣鮮艷,而且極為瑩徹,久看不厭!壇體為圓形,周邊有如五彩虹光構成光網,在其面積適合的青色中心點上,明顯現出一尊結跏跌坐的至尊文殊(胸間現有)色如紅花的‘阿惹巴扎那咒文,久看亦不厭足。”
在元代,藏傳佛教的佛像和供器出現瓷制品,反映出蒙古族統治者為了統治漢族地區而尊重漢地文化,為了加強對西藏的統治而尊崇藏傳佛教。尊重漢地文化的表現之一,就是用瓷器這種漢族地區的傳統工藝作為宗教祭祀的供器;而瓷器作為供器所服務的宗教不是別的,是藏傳佛教。這樣藏傳佛教和瓷器就結合在一起。
青花瓷器的色調是藍色,而藍色在藏傳佛教中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善妙蓮華《西藏佛教圖像學》(以下簡稱圖像學)中說:“中國人用紅、金以示喜慶,西方倒以紅表憤怒、危險、和勇氣,又以綠表示嫉妒等。同理西藏佛教本尊之顏色變非偶定,而代表其內在本質。”關于藏傳佛教五方佛之系統,《圖像學》說:
“部剛金色藍央中
智性體界法:嗔
佛動不:蘊色
母佛在自:天空”
熊寥《元代青花瓷器裝飾》中說:“元代青花瓷器與同時代各個部類藝術相比,顯得更加不可遏制地從蒙、藏喇嘛教文化吸收營養,這里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原因:元代中前期燒造的青花瓷器,主要是為佛道供器或殉葬明器而制作的,筆者所持的這個看法,可從出土實物得以佐證,出土的元代中前期青花瓷,如元代延祜己未(公元1319年)墓出土的元青花牡丹塔蓋罐,杭州前至元13年(公元1276)墓元青花觀音塑像,江西省博物館收藏的“至元戊寅”(公元1338)款的塔四靈蓋罐和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均屬佛道器物或殉葬明器。正因為元代中前期的青花瓷的制作,大都供佛道或殉葬之用,所以它就不能作為生活用瓷和陳設用瓷投放市場,正是基于這種原因,于元代中期至順年間(公元1331——1332年)沉沒于南朝鮮海域的中國元代沉船內打撈出一萬八千多件瓷器,內中有元代全國各大窯口,唯獨不見一件青花瓷,成書于元代至冶——泰定年間的蔣祈《陶記》內,也不見青花瓷生產和銷售的記載。而元代雖然對各種教派均不歧視,但蒙藏奉行的喇嘛教卻受到極大推崇。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尊土蕃喇嘛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并命其創制蒙古文字。八思巴之后,喇嘛相繼為帝師。嗣后,歷代皇帝即位時,俱受其戒,而且后妃公主無不膜拜頂禮。既然元代中前期的青花瓷的生產,主要服務于當時的佛道及其禮儀,而元代佛道又以喇嘛教最為隆盛,那么元代青花瓷器的裝飾藝術深受喇嘛文化的影響,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元代青花瓷器中服務于佛道及其禮儀的器物,其裝飾也必然服務于佛道及其禮儀的需要。我們在這些器物上看到帶有藏族文化色彩的八吉祥紋、串珠紋、垂云紋、方形蓮瓣紋等。如至正年(1276年)制作的青花觀音像胸部飾以垂云紋,河北省保定出土的青花釉里紅鏤雕大蓋罐上以串珠組成開光形式元延右己未墓出土的青花塔蓋罐上飾蓮瓣紋、上海博物館藏青花蓮瓣紋盤上的蓮瓣紋中飾八吉祥紋。云彩在藏傳佛教中具有吉祥意義,如“云彩為衣裳發辮為佛珠”“佛陀在世上聚起教法的祥云……。”即為此意。串珠紋又稱纓絡紋,亦具有吉祥的意義,如“師之善名如美瓔,美女項飾增光榮……。”蓮瓣紋元代以前即已出現,元代時,瓷器上的蓮瓣紋開始模仿藏地佛塔須彌座上的蓮瓣紋,變形成規矩的形式。八吉祥紋,有法螺、法輪、寶傘、鐘、花、瓶、魚、盤腸組成,其形象來自藏傳佛教的法器。
上述《西藏圖像學》中鮮明地反映出五方佛系統的中央飾以藍色。藍色反映的是天空,而元代時以瓷器為祭器,以其上面的藍色裝飾來反映天空的境界,也反映的是蒙古族對于天空的觀念。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共同的自然崇拜是對于天的崇拜。如《史記》載:“其明年(孝文六年,前174年),單于遺漢書月:‘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倨傲其辭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反映出天授予單于統治人間的權力的觀念。
《蒙古秘史》中說:“奉天命而生之孛兒帖赤那。”在蒙古人的思想觀念中,“長生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原始社會中。蒙古人的“天”是被人格化了的自然事物,并不具有社會內容。到了12世紀前后,蒙古社會向封建的宗法社會過渡,“長生天”意即“永恒的天”的觀念開始深入到社會的機制中去。如“但是,當我們細心翻閱早期蒙古史料時,就會有這樣的感覺:13世紀前后的蒙古階級社會有一種極溫和的色彩,封建主同牧奴之間的關系比較緩和,乃至以兄弟,父子相稱。家中幼子繼承父親的葛爾朵,社會組織以血緣部落為單位,成吉斯汗建國后,依舊以孛兒只斤氏家族為中心(包括一些外姓勛臣),進行了領土分封,整個社會呈一金字塔形:血緣各部落——千戶——萬戶,最后達到頂端一一無上的君主,完全是家天下。事實證明,當時的蒙古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會。‘天思想在這種新形勢下,不僅未被淘汰,反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升華到鼎盛階段。”這樣,“長生天”可以支配人間的尊卑和富貴,這種支配力量是神圣不可動搖的。而在另一面,當蒙古社會動蕩,人民迫切希望統一的時候,他們便把希望寄托于某一統治者。由于統治者代表著上天的意志,因而治亂理政,處理社會尊卑富貴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于是成吉斯汗得以起家,成就統一蒙古的霸業。
忽必烈即汗位后,提出“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的理論。其“……用‘至誠一語來表達自己世界觀的核心內容,這不論是從他多年接觸漢族文化的經歷和任用眾多漢族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來看,尤其是從相似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內容來看,都可以斷定,‘至誠一語是他從子思的《中庸》篇中引為自用的。”而《中庸》中講: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這樣,藏傳佛教五方佛中心的天,與蒙古族思想觀念的“長生天”,漢地儒家文化中的“天之道”,就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融合在一起。
如“比如,忽必烈在政治上‘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民; 定法律,審刑獄”,‘妝生殺之權于朝,使‘諸侯不得而專;‘設監司,明黜陟,使‘善良奸窳可得而舉剌;‘務一萬方,嚴禁‘不隨我朝的現象存在,把全國領土完全置于中央集權制統治下加以治理,從而使我國歷史上出現了空前大統一的多民族同生共存的大元王朝……。然而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忽必烈的‘拯民‘實惠的救世主思想,是他的‘應天‘至誠觀在歷史觀上的具體反映。因此,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拯民‘實惠思想及其實踐,是他‘應天‘至誠觀的既實在又具體的‘至誠內容。所以,‘拯民‘實惠的救世主思想及其實踐的結果,當然不是其拯救民眾和給人民帶來的‘實惠本身,而是忽必烈‘欽應上天之命而成為‘實可為天下主——個統治壓迫各民族人民的封建皇帝。
如果把思想觀念和現實的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就可以明確地顯示出所謂的“天”,實際上反映的是皇權本身和中央集權的統治,而“天”的色調藍色則不過是體現這一意義的物化符號。在這一層次上講,元代青花的興起,是由于其藍色體現了皇權和中央集權的統治,因而使青花瓷器成為元、明、清時期瓷器的最重要品種。
從工藝上講,景德鎮青花瓷器受宋代吉州窯釉下彩工藝的啟發而成。如馮先銘講:“江西省宋代名窯有景德鎮和吉州兩窯,產品行銷國內各省,景德鎮晶瑩如玉的青白瓷博得假玉器的美稱。宋代兩窯產品也行銷海外,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都出土有一些景德鎮青白瓷和吉州窯玳瑁釉、剪紙貼花、剔花等黑釉瓷器及釉下彩繪瓷器。”另如清代朱琰《陶說》中說:“《矩齋雜記》: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成玉,工懼事聞于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
三
總體上講,青花瓷器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強化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和皇權統治的產物,是多民族文化交匯整合的產物,是中國古代造物方式得到升華的產物。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封建社會早已塵埃落定,但是青花瓷器卻依然流行于社會,并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志而得到多方推崇,這說明它已經脫去了自身的精神意味,而保留了審美意趣。
參考文獻:
(1)《西藏風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
(2)法王周加蒼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師傳》,青海人民出版社
(3)善妙蓮華《西藏佛教圖像學》
(4)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
(5)土觀·洛桑卻吉尼瑪《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民族出版社。
(6)《史記·匈奴列傳》。
(7)《蒙古秘史》開篇。
(8)烏恩《淺論蒙古族“長生天”思想產生及演變的根源》,巴干、趙智奎、陳紅艷編《蒙古族哲學思想史論集》,民族出版社。
(9)巴千《忽必烈“應天”“至誠”觀及其體系簡論》,巴干、趙智奎、陳紅艷編《蒙古族哲學思想史論集》,民族出版社。
(10)馮先銘《中國陶瓷考古概論》《中國古窯址瓷片展覽》,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
(11)清代朱琰《陶說》卷二《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