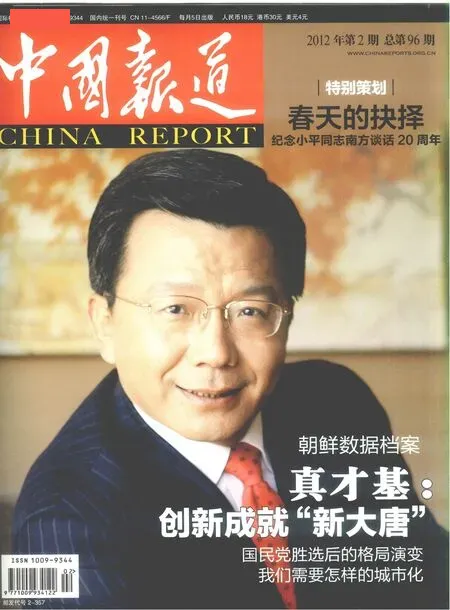來(lái)自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政治呼喚
鄭永年


無(wú)論從哪一個(gè)方面說(shuō),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無(wú)疑是當(dāng)代中國(guó)改革智慧的體現(xiàn)。如今,雖然中國(guó)面臨著一個(gè)全新的時(shí)代,依然迫切需要南方談話那樣的改革大智慧。
南方談話解決中國(guó)改革的兩個(gè)最大難題
未來(lái)的歷史會(huì)告訴人們,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中國(guó)當(dāng)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一座里程碑。我們今天所看到改革開(kāi)放的所有成果都和南方談話密切相關(guān)。
南方談話的意義在哪里?簡(jiǎn)單地說(shuō),它解決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改革所面臨的兩個(gè)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zhí)行。
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改革自20世紀(jì)70年代后期開(kāi)始,整個(gè)80年代都處于一種探索狀態(tài)。在意識(shí)形態(tài)層面,對(duì)于改革并沒(méi)有強(qiáng)有力的共識(shí),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當(dāng)時(shí)稱“商品經(jīng)濟(jì)”)之間搖擺。在路線不甚明確的情況下,執(zhí)行必然出現(xiàn)問(wèn)題。整個(gè)80年代,經(jīng)濟(jì)政策在放權(quán)和收權(quán)之間進(jìn)退。除了最初的農(nóng)村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功,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盡管都進(jìn)行了嘗試,但沒(méi)有找到一個(gè)突破口。南方談話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成為當(dāng)年召開(kāi)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第十四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的主導(dǎo)思想,這次會(huì)議上正式確立了“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概念,是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重大突破,從此,“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成為執(zhí)政黨的基本路線,并表示一百年不變。
路線確定之后,圍繞著這個(gè)目標(biāo),執(zhí)政黨很快就進(jìn)入動(dòng)員狀態(tài),集聚改革力量,實(shí)施改革政策。南方談話之后,由地方政府領(lǐng)頭發(fā)動(dòng)了一場(chǎng)激進(jìn)的分權(quán)運(yùn)動(dòng)。(盡管80年代也有分權(quán),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方談話之后的分權(quán)。)“分權(quán)”釋放出來(lái)巨大的改革和發(fā)展能量有力有效地沖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存在的經(jīng)濟(jì)和制度基礎(chǔ)。當(dāng)然,“分權(quán)”也帶來(lái)了很多問(wèn)題,但如果沒(méi)有這些問(wèn)題,舊體制還是會(huì)繼續(xù)牢固不動(dòng)。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基本制度紛紛建立起來(lái),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期之后進(jìn)行的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guó)有企業(yè)改制,盡管在執(zhí)行過(guò)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問(wèn)題,主要是國(guó)有資產(chǎn)的流失,但是沒(méi)有這一過(guò)程,國(guó)有企業(yè)根本沒(méi)有出路。經(jīng)過(guò)90年代的國(guó)有企業(yè)改制,中國(guó)基本上實(shí)現(xiàn)了一個(gè)比較平衡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即國(guó)有企業(yè)和民營(yíng)企業(yè)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chǎng)之間的平衡。與此同時(shí),在對(duì)外經(jīng)濟(jì)方面,中國(guó)成功加入了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從制度上完成了和世界經(jīng)濟(jì)的接軌。
但今天的中國(guó),在經(jīng)濟(jì)改革方面又有類(lèi)似于南方談話前出現(xiàn)的停滯不前的情況,這主要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嚴(yán)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內(nèi)需之間的失衡,國(guó)有企業(yè)和民營(yíng)企業(yè)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之間的失衡,等等,所有這些失衡的結(jié)果就是政府與市場(chǎng)之間的嚴(yán)重失衡。
而這一切的核心問(wèn)題,我認(rèn)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國(guó)有企業(yè)大擴(kuò)張?jiān)斐傻摹?/p>
再次回溯到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導(dǎo)下,中小型國(guó)有企業(yè)被民營(yíng)化或者說(shuō)中國(guó)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為企業(yè)集團(tuán),另一方面也收縮戰(zhàn)線,從一些競(jìng)爭(zhēng)性領(lǐng)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對(duì)國(guó)家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領(lǐng)域。同時(shí),國(guó)有企業(yè)的改制也比較成功,主要是企業(yè)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國(guó)有企業(yè)在改制方面沒(méi)有進(jìn)步,其市場(chǎng)化和企業(yè)化程度不足,因此它不是依靠市場(chǎng)上的競(jìng)爭(zhēng),而是通過(guò)政治和行政權(quán)力壟斷市場(chǎng)。企業(yè)發(fā)展可能已經(jīng)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機(jī)之后,國(guó)有企業(yè)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國(guó)家戰(zhàn)略領(lǐng)域,有的甚至擴(kuò)張到原來(lái)民營(yíng)企業(yè)的領(lǐng)域,造成一些不合理現(xiàn)象。
在亞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韓國(guó)、中國(guó)臺(tái)灣和中國(guó)香港都是通過(guò)政府對(duì)私營(yíng)企業(yè)的大力支持而壯大產(chǎn)業(yè)。新加坡盡管也有龐大的國(guó)有企業(yè),但是這些國(guó)企是高度企業(yè)化和市場(chǎng)化的。而中國(guó)在這方面,與這些經(jīng)濟(jì)體存在很大不同,因?yàn)檎罅χС值氖菄?guó)有企業(yè)。
但中國(guó)國(guó)企的問(wèn)題愈演愈烈,現(xiàn)在它已經(jīng)演變成為中國(guó)的“華爾街”問(wèn)題,大而不能倒,甚至挾持了政府的經(jīng)濟(jì)政策。
我一直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和美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模式是兩個(gè)極端的模式,美國(guó)是“(市)場(chǎng)內(nèi)國(guó)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國(guó)是“(政)府內(nèi)市場(chǎng)”(market in state),就是說(shuō),美國(guó)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chǎng)原則的,而中國(guó)的市場(chǎng)是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guó),如果市場(chǎng)占據(jù)了完全的主導(dǎo)地位,而政府失去對(duì)市場(chǎng)的規(guī)制,那么經(jīng)濟(jì)危機(jī)必然發(fā)生。相反,在中國(guó),如果政府占據(jù)了完全的主導(dǎo)地位,而市場(chǎng)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經(jīng)濟(jì)危機(jī)必然發(fā)生。所以說(shuō),如果美國(guó)的危機(jī)出在華爾街,那么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很可能將出在國(guó)有企業(yè)。
新時(shí)期社會(huì)改革是一條出路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guó)社會(huì)開(kāi)始大轉(zhuǎn)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合法化給中國(guó)社會(huì)創(chuàng)造了無(wú)限的經(jīng)濟(jì)空間。中國(guó)很快從一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型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成為物質(zhì)利益導(dǎo)向型社會(huì)。此后的20多年間,整個(gè)中國(guó)社會(huì)步入了一個(gè)人們所說(shuō)的物質(zhì)主義時(shí)代。隨著經(jīng)濟(jì)空間的大擴(kuò)張,各個(gè)社會(huì)群體紛紛在物質(zhì)世界領(lǐng)域里追求和滿足自身的需求。各個(gè)社會(huì)群體不可能在經(jīng)濟(jì)擴(kuò)張過(guò)程中取得同樣多的利益,于是在這一過(guò)程中出現(xiàn)了各種社會(huì)矛盾。不過(guò),有一些社會(huì)矛盾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被忽略了。
逐漸地,人們發(fā)現(xiàn)在20多年的經(jīng)濟(jì)擴(kuò)張之后,這個(gè)社會(huì)已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會(huì),就自然出現(xiàn)了各種“反現(xiàn)狀”的“理想主義”。今天,對(duì)每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來(lái)說(shuō),“理想主義”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社會(huì)形態(tài),使其適應(yīng)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這與上世紀(jì)80年代的理想主義已經(jīng)有了很大差別)。在一個(gè)高度分化的社會(huì)里,不同群體展現(xiàn)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義”。或者說(shuō),現(xiàn)在的社會(huì)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訴求,缺乏對(duì)未來(lái)的共識(shí)。
如今,中國(guó)社會(huì)再次回歸,回歸到重新確定改革共識(shí)的時(shí)期。
中國(guó)應(yīng)該把社會(huì)改革確定為執(zhí)政黨的政治路線,確定為下階段的主體性改革,并且找到政策執(zhí)行的動(dòng)力。
為什么要把社會(huì)改革界定為下一階段的主體性改革?這里有幾個(gè)主要原因。首先,通過(guò)第一階段以經(jīng)濟(jì)改革為主體的改革,中國(guó)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已經(jīng)得到確立。經(jīng)濟(jì)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間,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完善問(wèn)題。總體國(guó)家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須找到新的突破口。較之政治改革,社會(huì)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會(huì)上下容易取得共識(shí),比較容易進(jìn)行。
其次,社會(huì)改革是為了“還債”。中國(guó)社會(huì)的民怨往往是因?yàn)闆](méi)有解決好民生問(wèn)題。今天有人把毛澤東時(shí)代的社會(huì)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務(wù)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這是道德判斷而非歷史事實(shí)。應(yīng)該說(shuō),那些符合計(jì)劃經(jīng)濟(jì)模式的舊的社會(huì)體制曾在當(dāng)時(sh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它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wù)非常之少,并且分配是不公平的,因此它的解體不可避免。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伴隨著舊制度的解體,以經(jīng)濟(jì)為主體的改革理應(yīng)提供另一套完整的社會(huì)制度體系。30年來(lái)的經(jīng)濟(jì)改革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制度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會(huì)保障、醫(yī)療、教育、住房等等。而今天,通過(guò)社會(huì)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會(huì)體制是中國(guó)唯一的選擇。
再次,社會(huì)改革為可持續(xù)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尋找新的動(dòng)力,這主要表現(xiàn)為要建立一個(gè)內(nèi)需社會(huì)。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中國(guó)的開(kāi)放政策造就了中國(guó)的外向型經(jīng)濟(jì),即出口導(dǎo)向型經(jīng)濟(jì),出口成為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主要?jiǎng)恿Α?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jī)爆發(fā)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影響表明,出口導(dǎo)向型經(jīng)濟(j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的影響。很多年來(lái),中國(guó)一直面臨西方的壓力,無(wú)論是出口還是進(jìn)口,特別是金融危機(jī)爆發(fā)以來(lái),中國(guó)主要的出口市場(chǎng)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開(kāi)始盛行,盡管中國(guó)不喜歡,但這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中國(guó)的控制范圍。每當(dāng)面臨來(lái)自西方的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中國(guó)往往感到力不從心。一個(gè)高度依賴于外貿(mào)的經(jīng)濟(jì)體,其可持續(xù)發(fā)展是非常成問(wèn)題的。
走出這一困局的唯一途徑在于建立一個(gè)消費(fèi)社會(huì),依靠社會(huì)內(nèi)部的動(dòng)力來(lái)達(dá)到可持續(xù)發(fā)展。但是,消費(fèi)社會(huì)的建立需要社會(huì)制度作為基礎(chǔ),如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社會(huì)的形成,不僅取決于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過(guò)社會(huì)改革建立起來(lái)的社會(huì)制度,包括社會(huì)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和教育等方面。在中國(guó),只有當(dāng)一整套社會(huì)政策得以確立之后,消費(fèi)社會(huì)的建立才有希望。應(yīng)當(dāng)說(shuō),在這一點(diǎn)上,執(zhí)政黨和社會(huì)也已經(jīng)具有了相當(dāng)?shù)墓沧R(shí)。
中國(guó)呼喚第二次南方談話
今天的中國(guó),需要第二次南方談話來(lái)尋找改革的突破口。但關(guān)鍵的問(wèn)題是,誰(shuí)來(lái)進(jìn)行南方談話?從某種意義來(lái)說(shuō),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政治強(qiáng)人的南方談話。但今天,政治強(qiáng)人時(shí)代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新時(shí)期的改革,應(yīng)該重新確立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作為改革的主體地位。
如何確立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作為改革的主體?這就是最近這些年人們開(kāi)始討論改革“頂層設(shè)計(jì)”的原因。
“頂層設(shè)計(j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實(shí)施改革?這些問(wèn)題都需要通過(guò)“頂層設(shè)計(jì)”過(guò)程來(lái)回答。或者說(shuō),從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設(shè)計(jì),到改革政策的落實(shí),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離不開(kāi)自上而下的權(quán)力。在近現(xiàn)代國(guó)家,沒(méi)有一項(xiàng)重大的國(guó)家制度是在沒(méi)有強(qiáng)勢(shì)領(lǐng)導(dǎo)人巧妙的權(quán)力運(yùn)作下得以確立的。
但是,在中國(guó)的政治環(huán)境中,無(wú)論是改革的發(fā)動(dòng)還是改革的可持續(xù),地方和社會(huì)的動(dòng)力都非常重要。一旦忽視地方和社會(huì)的力量,任何形式的“頂層設(shè)計(jì)”都將是空中樓閣。
改革動(dòng)力從何而來(lái)?首先就要從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中尋找。這幾乎是中國(guó)改革的定律。中國(guó)的改革往往首先是從地方開(kāi)始的,在各個(gè)地方實(shí)踐,然后通過(guò)“頂層設(shè)計(jì)”,把地方經(jīng)驗(yàn)提升成為國(guó)家政策,推廣到全國(guó)。
這些年來(lái),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試驗(yàn)一直在進(jìn)行,如浙江的政府鼓勵(lì)民營(yíng)企業(yè)發(fā)展的模式;廣東的外向型企業(yè)的轉(zhuǎn)型和公民社會(huì)建設(shè)模式;重慶的國(guó)家動(dòng)員模式;江蘇的政治改革模式(“公推直選”)等等。這些地方的領(lǐng)導(dǎo)層面對(duì)各自現(xiàn)實(shí)尋找著適合自己情況的改革和發(fā)展模式。事實(shí)表明,如果能夠充分授權(quán)于地方,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是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
除了地方政府層面,改革更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社會(huì)的參與。沒(méi)有社會(huì)的參與,“頂層設(shè)計(jì)”不可能科學(xué)。在改革領(lǐng)域,無(wú)論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政治改革,其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都是社會(huì)。如果沒(méi)有社會(huì)的參與,很多決策在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理性和科學(xué),但實(shí)際上卻脫離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并不能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需求,最終可能流于空想。
頂層設(shè)計(jì)也必須滿足中國(guó)社會(huì)日益增長(zhǎng)的參與要求。改革開(kāi)放之后,中國(guó)的社會(huì)力量已經(jīng)得到很快的發(fā)展。一部分人在解決了溫飽問(wèn)題而躍升為中產(chǎn)階層之后,就開(kāi)始萌發(fā)政治參與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處于比較貧窮狀態(tài)的人,因?yàn)榈却嗄瓴荒芨淖冞@種狀態(tài),也在逐漸激進(jìn)化,當(dāng)然也希望通過(guò)政治參與來(lái)追求基本的社會(huì)公平和正義。如果不能滿足社會(huì)參與的要求,經(jīng)過(guò)“頂層設(shè)計(jì)”的政策很難具備較高程度的社會(huì)合法性。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huì)參與可以影響目前的中央和地方關(guān)系。中國(guó)各地地方差異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個(gè)地方實(shí)施,這就給地方政府創(chuàng)造了去實(shí)踐各種地方改革的客觀條件。但在沒(méi)有社會(huì)監(jiān)督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的改革有可能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只是為了自己的個(gè)人前途而改(在現(xiàn)有體制下,這種情況很容易發(fā)生)。而社會(huì)的廣泛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會(huì)迫使地方官員必須從長(zhǎng)遠(yuǎn)的利益出發(fā),而非為短期個(gè)人利益所驅(qū)使。同樣重要的是,社會(huì)參與可以解決地方官員的權(quán)力制約問(wèn)題。中國(guó)目前的情況是,隨著黨內(nèi)民主的實(shí)施,中央層面領(lǐng)導(dǎo)人所受到的制約越來(lái)越多,但地方仍然沒(méi)有發(fā)展出有效的制約機(jī)制。
今天的時(shí)代呼喚執(zhí)政黨領(lǐng)導(dǎo)集體來(lái)一次集體南方談話。只有改革,才能拯救改革,拯救社會(huì)。在紀(jì)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的今天,人們期待著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能夠再次尋找到改革靈魂,把中國(guó)的改革事業(yè)推到下一個(gè)階段,以實(shí)現(xiàn)執(zhí)政黨“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理想目標(biāo)。
本文為作者2012年1月8日在《東方論壇2012:改革的智慧》(北京)上所作的演講。作者授權(quán)本刊刊登。刊登時(shí)有刪節(jié),小標(biāo)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