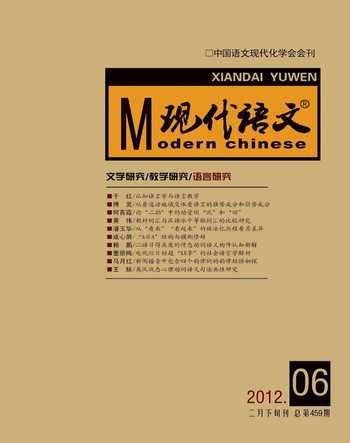概說語言哲學視域下的意義理論主潮
摘 要:哲學的語言轉向使意義問題成為哲學研究的主題。語言哲學家們發展出一些影響較大的意義理論。這些意義理論主要包括意義的對象說,意義的真理說和意義的意向說。雖然這些理論都把意義歸結為某種東西,但是理論家們依然贊同意義的整體觀。
關鍵詞:意義意義的對象說意義的真理說意義的意向說整體觀
隨著20世紀哲學的第二次轉向,語言問題成為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哲學從發問“實在是什么”,到“人的認識能力如何”,再到“哲學命題有意義嗎”,已經走過了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語言的過程。哲學要把握的是人的理性和思想,而思想唯有通過語言來傳達,因此研究語言本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而轉向之后的哲學主要關心的是語言的意義問題,因為哲學家普遍認為“哲學不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體系……就是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科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理性,哲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1]。由于轉向之后的哲學家們紛紛就意義問題展開討論,從而發展出了一些較為精致的意義理論。
一、意義的對象說
“意義的對象說”是與“語言的特征和功用是再現世界”,與“語詞的功用是代表事物”這樣的觀點緊密相聯系的,這種理論也被稱作意義的指示論(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denote”作為一個邏輯術語,既有“指示”也有“代表”的意思。一個語詞自有其含義,賴此含義可以確定它所代表的一個或一類對象。因此,符號既有內涵(connotation),又有外延(denotation)。從這一對概念具有相同的詞根可知,“指示”表明了含義與對象之間的關系,表明了從詞義向對象的運動,表明符號的意義就是它所代表的對象。
最早提出這種理論的是弗雷格。弗雷格的哲學出發點是要建構一種適合于數學科學的符號語言,在此過程中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邏輯中“等同”概念的含義,而它的主要內容則是探討語句的指稱問題。“等同”到底是符號之間的關系,還是符號所代表的對象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a=b”這個表達式中,是指兩個符號相等,還是兩個符號所指對象相等?如果它表示的僅是符號之間的關系,那么a與b之間的關系就是任意的,我們也因此得不到任何實際的知識。若表示的是對象之間的關系,那么a與b就是同一個東西,“a=b”表示的不過是一個對象與自身的同一,這就具有了認識上的價值。例如,說“晨星即暮星”,表示的是天文學中的一大發現。弗雷格認為,僅僅符號之間的等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沒有認識上的價值;只有符號所代表的對象之間的等同才有意義,因為它有認識上的價值。符號的意義在于它所代表的對象。[2]
這一理論的另一個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早期的羅素。在他早期的著作《意義和真理的探究》中,羅素認為,“在句子的結構和句子推斷的事實的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可以發現的關系。我并不認為言辭之外的事實的結構是全然不可知的,我相信,只要充分注意,語言的性質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結構。”[3]而在另一本較早的書中,他也提到,“所有的語詞作為代表自身以外的某種東西的符號,在這種簡單的意義上它們是有意義的。”[4]羅素顯然認為,語詞的意義就是它所指示的對象。后來羅素又把自己的理論更加精致化,他認為以前的所謂指示語詞過于籠統,他于是又將其細分為專名(proper name)和摹狀詞(description)兩類。專名直接指稱一個對象,該對象就是該專名的意義。該專名不需要憑借其他語詞而僅憑自身就有這種意義。如果一個名稱沒有所指,那么它在命題中就是無意義的。摹狀詞卻沒有這類限制,它的意義由組成該摹狀詞的語詞的意義決定。由此看來,專名最符合意義的指示論,因為專名除了指示或代表某個特定的對象之外沒有別的功能。有一個專名“亞歷山大”,其前提是歷史上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的人。
有一種方法可以最直接、最簡單而又最天然建立起專名和對象之間的聯系,這就是實指定義(ostensive definition)法。例如,當你說“亞歷山大”而別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時,你可以指著亞歷山大的畫像說:“這就是他”。
維特根斯坦早期也持這種意義的指示論。維特根斯坦在他前期的著名論著《邏輯哲學論》中就曾斷言“語句是現實的圖像”,“名稱意指對象。對象就是它的意義”[5]。他認為語言之所以能夠描繪現實,乃是因為它們之間必定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即邏輯形式。語言對于現實的表現或描畫,不像照片、寫生或素描與景物的關系,而是邏輯上一一對應的關系。“世界是事實的總和”[6],事實中最簡單的一種叫做原子事實。這些原子事實彼此獨立,從一個原子事實推論不出另一個原子事實。與原子事實相對應的是原子命題或基本命題,它們描繪原子事實的存在與否。與原子事實相對應,這些原子命題也是彼此獨立的,即不能從一個原子命題推論出另一個原子命題。
“意義的對象說”遭到后來許多理論家的詰難,比如,如果語詞的意義就是它的對象,連詞“而且”“如果……那么”的對象是什么呢?針對這種詰難,前述幾位哲學家都對這種理論做出了某些修改,他們都不再堅持以所指對象來說明語詞的意義,而代之以語詞和對象之間的關系。
二、意義的真理說
哲學轉向之后形成的第二大意義理論是所謂的真值條件論或意義的真理論。真值條件論者把語句的意義和語句的真假相聯系,并以后者來說明前者。
最早提出這種理論的哲學家是弗雷格。弗雷格開始時使用“符號和對象”來說明“等同”關系,但是他后來發現要想說明符號與對象之間的聯系卻非常困難,于是,他便把符號又細分為涵義和指稱,從而從符號內部來說明語詞和語詞所代表的對象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符號不僅有被命名的對象,而且還有它的涵義,涵義中包含了符號出現的方式和語境,包含了辨識所指對象的方式。當兩個符號有相同的所指對象時,由于二者的涵義不同,即認識這個對象的過程和方式不同,所以兩個符號的相等具有認識上的價值。弗雷格還用這對概念來探討語句的涵義和指稱。語句的涵義就是它所表達的思想,這里的思想指的是可為人人所理解的思維的客觀內容。而語句的指稱,弗雷格認為就是語句的真值,即語句要么為真,要么為假的情況,而語句的意義則在于它是一個真命題。
塔爾斯基在其“真理的語義學概念和語義學的基礎”等文章中試圖找到一個符合亞里士多德古典真理概念的,在實質上適當,在形式上正確的關于真理的定義。“滿足”這個定義的核心概念,就是滿足數學上的條件。這個概念把語言表達式和世界上的事物聯系起來:語句若被一切對象滿足則為真,若相反則為假。塔爾斯基找到的這種實質上適當、形式上正確的真理的表達式為:
(T)X是真的,當且僅當P。
塔爾斯基稱此表達式為“T慣例”,這實際上是一個符合要求的關于真理的語義學圖式。式中P是任何一個語句,而X則是該語句的稱呼,或對它的描述。這個語句具有遞歸性質,它開始規定最簡單的語句函項如何才算被滿足,然后說明滿足復合函項的條件,最后自動地滿足不包含自由變量的語句函項,因此,它適用于一切語句。例如,把“雪是白的”這個語句套入“T慣例”就成了:語句“雪是白的”為真,當且僅當雪是白的。
戴維森就這種真理的語義學定義給出如下的評論:
不必隱瞞塔爾斯基已經說明了如何構造出來的那一類真理定義與意義概念之間的明顯聯系。這種聯系就是:那種定義通過對每個語句的真實性給出充分必要條件而起作用,而給出真值條件也正是給出語句意義的一種方式。知道一種語言的關于真理的語義學概念,便是知道一個語句(任何一個語句)為真是怎么一回事,而這就等于理解了這種語言。[7]
戴維森在塔爾斯基奠定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了自己的意義理論。戴維森的觀點是這樣的:首先,一種適當的意義理論必須能夠推行出一切如下形式的語句:
s意謂m(s means m)
式中“s”是對于語句結構的描述,“m”是指稱該語句的意義的單稱詞項。
通觀自弗雷格以來的幾種主要意義理論,戴維森看到,無論是把語詞的意義當成某種實體,還是把語句的意義當成真值,以及把語句的意義當成語詞意義的函項,都是不成功的嘗試。因此,必須找到另外的東西代替指稱意義的單稱詞項m,它的辦法是用一個語句p來代替,于是上式便成為:
s意謂p(s means that p)
蒯因之對“意義”概念的批評,尤其是他認為“意謂”概念只會把人引向歧途,從而更青睞于外延性的指稱概念的看法,使戴維森認識到上述表達式中的“意謂”必須找到某種東西來代替。他的想法是:“作為最后一個大膽步驟,讓我們嘗試以外延的方式處理由‘p所占據的位置:為了做到這一點,就要拋棄難解的‘意謂,向替代p的語句提供一個恰當的關聯詞,而向替代‘s的描述語提供它自己的謂詞。看來合理的結果便是:
(T)s是t當且僅當p”[7]
式中“t”是任一謂詞,不論對“是t”加以明確定義還是用遞歸的方式描述其特征,它所使用的語句顯然恰恰是我們討論意義理論所適合的語言中的真語句,因此上式可轉換為在形式上和T慣例相同的表達式:
(T)S是真的,當且僅當P
戴維森指出,這里重要之點并不在于真理概念,他的貢獻在于他提出以下觀點:一種適當的意義理論必須描述符合某些條件的謂詞的特征,而這樣一種謂詞恰恰適用于真語句。
戴維森的以上理論用一句話總結就是:語句的意義是由這些語句真值條件給出的,這就是戴維森著名的意義真理論(truth theory of meaning)。對于這種意義理論,有一些批評意見值得反思。第一,戴維森的意義理論預設了一個前提:任何語句都有其真值條件,這一點顯然大有問題;第二,一般來說,人們總是先把握語句的意義,然后才把握其真值條件,因為語句的意義可以僅憑語句本身而獲得,語句的真值條件與外界事物有關,戴維森把意義與真值條件的關系顛倒過來,顯然讓人難以接受。
三、意義的意向說
意義一旦涉及到人,就必然涉及到人使用語言時必不可少、最具特征性的現象——意向性作用。意義的意向說開始于胡塞爾。胡塞爾認為,在意識賦予意義的活動之前,語言符號不過是一些任意的、只具有物理特性的聲音或墨跡。表達式的意義來自人的意識的意向性,實際就是意識對于對象的念及。意向性的含義是:第一,意識總是關涉于某物的意識,它總是“意指”著某物;第二,意向性就是“思”,而“思”總是有它的“所思”,即以經驗、思維、情感、意愿等的方式“意識地擁有某物”[8]。胡塞爾后來又通過他的兩種現象學還原達到了意義的根源之所在:本質還原從對象方面排除掉事實,只剩下本質,從而顯露出了意義的“客觀”根源之所在;先驗還原從主體方面排除掉經驗自我及其個別體驗,只剩下先驗自我及其我思,從而顯露出意義的“主觀”根源之所在。
胡塞爾的“意向說”表現在文學理論領域,是把文本的意義看作是作者的意向或意圖。“講話者的意義不僅為他所敘說的內容,而且也為他發揮作用的意圖所決定。這樣,詩人或作者的意圖便顯得是解釋學文本意義的天然基礎”[9],“在對文學作品意義的陳述和對作者意圖的陳述之間存在著邏輯聯系,而作品的意義亦即作者意圖的陳述”[10]。
而轉向后的分析哲學受到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即其用法的思想和胡塞爾意義意向理論的雙重影響,開始把語言當成是一種行為,而言語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講話者的意圖,以及所欲達到的目的。因此,研究講話者的意向便成了更進一步研究言語行為的課題。格耐斯是這一理論的重要代表。格耐斯主要研究意向在表達意義中的作用,他認為,說話者A用語言表達或X來意指某物或某事的條件是,A必須有這樣的意向,他用X在聽話者那里造成一種信念,同時,他還必須有意使聽話者被人承認受到了他的意向的作用或驅使。他的觀點可總結如下:
1.“A以X意指某事”大體相當于“A有意使說出X在聽話者那里由于意識到他說話的意圖而產生某種效果”,問A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求對他意欲達到的效果做出什么;
2.“X意指某事”大致相當于“某人以X來意指某事”;
3.“X無時間性地意指如此這般的情況”等于關于人們以X意欲此效果的陳述或陳述的析取。[11]
格耐斯為了完善自己的意義意向理論,他把意義分為四種,其中最基本的叫做講話者的情景意義(utterers occasion-meaning)。他認為,講話者的情景意義可用講話者的意圖來說明。他對“講話者說出X意指某事”為真所下的定義是:
當且僅當對于某個聽話人,講話人說出X意欲:
1.使聽話人產生一特定反應r;
2.聽話人應認識到講話人的意圖如上;
3.聽話人要在滿足第2項的基礎上滿足第1項。[12]
后來的斯特勞森調和了格耐斯的意義意向理論和戴維森的意義真理論,他認為,一方面,要知道語句的意義就是要知道該語句在什么條件下為真,因此意義和真理相關;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對于講話者而言,說某事為真就是意指某事,因而真陳述這個概念必須以講話者意指什么來分析。
塞爾繼承并發展了格耐斯的理論,他承認講話者的意圖是他的話語意義的重要因素,但他認為,意圖還應當和使用語言的規則和習俗相結合。塞爾設想了一個講話者的意圖和語言習俗相脫節的例子。
假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軍隊俘虜了一名美國士兵,這個美軍士兵想讓意大利人以為自己是德國人以便逃脫,他于是就決定說德語,并且寄希望于意大利士兵不懂德語上。這個美軍士兵中學曾學過德語,但現在都記不得了,他只記得一句德文詩,他于是就把這首詩背了出來。照格耐斯的定義,這個美國士兵想制造意大利人以為他在講德語從而是德國人的效果,而且他有意讓他們認識到他想用德語說出什么來達到效果。這個美軍士兵吟誦的這句詩是“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en?”(“你可知道那一片土地,檸檬樹正花繁葉茂?”)然而這句詩的意義是不是“我是德國士兵”?很顯然,我們不能做如是解。
因此,當一個人使用語言傳達某種意義時,他不僅有達到某種目的的意圖,不僅要讓聽話者感覺到他欲達到的目的,而且他選擇的語言表達式應該以某種方式和他的意向一致,也就是說,他必須遵守規則和習俗。塞爾最后總結說,只有意向和習俗兩者的結合,才能對言語行為所欲傳達的意義作出說明。[13]
四、結語
雖然以上各種意義理論要么把意義歸結為對象,要么歸結為真理或人的意圖,也就是說,這些理論好像各自把詞和句子的意義歸結為某種東西,但是這并不表明這些理論就是意義的原子論,持有它們的理論家也不是意義的原子論者。相反,在意義問題上,無論英美分析哲學家,還是歐陸現象學和解釋學哲學家,他們都支持一種關于語言意義的整體觀。他們的總原則是:不能孤立地尋問一個詞的意義,而要在整個語句中確定它的意義。因此,小到字詞、文學作品的意義,大到文化現象、歷史事件,都必須把它們放回到它們所從出的整個文本以及時代背景和社會語境中去理解,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較準確的意義。
注釋:
[1][德]石里克.哲學的轉變[A].洪謙.邏輯經驗主義[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2][德]弗雷格.論涵義和指稱[A].涂紀亮.語言哲學名著選集[C].北京:三聯書店,1988.
[3]Bertrand Russell.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M].London: Allen,1951.
[4]Bertrand Russell.The Principle of Mathe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3.
[5]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London: Routledge,1992.
[6]Ibid.p.31.
[7][美]塔爾斯基.真理的語義學概念和語義學的基礎[A].涂紀亮.語言哲學名著選集[C].北京:三聯書店,1988.
[8][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張慶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9][美]霍伊.闡釋學與文學[M].張弘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10][美]卻爾.解釋:文學批評的哲學[M].吳啟之,顧洪浩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11]Grice.meaning[A].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9.
[12]Grice.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sions[A].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13]Searle.What is a Speech Act?[A].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王軍偉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65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