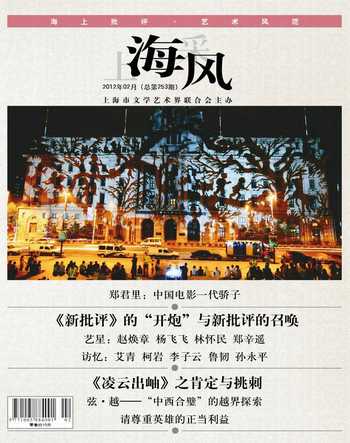咱們的“魯馬列”
陳清泉
1973年秋末冬初,我擔任了于炳坤同志的新作《飛雪迎春》的責任編輯。
于炳坤曾與朱道南合作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大浪淘沙》,并拍成了影片。由他自己來改編自己的小說將會事半功倍,所以廠部對這個劇本的創作前景十分樂觀,在劇本階段就明確了由魯韌來擔任此片的導演,并安排了上海電影專科學校畢業的高材生徐偉杰當魯導的助手。
魯韌曾經導演了膾炙人口的《今天我休息》《李雙雙》以及《猛河的黎明》《洞簫橫吹》等影片,是我心儀已久的一位名導演,但他容易合作嗎?對我們這些“后生小子”處得來嗎?
時間緊迫,廠里要我陪著魯韌趕赴銅陵,與先期到達的于炳坤等會合,一起深入生活,創作劇本。
前去銅陵沒有臥鋪,車票又難買,只買到不對號的站票,怎么辦?他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又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與我一起軋這趟火車,行嗎?我把這些顧慮坦率地對他說了后,他竟笑嘻嘻地講開了:“怎么,不相信我這個老頭子?論體力,你這個小伙子恐怕不如我哩!軋火車,算得了什么!”
于是,我們早早到了車站,因為沒有座位只好站在車廂的走道上。我看著他這樣子,內心十分歉疚,剛想開口說話,他卻對我擠擠眼睛:“怕我站不動?說不定你趴下了我還站得筆挺哩!”這一句說得很輕松的打趣話,將我的不安驅散了很多。
我們這個集體,有好幾位如徐偉杰、陸壽鈞等方三十出頭,我則年逾四十,而魯導已是六十開外了。本來以為,在銅陵的生活是很刻板的,但由于有魯韌在,他又是沒有架子的人,和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時,常常說說笑笑、嘻嘻哈哈,所以近兩個月的銅陵深入生活,可用輕松而又愉快來形容。
魯韌是一位很透明的人,對自己的經歷包括戀愛經過,都會“無遮攔”地“漏”出來。他的經歷豐富,肚子里有很多故事,常常在大家入睡之前,請他吹“山海經”,對我們的提問,他也是有問必答,從不遮遮掩掩。
他出生在一個很有錢的“大戶人家”,從小嬌生慣養,漸漸長大后,他不滿那個醉生夢死的環境,希望通過進步戲劇活動批判那個舊社會。他說:“我能夠下決心離開那個家庭,已經夠進步的了,不是嗎?”我們則沒大沒小地:“別自我吹噓了,大少爺!”其實心里還是稱贊他很不容易。
他離開家庭到了北平,進了中國大學英文系。這時候,他已經與戲劇難解難分了。在中國大學,他先后組織了“三三劇社”、“矛盾劇社”,并參加了左翼戲劇家聯盟。說到這里,他有點志滿意得了,提高了嗓門說:“那個時候,在北平的戲劇界,誰不知道我吳博呀!”
據他自己說,他很佩服魯迅,贊揚他的韌性戰斗精神,所以放棄原名,改稱魯韌。
我們幾個年輕人起哄:“我們怎么不知道有個吳博呀!”
他知道我們“不懷好意”,便以調侃對調侃:“那時候呀,你們還沒生出娘肚子哩,能聽到這名字嗎?”
魯韌說他能夠在戲劇界站住腳,首先是因為自己有“頑藝兒”,但也得益于經濟上有后臺——家里有錢供自己花。他不抽煙、不賭錢、不進聲色犬馬的場所,讓他把錢花在搞戲劇、搞藝術上家里是不反對的!他強調說:“如果沒有一點經濟來源,那時候要搞戲談何容易,哪像現在有政府支持呀!當初的我,可是賠了錢來搞戲的。”那時候的人,像顧而已、趙丹他們,也都是在家里的經濟支持下搞戲劇運動的。
我們這班小家伙,總想抓機會“攻擊”他,這一來,就給我們話把兒了。于是,有的說:“誰叫你是公子哥兒呢?賠點錢,那是應該的。”有的說:“大少爺搞戲,得花大洋!”就這么不分長幼尊卑地,開開心心地與他相處著。
我早就聽說,他有個外號,叫“魯馬列”。
有人說,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魯韌常用的一句話就是“馬克思、列寧教導我們”,以此為據地闡述自己的想法,對照知識分子的“弱點”,說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后來人們以“魯馬列”來贊揚他言必稱“馬列”,這分明是褒義。
也有人說,魯韌有時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引用馬克思怎么說、列寧怎么說,人們認為他生搬硬套,有點教條,所以挖苦他,起了這么個外號,這又有點貶義了。
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便想當面問他這“魯馬列”的來歷,但又怕他“多心”,常常把想說的話強咽了回去。
一天,正好沒有旁人在場,我便趁機提出這個問題:“人家叫你魯馬列,怎么回事?”說完,我又覺得唐突了。
他并不在意,只是笑著用手指點了點我的額頭,接著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在大學時代,曾經偷偷讀過幾本馬列著作。解放以后,為了追求真理、趕上時代的步伐,確實認真地讀過馬列原著,他們講的道理很深刻,確實可以指導我們這些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做人、行事。所以,我喜歡引用馬列的話,有時候也難免詞意相斥,人家說我教條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我的馬列水平很低,這外號有點埋汰人哩!你知道,我至今還沒入黨呢!”他這番話讓我肅然起敬起來,一位老知識分子,為了適應新的時代,企求以馬列原理來指導自己的言行,當然是無可厚非的。
在銅陵的日子里,我們常常要下井,并且一直走到“掌子面”與礦工一起采掘。一次在鳳凰山銅硫礦,貫籠(即運載工人垂直下井的電動梯)剛到井口,他就搶在我們前面竄了上去。我便趁機調侃他:“身手不凡嘛。”他瞪了我一眼:“不服氣?我的‘不凡多著呢。”
果然,過了沒幾天,我就親身體驗到他的不凡。
我發了燒,顯然是著了涼。他命令我:“躺下!”
我很不情愿地躺了下來,心想,老先生又耍什么花招呢?平時,我們逗他,他也會尋機報復你一下的。他是否要借機“整”我呢?
他卻一臉嚴肅:“別動,聽話,讓我來給你瞧瞧……”
“你瞧瞧?!”我更加狐疑了。只見他從懷里掏出一包東西,在我面前晃了一晃。
我有點詫異,又有些緊張,便挺起身子問:“你要干什么?”也有人起哄:“手上拿的什么法寶?”
他打開布包,把手中東西一亮:“法寶,真的是法寶,治病的法寶……”我這才看清楚,原來是閃閃發光的一把銀針。我說:“你別是蒙古大夫吧……”他則回敬我:“還敢調皮,再調皮看我怎么收拾你!”不容我分說,就扎了我三針。
在他的治療下,感冒很快就好了。我問他:“從哪兒學的?”他告訴我,年輕的時候,對什么都感興趣,曾在天津與北平觀察針灸醫生給人扎針,還買到一個標明人身穴位的銅人,把病癥與對應的穴位記下來,慢慢地掌握了這門技藝。他說到得意處,不僅眉飛色舞,還伴之以手舞足蹈,又不經意“漏”出了一些扎針“軼事”——
在《猛河的黎明》拍攝外景期間,不少人因水土不服,不適應南方氣候等原因生了病,攝制組因此而停了工。這位魯導演把所有生了病的人集中在一起,讓他們挨個兒躺下,一個一個地用他手中的銀針扎過去,只一兩天功夫,他們都神氣活現了。說到這里,他又加強語調說:“連制片主任也對我感激不盡,因為我出手不凡,才沒耽誤拍片子呢!”
他的話,讓大家聽得一愣一愣的——老頭兒的招兒還真不少呢,他明顯看出了大家的反應,又賣關子地:“我的絕招還沒說呢,要聽嗎……”
大家故意地:“要講就講,不講拉倒。”
他眨了眨眼睛,問:“要過年了,想家嗎?”見大家沒有答話,“哪個想家,我給治——我專治想家、想老婆的病。”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他“老不正經”,“你才想老婆哩!”他不動聲色地:“要不要聽我怎么治的?”接著就說開了。
“還是《猛河的黎明》拍外景時,眼看就要過年了,大家心有點散了。我一看苗頭不對,讓這些小伙子們(多數是照明組的)躺成一排,然后在他們臍下三寸的地方就一針下去,然后一個一個捻過去,捻得大家把那個想家的念頭控制住了,你們信不信。”
突然,他抓住我說:“不信,你試試。”我當然不會讓他扎一針,便掙扎著逃開了。
這么一位很有成就的導演,居然和我們這些“毛頭小伙”打成一片,當我回憶這些往事時,他那一口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他那在慈祥中又包含著“童真”的笑容,他那句十分自豪的“出手不凡”,又回到我的耳畔和眼前。
熱烈而執著地追求馬列、追求中國共產黨的魯韌,終于在晚年實現了他的夙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與他相處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一位嚴謹地對待藝術創作的老藝術家的另一面,即他在待人接物、人品風范的許多側面,這也是人們喜歡他、尊重他,至今仍然懷念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