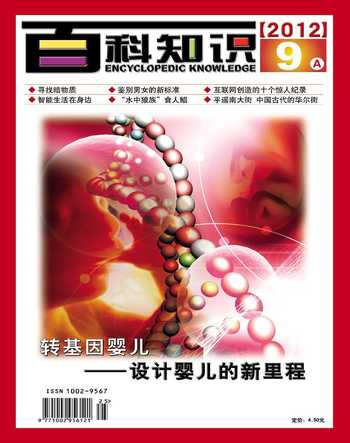世界各地的童子軍
王江波

2012年7月10日,總部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對今年3月已經核定罪名的剛果(金)武裝組織“剛果愛國者聯盟”領導人托馬斯·魯邦加判處有期徒刑14年。與2009年以涉嫌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為由,正式對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的行為相比,國際刑事法院這一次是動“真格”的了。這是國際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有罪判決,而這一切則源于魯邦加征募童子軍,躲藏在這背后的童子軍與世界和平與安全有著怎樣的聯系?
童子軍誘發的“十年首判”
1998年7月17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以下簡稱《羅馬規約》)在意大利羅馬全權外交官大會上順利通過。2002年7月1日,《羅馬規約》正式生效,國際刑事法院也在當天正式成立。作為世界上追究個人犯有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滅絕種族罪和侵略罪的常設司法機構,10年來一直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行”。對剛果(金)武裝組織“剛果愛國者聯盟”領導人托馬斯·魯邦加判處有期徒刑14年的舉措成為國際刑事法院10年以來的首次有罪判決,雖然有輿論質疑其量刑過輕,但從營造輿論壓力、懲戒和威懾犯有更嚴重罪行的人等方面來說卻意義深遠。
導致“十年首判”的罪名是征募童子軍,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確定有充足證據證明,在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剛果伊圖里地區部族沖突期間,魯邦加因其部隊招募不足15歲的童兵入伍,把他們作為刺殺、搶劫和強奸的工具從而被認定犯有戰爭罪。
在確定國際刑事法院認定的罪名之前,有必要先分析國際刑事法院對魯邦加案件的可受理性。根據《羅馬規約》第17條第1款的規定,特別是第1款第4項關于罪行嚴重程度的考慮,應該是國際刑事法院決定是否對魯邦加案件進一步采取行動的關鍵前提條件。因為,根據《羅馬規約》第17條第1款第4項的規定,如果“案件缺乏足夠的嚴重程度,本法院無采取進一步行動的充分理由”,而對這個條件的衡量又取決于審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是否是有系統的或者大規模的。經過對案件事實的審查,對國際刑事法院可受理性的回答是肯定的。
根據《羅馬規約》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對戰爭罪具有管轄權,特別是對作為一項計劃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實施的行為,或在大規模實施這些犯罪中所實施的行為。魯邦加被控自2002年9月以來,在民主剛果領域內實施了《羅馬規約》第8條規定的戰爭罪——招募兒童兵。據報道,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間,大約800名平民被愛國者聯盟殺害;在2003年2月18日~3月3日,“剛果愛國者聯盟”在某一地區摧毀了26個村莊,殺害了350多人,迫使6萬人背井離鄉;自從2004年12月開始,超過10萬平民被迫轉移。魯邦加發布命令,要求居住在他管制之下的所有家庭有嚴格的義務向其交納牛和錢甚至兒童以支持戰爭成功,10歲~16歲的兒童被編入其軍事力量。其行為已構成《羅馬規約》第8條第2款第5項規定的“嚴重違反國際法既定范圍內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法規和慣例的其他行為,即下列任何一種行為:(7)征募不滿15歲的兒童加入武裝部隊或集團,或利用他們積極參加敵對行動。”基于國際刑事法院的可受理性和確有證據證明魯邦加犯有戰爭罪,國際刑事法院有權認定魯邦加犯有戰爭罪并對其判刑。
童子軍的現狀與復雜成因
在歷史的長河里,未成年人參加戰爭的最早記錄是在中世紀前的古代,在地中海流域未成年人作為成年武士的助手、駕駛馬車者和盔甲持有人參加戰爭。歐洲在中世紀封建與宗教戰爭的時期,亦有兒童參加戰爭的記錄。社會歷史的發展并沒有根除童子軍這一社會現象,反而在全世界范圍內有愈演愈烈之勢。
聯合國的評估報告表明,目前全世界至少有30萬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參與了世界各地30多場武裝沖突,幾乎占了全球沖突交戰方士兵總人數的1/4,大部分是作為士兵直接參與,同時還擔負其他職能,如間諜、信使、運輸員、性奴隸等。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童子軍現象最嚴重的是緬甸,目前有大約7.5萬名童子軍,其次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哥倫比亞、利比里亞和安哥拉等國,分別有3萬、1.6萬、1.5萬和1.1萬童子軍。此外,北愛爾蘭、以色列、巴勒斯坦、尼泊爾、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也有大批未成年人被征為童子軍。童子軍的現象并不僅僅存在于戰火紛飛的落后國家和地區,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存在童子軍現象。2001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魔鬼營”接受童子軍訓練的人數就達到1.4萬多名,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中,美國也有使用童子軍的現象。
時值21世紀的今天,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并沒有根除童子軍這一世界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根除童子軍產生的根源,童子軍的產生是一系列綜合因素的結果。
戰爭無疑是童子軍產生的核心根源。二戰結束后,世界維持著相對和平的狀態,沒有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局部戰爭和沖突不斷,世界各地爆發的戰爭多達180場,有戰爭就有殺戮,有戰爭就有士兵的需求,在兵源短缺的情況下,童子軍便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戰爭帶來的巨大破壞往往也成為童子軍產生的一個誘因,連年內戰使得許多兒童失去家庭成了孤兒,饑餓、無家可歸等因素的存在迫使他們加入童子軍,因為對他們而言,加入童子軍就意味著食物和“家”。據NHK紀錄片《非洲童子軍誕生起源——莫桑比克內戰的惡果》稱,非洲童子軍起源于莫桑比克內戰,1975年獨立之后的15年內戰造成10萬人喪生,300萬人背井離鄉,150萬難民流落他國,自此,童子軍便在非洲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
國際公約的約束力相對缺失容易導致對童子軍組織者懲罰不嚴,也使得許多童子軍組織者鋌而走險。
童子軍自身的特殊性也往往容易被組織者所利用。根據政治心理學“政治人格”理論表明,兒童的性格可塑性最強,青少年時期是兒童性格的形成時期。此時,只要稍加利用便可形成未來穩定的政治人格。長期的內戰生活環境和組織者的威逼利誘往往容易導致兒童被洗腦,從而堅定地成為一名童子軍。同時在不對稱戰爭中,童子軍的相對可獲得性和可塑造性使得許多童子軍組織者往往傾向于選擇兒童作為士兵后備資源。同樣,利用對手對童子軍的憐憫心理也是考慮之一,許多美國軍官表示,在與童子軍對抗時,官兵們會產生道德和心理緊張情緒,指揮官們則負有嚴重的道德責任感。
多管齊下的治理策略
縱覽現代國際舞臺,童子軍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兒童權益的保護理應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對童子軍的治理已經刻不容緩。
戰爭和沖突是制造童子軍的“機器”,只要內戰不止,童子軍現象就不會結束。童子軍現象的解決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如何消除內戰,內戰的消除在于消弭引起沖突的原因,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源上解決童子軍問題。
童子軍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因此需要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減少乃至杜絕這一現象。2007年2月在法國首都巴黎簽訂的《巴黎承諾》是國際社會對阻止征募和使用童兵的最新舉措,此外《<兒童權利公約>的有關兒童參與武裝沖突的選擇性議定書》、《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條約也都對兒童權利的保護做了相關規定,但是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使得國際條約并不具備強制執行力,因而議定書的切實遵守和義務的實際履行仍然需要國家、國際組織、國內武裝力量、民間團體的努力和監督。例如,2005年聯合國為阻止雇傭童子軍的現象,成立了一個觀察小組,專門負責對戰爭中兒童被凌虐、誘拐或被征召為童子軍的現象進行監督。
童子軍現象的治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國家內部的建設,尤其是民族集體認同建設。存在內部沖突的國家往往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非常模糊,整個國家被族群、教派碎片化,對于民族國家的認同感更是薄弱,存在國家認同的模糊和錯位,導致公民對族群等次國家組織的認同取代了對國家的認同,部落、地方族群等傳統社會組織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加強國家內部建設尤其是民族集體認同建設、組建合法政府、統和各部族力量、維持國內和平穩定對于治理童子軍來說也意義重大。
童子軍現象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錯綜復雜的原因,單方面的舉措或行為都不足以完全治愈這一現象,只有多管齊下才能有所成效,童子軍現象的治理任重而道遠,只有全世界一道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守得云開見月明”。
【責任編輯】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