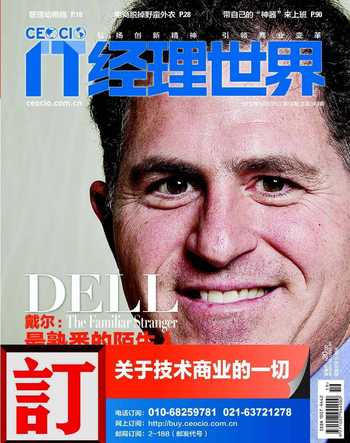淺議手相
汪丁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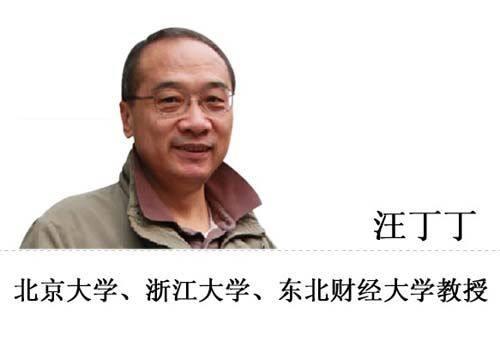

只要有生命,或遲或早,在生命演化的某一階段,生命個體就可能意識到環境及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關于不確定性的意識,概括地稱為“時間”。一百年前,人類相信只有人類具有時間意識。現在,心理學家、腦科學家、動物保護主義者和廣義環境主義者,都認為時間不是人類獨有的。
那么,從何時開始,人類有了時間意識?任何知識,都需要知識考古,不如此,我們就難以預測知識的未來。人類的時間意識,我推測,始于現代人類在6萬年前的“表哥”尼安德特人的喪葬儀禮。尼安德特人,大約在3萬年前滅絕。根據體質人類學家的研究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的腦科學家埃克爾斯的推測,尼安德特人可能有自己的藝術、宗教和語言。值得玩味的是,人類早期巖洞壁畫的年代是在1萬年至3萬年之間,不難想象,尼安德特人可能最先創造了巖洞壁畫,我們只是繼承他們的文化遺產。另一不難想象的推測是,或許我們的祖先導致了他們的滅絕?根據《科學》雜志2010年5月7日的封面報道,尼安德特人可能與直立人雜交,并影響了中國人和法國人的基因序列。
不論如何,在史前史的晚期,在我們的祖先進入農耕時代之前,“時間”已經存在。有了時間意識的生命個體,必試圖預測未來。農耕時代的人類,靠天吃飯。很自然地,進入農耕最早的古代巴比倫人和古代埃及人,觀天象以預測未來。法老與上帝對話,形成了特定的祭祀方式。這一對話,延續到未來。例如,表現為埃及大金字塔與獵戶座三顆星之間的神秘關系。經驗不斷積累,較早進入農耕的人群,有了分工。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些治歷授時的人,必須研究星象,從而有“占星術”。據李零(2012年《文景》,6、7、8連載,“談易學革命”)的介紹,中國漢代,星歷演變為“日者之術”,就是黃歷,擇吉日而行事。當時流行的第二類方術,曰“卜筮”。第三類是“占夢、厭劾、祠攘、相術、風水”。這三類方術,李零又引古人教導:“譬若積薪,后來居上。”越是流行,就越是晚出的。較早流行的,被壓在下面了。卜筮,被黃歷壓在下面了。根據“蓍草”(Achillea Millifolium)的歷史,我推測,相術比卜筮晚。狹義而言,相術就是“相人術”,可考的,大約有三千年歷史。與占星術類似,相人術最初也是“帝王術”。隨著財富積累,術士的人數不斷增加,相術的經驗由專人系統整理,就形成面相學和手相學。
其實,介于卜筮和相術之間的,還有許多民間命相術。例如,西方和中國都有的一種,是觀察杯中剩余茶葉的分布形狀以測兇吉。那么,為何流行至今的似乎只有面相學與手相學?簡單地回答,就是因為“好用”。早期的龜卜,每年都要結算,靈驗的卜辭傳給后代,不靈驗的,銷毀。易經的卦,在卦辭之外還有“系辭”,就是對占卜的“后驗”解釋。
最后,這是我自己的經驗,與相面不同,相手的靈驗,具有更神秘的涵義。一個人的面孔,用博弈論的語言說,是“公共信息”(知識是理解了的信息)。帶著這樣的公共信息,一個人的“命運”(財富、權力、幸福感)往往取決于他在社會博弈中采取的各種策略以及其他人的策略。面孔傳達的公共信息,影響他和他人的策略。所以,在均衡狀態,面相與特定的后果聯系著,總可以被解讀為具有兇吉意義的符號。故而,借用統計學語言,由于上述的“選擇性”,面相學的命題,必可獲得數據支持。
手相,幾乎完全是私人信息,故不存在上述的選擇性。于是,根據手相預測未來的技術,至今仍流行,這件實事本身就很值得思考。私人信息,如何靈驗?它之靈驗所依靠的是哪些途徑?
那么,一個人的“生辰”信息呢?通常,也是私人信息。如果星占術靈驗(流行至今的或多或少都靈驗),那么,上面的問題當然也適用于星相學。可是,如果我們考察星占與相手之間的差別,不難看到,星占的預測,必可應用于特定時空點誕生的全體生命(因為他們全體都有相同的生辰八字),又因為星盤對應的空間范圍很大,故星相學家通常無法解釋在同一區域內有同樣生辰八字的人群之內的個體差異。手相學,以我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個體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