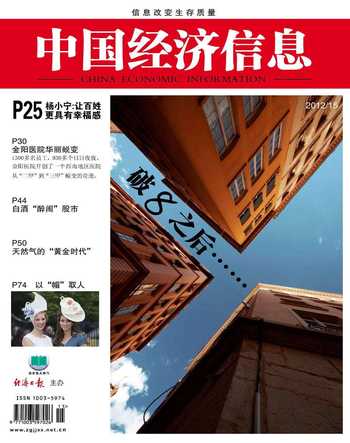讓革命回歸歷史
易玨

對(duì)當(dāng)下的關(guān)懷與價(jià)值的擔(dān)當(dāng),將為我們尋找社會(huì)發(fā)展的歷史成因與未來(lái)道路尋找到更為清晰的脈絡(luò)。
欲知今日中國(guó)向何處去,必先讀懂革命中國(guó)從何處來(lái)。欲知革命中國(guó)從何出來(lái),必先了解革命黨派之歷史。而當(dāng)我們需要了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歷史時(shí),卻會(huì)遇到厚厚的隔離墻。墻外的人想看墻里的故事,困難重重。
臺(tái)灣“中研院”院士陳永發(fā)撰文說(shuō):“我一直在想,中國(guó)革命史這個(gè)領(lǐng)域在今天世界面臨經(jīng)濟(jì)危機(jī)之際特別重要,當(dāng)下中國(guó),改變了‘階級(jí)斗爭(zhēng)治國(guó)路線(xiàn)以后,竟然在短短30年內(nèi)由‘只能和赫魯曉夫勉強(qiáng)在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陣營(yíng)分庭抗禮的國(guó)家,銳變?yōu)橐悦绹?guó)為首資本主義新世界體系里可以呼風(fēng)喚雨的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和軍事體。處此關(guān)鍵時(shí)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國(guó)何去何從的老問(wèn)題,正迫切需要對(duì)中共革命史有實(shí)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
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認(rèn)為,要解答中國(guó)為什么會(huì)發(fā)生一系列事件,“必須要先回到歷史中。我還要想辦法盡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來(lái)分析、討論歷史是怎么發(fā)生的。所有這些原因如果沒(méi)有一個(gè)深入討論,就沒(méi)辦法回答當(dāng)下所存在或所發(fā)生的或今后可能存在發(fā)生的問(wèn)題。”
革命的真實(shí)
由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楊奎松著作集》,以“革命”為主題,將楊奎松的四部經(jīng)典著作合而為一。結(jié)集出版的四書(shū),包括《“中間地帶”的革命》、《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國(guó)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和《西安事變新探》。
《“中間地帶”的革命》、《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著眼于中國(guó)革命的內(nèi)外關(guān)系及其相互作用與影響。《“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shū)敘事宏大,是對(duì)中共革命由來(lái)及其經(jīng)過(guò)的全景式論述;《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shū)聚焦人物,是對(duì)蘇俄作用下中共領(lǐng)袖曲折成長(zhǎng)經(jīng)歷的剖析。
《國(guó)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西安事變新探》著眼于中國(guó)兩大革命黨,即中國(guó)國(guó)民黨與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自20世紀(jì)20年代初以來(lái)分合糾結(jié)、力量消長(zhǎng)的互動(dòng)經(jīng)過(guò)。《國(guó)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一書(shū)以1949年以前長(zhǎng)期居于革命主導(dǎo)地位、執(zhí)政地位的國(guó)民黨對(duì)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與政策變遷為考察對(duì)象,解讀兩黨關(guān)系變化全程。《西安事變新探》一書(shū)則是對(duì)改變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史的這一重大事件背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蘇聯(lián)、蔣介石、張學(xué)良等方面關(guān)系的一種描述。
在楊奎松《革命》四書(shū)的座談會(huì)上,雷頤表示,傳統(tǒng)的黨史教育傾向于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大量檔案還有待公開(kāi),導(dǎo)致諸多真實(shí)的歷史理解無(wú)法獲知。
談及抗戰(zhàn),抗戰(zhàn)史的宣傳和介紹不能“報(bào)喜不報(bào)憂(yōu)”,只講團(tuán)結(jié)抗戰(zhàn),不講磨擦沖突;只講過(guò)五關(guān)斬六將,不講關(guān)公走麥城。楊奎松提醒讀者:“特別重要的是,今天講抗戰(zhàn)史,激發(fā)大家的愛(ài)國(guó)主義情感,絕不應(yīng)當(dāng)忽略當(dāng)年存在的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讓讀者了解,為什么在這樣一場(chǎng)全民族的對(duì)外戰(zhàn)爭(zhēng)中,特別是隨著抗戰(zhàn)時(shí)間的延長(zhǎng),中國(guó)人內(nèi)部還是會(huì)表現(xiàn)出很深的裂痕?”
楊奎松說(shuō):“歷史研究有點(diǎn)像刑警破案,通過(guò)種種珠絲馬跡,深入發(fā)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線(xiàn)索,運(yùn)用邏輯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夠掌握到的歷史碎片串連拼合起來(lái),最后常常能夠發(fā)現(xiàn)一幅讓人吃驚的歷史畫(huà)面。”這既是對(duì)作者學(xué)術(shù)生涯的一個(gè)階段性總結(jié),又具有歷史意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
史料的鉤沉
歷史學(xué)家楊天石在對(duì)談會(huì)上感慨,楊奎松的著作“資料非常豐富,有大量的資料是我們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有大量的史實(shí)也是我們不知道的”。
對(duì)此,楊奎松說(shuō),寫(xiě)這套書(shū)最大的阻力就是資料,“在1980年代我剛剛想從歷史角度來(lái)研究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歷史的時(shí)候,那個(gè)時(shí)候資料幾乎找不到,大多數(shù)的檔案都不開(kāi)放。”但是機(jī)緣巧合,當(dāng)時(shí)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工作。中央黨校是少數(shù)幾個(gè)可以保存中央內(nèi)部文件的單位,同時(shí)黨史研究編輯部又是可以隨時(shí)接觸到大量歷史研究成果的地方。
“所以,我等于從兩個(gè)方面受到了滋養(yǎng),一個(gè)方面是我看到很多資料,另外我可以在黨史研究編輯部吸取相當(dāng)多研究中共黨史包括研究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學(xué)者的各種各樣的問(wèn)題和成果。”
楊奎松像一個(gè)史學(xué)界的清道夫,耐住寂寞,耐住誘惑,扎在故紙堆里找線(xiàn)索。黨史研究界素有“南高北楊”,與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高華擅長(zhǎng)從常見(jiàn)史料細(xì)節(jié)中發(fā)現(xiàn)不常見(jiàn)的問(wèn)題有所不同,楊奎松則依據(jù)詳實(shí)的資料挖掘歷史的真實(shí)。
同情的理解
在題為《直面中國(guó)的革命》的總序中,楊奎松指出:“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guó)革命,不是要探討其應(yīng)否的問(wèn)題,而是要還原其史實(shí)真相,考察變化邏輯,揭示其內(nèi)在的種種因果關(guān)系。”他最后說(shuō),“所謂敗者自敗,成者天成,理也,勢(shì)也,命也。”其中蘊(yùn)含的憂(yōu)患意識(shí),透過(guò)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考證,躍然紙上。
正如雷頤所說(shuō),楊奎松的成就與價(jià)值在于將中共黨史從一門(mén)凌駕于各學(xué)科之上的學(xué)問(wèn),回歸到歷史學(xué)范疇。陳寅恪所說(shuō)的“同情之理解”的歷史研究態(tài)度在楊奎松的書(shū)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哈佛大學(xué)Henry Rosovsky政治學(xué)教授裴宜理看來(lái):“用國(guó)際視野來(lái)考察中國(guó)革命和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的歷史,放眼海內(nèi)外沒(méi)有學(xué)者比楊奎松做得更出色了。通過(guò)發(fā)掘中國(guó)大陸、臺(tái)灣、美國(guó)和俄羅斯的大量檔案資料,楊奎松教授以縝密的研究,對(duì)從西安事變到中蘇關(guān)系破裂等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wèn)題,都給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見(jiàn)解。”
研究歷史,并不止于對(duì)史料的鉤沉與尋找事實(shí)的真相,更多的是關(guān)懷現(xiàn)實(shí),通過(guò)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很多問(wèn)題激發(fā)我們對(duì)歷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對(duì)當(dāng)下的關(guān)懷與價(jià)值的擔(dān)當(dāng),將為我們尋找社會(huì)發(fā)展的歷史成因與未來(lái)道路尋找到更為清晰的脈絡(luò)。
整個(gè)1980年代,楊奎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查閱搜集各種文獻(xiàn)史料上面,光是手抄卡片就做了數(shù)萬(wàn)張。將近十年的資料積累與研究,才沉淀了這套《革命》四書(shū)。我們或可借此一探中國(guó)革命的邏輯與辯證。
無(wú)論今日中國(guó)何去何從,無(wú)論哪種主義與主張,都必須建立在對(duì)于中國(guó)共產(chǎn)革命的真確理解基礎(chǔ)之上。觀照歷史,才能照亮未來(l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