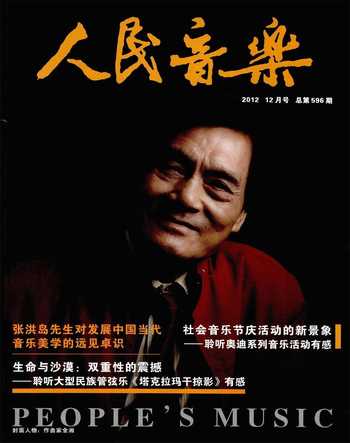芻議音樂的聽與看
古今中外音樂理論體系中,對(duì)音樂的本質(zhì)屬性形成了一個(gè)共識(shí)——音樂是訴諸于聽覺的藝術(shù)。孔子說:“師摯之始,關(guān)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①荀子也說:“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yǎng)耳也。”②這里的“盈耳”與“養(yǎng)耳”都是兩位圣賢充耳聞到音樂之美后發(fā)出的贊嘆!法國(guó)哲學(xué)家、作家盧梭(J.J.Rousseau,1712—1778)說:“全世界的人聽到美的聲音都會(huì)得到滿足,但如果沒有旋律的習(xí)慣變化賦之以生命,單憑這種滿足是引不起喜悅之情的,是不會(huì)成為高度的精神享受的。”③盧梭所指的“美的聲音”顯然不是特指音樂,而是指除音樂以外的所有能夠引起人的快感的聲音。如婉轉(zhuǎn)的鳥鳴、戀人的笑聲、自然界引起人的瞬時(shí)美感共鳴的風(fēng)雨雷電等所有的聲音,甚至一些喧鬧聲或噪聲也會(huì)被有些精神囿于短暫特殊情境的人認(rèn)為是“美的聲音”;而“旋律的習(xí)慣變化”是指由作曲家(包括那些大量的、不知姓名的民間作曲家)的靈感“賦之于生命”的“美的聲音”。盧梭認(rèn)為,只有能稱之為音樂作品的“美的聲音”,才會(huì)引發(fā)人們“滿足”后的“喜悅之情”,才能使人們得到“高度的精神享受。”而后者,正是音樂訴諸于人的聽覺所獲得的。奧地利音樂美學(xué)家、評(píng)論家漢斯立克(E.Hanslick,1825—1904)說:“音樂美是一種獨(dú)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這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nèi)容的美,它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中。優(yōu)美悅耳的音響之間的巧妙關(guān)系,它們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和對(duì)抗,追逐和遇合,飛躍和消逝,——這些東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現(xiàn)在我們直觀的心靈面前,使我們感到美的愉快。”④漢斯立克作為“自律論”音樂美學(xué)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否認(rèn)音樂中思想性和情感因素的存在。他所說的音樂“不依附、不需要”的“外來內(nèi)容”正是指音樂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在他看來,音樂那獨(dú)特的美,只“存在于樂音,以及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中”;換言之,音樂無需所謂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等“外來內(nèi)容”的干擾,僅依賴于其“優(yōu)美悅耳的音響之間的巧妙關(guān)系,它們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和對(duì)抗,追逐和遇合,飛躍和消逝”就足以“使我們感到美的愉快”啦!而這愉快的情感體驗(yàn),是人類被作為審美客體的“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所感染而引發(fā)的、僅屬于人類情感泛起的漣漪而已,與由“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所構(gòu)成的音樂毫無關(guān)系。無論漢斯里克所鼓吹的“自律論”音樂美學(xué)觀如何擯棄音樂藝術(shù)內(nèi)涵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但他十分肯定地認(rèn)為“音樂所特有的美……存在于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這音樂的基本表現(xiàn)形式之中,而“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正是觸動(dòng)人類大腦聽覺神經(jīng)而產(chǎn)生“優(yōu)美悅耳的音響”的音樂。
美國(guó)當(dāng)代作曲家艾倫·科普蘭(AaronCopland,1900—1990)說:“在有生氣勃勃的聽眾的情況下,音樂才能真正地生氣勃勃。全神貫注地聽、有意識(shí)地聽、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聽是對(duì)我們推進(jìn)這門人類光輝的藝術(shù)的最起碼的要求。”⑤科普蘭干脆直截了當(dāng)?shù)匾笕藗儭坝米约喝康闹腔邸比ヱ雎犚魳罚欢抑挥小坝米约喝康闹腔勐牎保魳返穆牨姴欧Q得上“生氣勃勃的聽眾”。
請(qǐng)注意,科普蘭在這里還提出了一個(gè)意味深長(zhǎng)的問題:在“生氣勃勃的聽眾”面前,音樂怎樣“才能真正地生氣勃勃”?音樂作品作為作曲家智慧的結(jié)晶,怎樣才能“生氣勃勃”地展現(xiàn)于“生氣勃勃的聽眾”面前?顯然,這就需要另一群音樂家——指揮家、歌唱家與演奏家用“生氣勃勃”的表演來展現(xiàn)“生氣勃勃”的音樂。于是,此答案便引出了音樂本質(zhì)屬性的另一面——音樂表演。
音樂既然是訴諸于聽覺的藝術(shù),那么就必須依賴于指揮家有序地組織起“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依賴于歌唱家與演奏家以“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為媒介將作曲家腦際中“汨汨流淌”出的美妙樂思(這樂思的物質(zhì)載體即由復(fù)雜的符號(hào)體系構(gòu)成的、默默無聲的樂譜)以創(chuàng)造性的表演轉(zhuǎn)化為“真正地生氣勃勃”的“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呈現(xiàn)于“生氣勃勃的聽眾”的耳際,以最終完成音樂的表現(xiàn)功能。音樂的本質(zhì)屬性也由音樂表演的再創(chuàng)作得以體現(xiàn)和確立。
然而,作曲家腦際中的美妙樂思只是他們對(duì)世間萬象充耳聞之的藝術(shù)性再造?指揮家、歌唱家與演奏家在有序地組織創(chuàng)造性表演的過程中難道沒有打翻過他們內(nèi)心中蘊(yùn)藏著的“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真正地生氣勃勃”的音樂只是停留在訴諸于聽覺的演繹階段?聽眾僅憑“全神貫注地聽、有意識(shí)地聽、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聽”就會(huì)變得“生氣勃勃”?
德國(guó)哲學(xué)家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說:“音樂用作內(nèi)容的是主體的內(nèi)心生活本身,目的不在于把它外化為外在形象和客觀存在的作品,而在于把它作為主體的內(nèi)心生活而顯現(xiàn)出來,所以這種表現(xiàn)必須直接為表達(dá)一個(gè)活的主體服務(wù),這個(gè)主體把他自己的全部?jī)?nèi)心生活擺到作品里去。人聲的歌唱尤其如此;器樂也多少是如此,它只能憑熟練的藝術(shù)家以及他的精神方面和技巧方面的本領(lǐng),才演奏得出來。”⑥黑格爾所說的“主體”應(yīng)指的是指揮家、歌唱家和演奏家,還包括音樂的鑒賞家——聽眾。音樂的內(nèi)容是憑借“主體的內(nèi)心生活顯現(xiàn)出來”的。黑格爾強(qiáng)調(diào),要表現(xiàn)音樂那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主體”必須“把他自己的全部?jī)?nèi)心生活擺到作品里去”,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作品的再創(chuàng)作中。只有在此基礎(chǔ)上,才能借助熟練而精湛的演唱、演奏或指揮技巧,將作品的內(nèi)涵表現(xiàn)得更加完美,更加“真正地生氣勃勃”。而“主體的內(nèi)心生活”當(dāng)然是指“主體”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活動(dòng)中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而逐步積累的生活閱歷——逐步形成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品位——由生活閱歷和藝術(shù)修養(yǎng)的融合逐步升華的精神境界。這一切無疑都是“主體”對(duì)世間萬象的悉心觀察和體驗(yàn)的收獲,而不是僅憑聽覺所能得到的。因此,在作曲家對(duì)世間萬象藝術(shù)性再造時(shí)生成的美妙樂思中;在指揮家、歌唱家與演奏家進(jìn)行再創(chuàng)作時(shí)內(nèi)心打翻的“五味瓶”里,一定內(nèi)含著豐富多彩的視覺印象。這視覺印象與聽覺印象一樣,不僅是作曲家創(chuàng)作靈感的源泉,也是音樂表演家們進(jìn)行二度創(chuàng)作時(shí)再現(xiàn)和激發(fā)作品思想和情感內(nèi)涵的依據(jù)和動(dòng)力。
生理學(xué)認(rèn)為,光作用于視覺器官,使其感受細(xì)胞興奮,其信息經(jīng)視覺神經(jīng)系統(tǒng)加工后便產(chǎn)生視覺(vision)。通過視覺,人和動(dòng)物感知外界物體的大小、明暗、顏色、動(dòng)靜,獲得對(duì)機(jī)體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的各種信息,至少有80%以上的外界信息經(jīng)視覺獲得,視覺是人和動(dòng)物最重要的感覺。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社會(huì)活動(dòng)中都有這樣的體會(huì):當(dāng)嗅覺受到飯菜香味的刺激時(shí),大腦會(huì)根據(jù)曾經(jīng)的飲食經(jīng)驗(yàn)(此時(shí)應(yīng)有味覺的介入)來判斷香味的類別,此時(shí),無論你是否看到了飯菜,其香味類別的判斷結(jié)果總是以曾經(jīng)的飲食經(jīng)驗(yàn)的視覺印象加以確定。“盲人摸象”的典故告訴我們,失去了視覺感知的觸覺印象,只能是以偏概全的假象。另外,在人們生活中的有意無意間,心理活動(dòng)中的視覺印象總是“統(tǒng)領(lǐng)”著聽覺印象。如,當(dāng)我們聽到幼兒園孩子們的歡笑聲時(shí),他們的形象是通過聽覺產(chǎn)生的視覺聯(lián)覺而感知的,這種視覺聯(lián)覺是借助于我們以往若干次對(duì)學(xué)齡前兒童的特征及其玩耍形象的視覺記憶而生成的不確定印象;當(dāng)孩子們進(jìn)入我們的視線時(shí),由于實(shí)時(shí)視覺印象的介入,先前由聽覺產(chǎn)生的視覺聯(lián)覺會(huì)瞬間消失,不確定印象被立即修正,被孩子們可愛而頑皮的樣子所吸引而形成的視覺印象占據(jù)知覺的主導(dǎo)地位,聽覺悄然退居其次。這一知覺心理反應(yīng)在音樂審美心理活動(dòng)中屢見不鮮。如我們聆聽某音樂作品的錄音時(shí),聽覺占據(jù)著主導(dǎo)地位;當(dāng)我們觀看同一作品的音樂會(huì)錄像時(shí),視覺便毫不客氣地將聽覺推向知覺的邊緣而將知覺的主導(dǎo)地位據(jù)為己有。在音樂會(huì)現(xiàn)場(chǎng),觀眾同樣會(huì)有類似的知覺體驗(yàn):舞臺(tái)上,指揮家、演奏家或歌唱家們精湛的技藝和精準(zhǔn)的情感演繹自然會(huì)使聽眾一飽耳福。然而這“一飽耳福”僅僅是由聽覺感知貢獻(xiàn)的嗎?不然,“一飽耳福”之中必然包含著使聽眾“一飽眼福”的音樂家們與其精湛的技藝和精準(zhǔn)的情感演繹相輔相成的儀態(tài)(包括體態(tài)、步態(tài)等)、神態(tài)乃至由儀態(tài)與神態(tài)折射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否則,聽眾很難得到“一飽耳福”的滿足。聽眾從來就不是閉著眼睛聽音樂會(huì)的。特別是在當(dāng)代,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和電影等以視覺表現(xiàn)形式為主體的娛樂媒體,早已將音樂聽眾的欣賞習(xí)慣和審美情趣打造成了下意識(shí)的、以視覺知覺為先導(dǎo)的“音樂觀眾”。
走上舞臺(tái)的音樂家們?cè)诒硌葜校粌H要使自己訴諸于音樂觀眾的聽覺的技藝盡可能完美地展現(xiàn)出來,還要倍加注重培養(yǎng)并保持自己居于舞臺(tái)的美好儀態(tài)、神態(tài)乃至心態(tài)。這是音樂家對(duì)自己更是對(duì)音樂觀眾的尊重。某些音樂家因不注重自己自然天成的或經(jīng)表演修飾的儀態(tài)和神態(tài)的優(yōu)美(指美學(xué)意義上的優(yōu)美),或因表演中的失誤造成了儀態(tài)和神態(tài)美的缺失。在眾目睽睽之下,這種缺失必然會(huì)干擾“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洋洋乎,盈耳哉”,“主體的內(nèi)心生活”的顯現(xiàn)也會(huì)因這種視覺干擾而難以“真正地生氣勃勃”,從而進(jìn)一步干擾音樂觀眾獲得“高度的精神享受”的訴求。
不能否認(rèn)的是,音樂表演中的儀態(tài)、神態(tài)乃至心態(tài),是音樂家們?yōu)槭惆l(fā)音樂作品情感、傳達(dá)音樂作品思想觀念的有機(jī)的組成部分。譬如,指揮家對(duì)音樂作品內(nèi)涵的深刻理解不僅必須以其敏銳的聽力、無與倫比的記憶力和超強(qiáng)的樂感,也必須以其嚴(yán)謹(jǐn)、縝密、精準(zhǔn)的指揮技巧與動(dòng)作,熱情洋溢的外在氣度在歌唱家與演奏家們中間建立自己的權(quán)威和魅力,從而駕馭樂隊(duì)并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樂音的藝術(shù)組合”以鮮活的生命力。歌唱家與演奏家完美演繹音樂作品內(nèi)涵也不僅憑高超的演唱、演奏技巧和充沛的情感儲(chǔ)備,其規(guī)范的演唱演奏姿態(tài),基于作品情感宣泄的需要而生發(fā)的恰如其分的夸張形體和表情(包括適度的舞蹈動(dòng)作),與所表演的作品內(nèi)容、風(fēng)格相適應(yīng)的化妝與服飾造型(這里包括角色造型與非角色造型)及不同凡響的精神氣質(zhì)等,毋庸置疑地構(gòu)成音樂表演的兩個(gè)不可或缺的互補(bǔ)性創(chuàng)作條件。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觀點(diǎn)不僅適于“藝術(shù)音樂”概念所涵蓋的音樂形式的創(chuàng)作與再創(chuàng)作(指所謂的二、三度創(chuàng)作),也包括“布魯斯、爵士樂、狐步、探戈、鄉(xiāng)謠、新民歌”以及“結(jié)合古典音樂、民族音樂和現(xiàn)代流行音樂的探索匯聚成的‘世界音樂與‘新世紀(jì)(或譯新紀(jì)元)音樂”⑦等抒情性較強(qiáng)、表演形式接近于“藝術(shù)音樂”的一類流行音樂。當(dāng)然,訴諸于視覺感官的各種元素是否恰當(dāng),如何避免過度詮釋的“喧賓奪主”,也應(yīng)引起足夠的重視和研究。
因此,當(dāng)代的指揮家、演奏家和歌唱家們?cè)谝魳繁硌葸@一音樂作品的再創(chuàng)作中,不能僅奉獻(xiàn)給當(dāng)代的音樂觀眾以“聽覺盛宴”,也可以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獻(xiàn)給音樂觀眾以“視聽盛宴”。只有這樣的音樂表演“才能真正地生氣勃勃”,才能對(duì)得起“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去聆聽音樂“這門人類光輝的藝術(shù)”的“生氣勃勃的”的音樂觀眾。
①吉聯(lián)抗譯注《孔子孟子荀子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
②吉聯(lián)抗譯注《孔子孟子荀子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頁。
③何乾三選編《西方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音樂家論音樂》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頁。
④?眼奧地利?演漢斯里克《論音樂的美》,人民音樂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頁。
⑤?眼美?演艾倫·科普蘭《怎樣欣賞音樂》,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頁。
⑥同③,第103—104頁。
⑦金兆鈞《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親歷中國(guó)流行音樂》,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頁。
謝力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
(責(zé)任編輯 金兆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