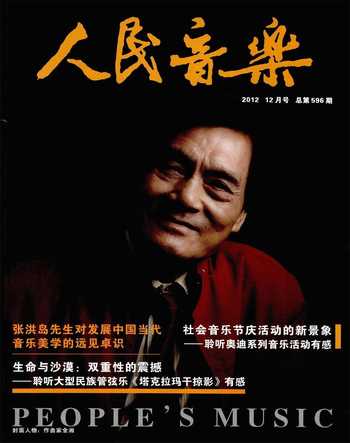試論歌劇《丑角》中的人物塑造及戲劇結構
孫遜
為19世紀晚期興起于意大利的真實主義?穴Verismo?雪歌劇的代表作,由意大利作曲家萊昂卡瓦洛(Leoncavallo,1857—1919)譜曲并自編腳本的《丑角》(IPagliaacio,1892)敘述了一個由愛生恨的情殺悲劇。該劇情節緊湊、筆法直白尖銳,腳本結構采用了戲中戲套疊結構。通常情況下,“丑角”多是與諷刺、嘲笑、滑稽、荒誕等詞相關聯,而在此歌劇中,作曲家賦予了“丑角”以更深層次的內涵——不再僅僅秉承著諷諫時事、滑稽調笑的傳統,而是通過這一特殊社會角色折射出主體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追問。在歌劇中,“丑角”作為歷史文化的承載者完成了對自身的超越,作為戲劇的特定角色,其含義通過人物性格塑造及隱喻手法而獲得延伸。
《丑角》中的人物塑造及戲劇套疊結構分析
(一)“丑角”的人物塑造
該劇是作曲家根據卡拉布萊地區發生的一起兇殺案改編而成。故事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的意大利,流浪劇團班主卡里奧帶領團員到卡拉布里亞村演出,發現妻子內達和村中青年希爾維奧偷情,正當卡里奧憤怒之時無奈演出即將開始,他們上演的戲劇恰好講述了由內達扮演的妻子科隆賓娜,背著由卡里奧扮演的丈夫帕里亞喬與情人幽會被發現的場景。恍惚間,卡尼奧將演出與現實混為一體,竟真的將劇中妻子及其情人殺死。
與傳統意大利歌劇不同,《丑角》并不以詠嘆調來表達和塑造角色,而是采用宣敘調與詠嘆調結合,并將日常生活中的喊叫和哭泣聲融于其中。器樂伴奏服務于歌劇劇情,具有明確的戲劇性。其中,男主人公卡尼奧是個點題角色,他的劇中唱段“我不是丑角”可以說是作曲家自我“丑角”意識的認知、轉變。
第一幕《穿上戲裝》(Vestilagiubba)
這段描寫的是卡尼奧發現妻子的出軌行為以后,卻要穿上戲裝強顏歡笑的一段內心獨白。一方面,妻子突如其來的背叛帶給他巨大痛苦;另一方面,演出在即他必須掩蓋內心痛苦而強顏歡笑。此時的音樂以弦樂為主,手法簡潔地呈現出卡尼奧內心苦悶情緒,隨著情緒的推進,旋律也逐漸出現起伏并推向戲劇高潮。唱段采用傳統的宣敘—詠嘆調模式,經過10小節建立在a小調上的宣敘調,旋律轉到了建立在e小調上的朗誦式詠嘆調。旋律中的增音程和大幅度的強弱對比,使卡尼奧內心的悲痛得到進一步強化。
托尼奧與佩里退場之后,小提琴聲部用斷斷續續的音型刻畫出卡尼奧內心情緒的不平靜。緊跟著低聲部沉悶的大鼓聲預示著演出即將開始,密集鼓聲營造出一種緊張的氣氛。此時宣敘調以弦樂伴奏,與旋律聲部級進的八分音符相對應的是伴奏織體擴大時值的二分音符,時值的擴大給人以豐滿的音響感覺。(見譜例1)
隨后,卡尼奧越說越激動,當發出感慨:“必須強迫自己,你算什么人?你是個丑角!”時,音樂以一連串短時值音的級進上行,來表現唱段中標注的“暴怒”①情緒。此時伴奏聲部的弦樂用短小而強有力的和弦以及銅管樂的加入,對旋律起到了強化和助推的作用。
經過一段的情緒起伏,卡尼奧以夾雜著傷心、痛苦、絕望的音調,唱出貫穿于全劇的“丑角”動機,仿佛一聲聲嘆息,達到情緒的至高點(見譜例2)。這一動機在序曲中就已使用,在隨后的托尼奧開場白、間奏曲以及劇情發展過程中卡尼奧的多個唱段中亦多次出現。動機的反復出現,一方面不斷強化著卡尼奧內心的憂郁情緒,另一方面也不斷加深了觀眾對戲劇悲痛基調的感受。作曲家在這里明確標注著“哭泣”②,而唱到此處卡尼奧已經泣不成聲。旋律轉由弦樂進行詮釋,反復奏出哀愁沉寂的《穿上戲裝》的旋律主題,已經完全取代了聲樂部分,最后結束在貝司低沉的“丑角”動機之中。
(二)戲劇套疊結構的分析
萊昂卡瓦洛在《丑角》中采用了套疊結構,即劇中劇結構。戲劇內外情節交疊,現實與舞臺混淆,戲劇上的復調結構及精神上的悲喜二重性,使得全劇充滿了戲劇性張力。表演過程中,卡尼奧扮演的帕里亞喬瘋狂地逼問內達那個情人是誰,而內達試圖用語言喚醒他:“你是帕里亞喬!”正是這句臺詞讓卡尼奧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扔掉丑角的帽子,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此時,臺下觀眾卻不明事理以為是演員故意添加的喜劇效果而開懷大笑。臺上卡尼奧越痛苦,越想沖出“丑角”帕里亞喬的樊籬,臺下觀眾越覺得他的表演詮釋真實。在這段音樂處理上,萊昂卡瓦羅運用了簡潔強烈的手法表現出音樂情緒風格的鮮明對比,悲喜之間的微妙處理彰顯出作曲家出色的駕馭音樂與戲劇關系的能力。例如:在第二幕的詠嘆調《我不是帕里亞喬》(No,pagliaccio nonson),與“穿上戲裝”相比,其音響中更加強調管樂的作用,顯然弦樂音色已不能充分表達卡尼奧內心強烈情緒。唱段一開始,內達提示性的“帕里亞喬”過后,弦樂在打擊樂的不安敲擊聲中,用持續的顫音,渲染出此處的氣氛(見譜例3)。卡尼奧用下行音調唱出:“不!我不是帕利亞喬!”弦樂與管樂共同奏出此唱段中的主要伴奏音型(見譜例4)。手法巧妙,筆觸簡潔,將卡尼奧近乎崩潰的痛苦心緒表現得真切動人。弦樂采用震弓奏法,持續一種不安、緊張的因素。與之呼應的是銅管樂跳躍式音型的進行,在弦樂昏暗濃厚的音色下,銅管先是一個跨越八度的八分音上行級進,構成逐漸增強的力度,緊隨其后的符點八分音以快速下行與前小節形成鮮明對比,同時又與弦樂構成對峙,力度由強至弱。這兩個主要伴奏音型貫穿全段,并采用調式調性的移位表現出卡尼奧內心情緒的不斷變化。
卡尼奧的一段抒情內心獨白過后,內達試圖將卡尼奧拉回劇中“唱著一曲俏皮的嘉禾舞曲‘沒有想到你如此殘忍(Suvviacositerribile)。”③音樂由緊張、恐怖的情緒突轉到以輕柔可愛的弦樂音色為襯托,輕松、滑稽的舞曲氣氛中。但此時的卡尼奧早就不可抑制自己心中的疼痛和憤怒,他用近乎嘶吼的聲音盤問著內達,伴奏織體表現為管弦樂隊的齊奏。音樂節奏更加緊促,伴隨著卡尼奧歇斯底里的喊叫,樂隊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級進上行緊接其后,音樂再次將我們帶入不安的情緒中。這里的卡尼奧自身所具有的“丑角”因素已經和戲劇表演中的丑角合二為一,卡尼奧作為生活中的丑角,與戲中的丑角帕里亞喬融為一體。
與此同時,內達與卡尼奧的關系徹底決裂并爆發,她用“尖叫”對抗卡尼奧的憤怒。樂隊伴奏同樣采用兩個八度連續十六分音符半音階級進上行與尖叫音調配合。內達的反抗聲、混雜著觀眾的質疑“他們還在表演嗎?芽還是當真了?”④加上希爾維奧的自言自語、臺旁佩里和托尼奧對白的插入,將戲劇推至高潮。最初內達的陳述,由弦樂以同音反復的連奏烘托,而隨著情緒的起伏,弦樂持續連奏保持緊張、恐怖的氣氛,而管樂與打擊樂逐漸加入,似乎預示著內達不可逃離的厄運。臺上的演出與音樂織體的變換將觀眾與角色的心連在一起。戲劇最終以內達的死宣告結束。場面一片混亂,甚至觀眾還來不及想是怎么回事,內達與希爾維奧已雙雙死在刀下。
《丑角》人物塑造及套疊結構的內涵
通過以上具體分析,我們可清楚地看到真實主義歌劇主張的美學觀念:力圖逼真、不加修飾地再現生活。藝術家們基于這樣一種追求,將原樣生活甚至于一些暴力、血腥場面直接搬上舞臺,以至于有學者稱“真實主義歌劇是電影電視恐怖片的無辜的祖先。”⑤處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真實主義歌劇,其風格理念在后世的許多歌劇流派中都可尋見蹤影。就整個音樂史發展來看,它為表現主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但歷史中似乎更多關注其表現手段而未深究它背后的審美理念及所折射出的思想內涵。
(一)審美價值——審美主客體關系的拓展
作曲家獨特的音樂語匯以及巧妙的戲劇構思,在審美過程中導致了審美主體下意識的心理距離消逝。由于《丑角》的戲中戲套疊結構,因此在欣賞過程中涉及到兩個審美主體,即戲內觀眾和戲外觀眾。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述審美主體是指戲外觀眾。導致審美主體心理距離消逝的原因,是主體在審美過程中的投情。在審美過程中,我們可以將主體意識分為三個轉化階段:自我、他我和本我。自我,是主體從自然中脫離出來以后所具有的意識階段;他我,是主體意識客體化的階段;本我,即超越自我,回歸心靈原初及本真的意識階段。在欣賞過程中,由于音樂對人物復雜矛盾心理的形象刻畫,使審美主體投情于作品,造成審美主客體的在欣賞過程中的同化、互溶,使
欣賞者忘掉自我、變成他我,最后回歸本我。
《丑角》中,音樂不僅作為重要的戲劇表現手段,而且作為觀眾理解歌劇內容的媒介,通過音樂特有的方式對人物心理進行形象刻畫。劇中唱段無論優美高雅還是平鋪直敘,經過作曲家的精心描摹讓我們在其引領下深入劇中。音樂的塑造使主人公卡尼奧陷入一定的情境,從而曝露他最內在的本質。舞臺上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為了使他產生激烈的內心沖突,而音樂的細膩刻畫讓聽眾完全投情于劇中角色而發生位置轉移。這種獨特的音樂語匯及巧妙的戲劇構思,由于人類審美判斷所具有的“共通感”⑥以及社會坐標的相似性⑦而使審美主體在感知過程中獲得了對客體的認同感。萊昂卡瓦洛塑造的人物特性并不是標簽式、臉譜式的,由于他曾在咖啡館任職鋼琴師,對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活有切身體驗,因此能在劇中準確地把握下層藝人復雜的心理。而作為同一社會背景下的普通百姓,在審美體驗中便不會將人物隔離化、藝術化,不會抽身游離于背景之外。真實主義歌劇是19世紀晚期意大利現實生活在藝術上的產物,作曲家通過作品揭示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下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和無奈,他對底層百姓的同情引起了他們內心最大的反響,使處在同一社會環境下的欣賞主體通過理解和體驗劇情而直觀生動地把握住作品
的內在精神品質。
(二)思想價值——“丑角”的精神內涵
萊昂卡瓦洛正是通過“丑角”形象所表達的苦難和矛盾,引起人們對社會下層小人物的關注,同時展開對生命價值的深層追問。
1.對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終極關懷
劇中男主人公卡尼奧作為點題的角色,被塑造成現實與戲劇中重疊交織的丑角。作為現實中的丈夫,他的妻子有了私情,人性受到擠壓;作為舞臺上的丑角演員,即使傷心欲絕,也要在戲中逗引所有人發笑。通過對卡尼奧不同唱段的分析,我們可以鮮明地體會到作曲家對于其自我“丑角”意識認知的
心理狀態的把握。
卡尼奧在戲中的內心獨白及其表現,已經超出了戲中之戲帕里亞喬的身份定位。他在傾訴發自內心的苦痛,但這一切又都完美契合:內心流淌的是帕里亞喬的悲哀,更是自己的苦痛。卡尼奧意識到自己不僅是戲中逗人發笑的丑角,更是現實生活中帕里亞喬可笑身影的折射。通過作曲家不同音樂
素材的塑造,兩個丑角融為一體。
歌劇的悲劇主題表現出卡尼奧對沖破丑角自我的強烈愿望,這種希望的渴求又處在與整個社會無法調和的沖突之中不得化解。在劇中,表現的是所有人的悲劇,每個人都是得不到完滿需求的個體,蒙在鼓里的卡尼奧、遭到拒絕的托尼奧、戀情不被允許的內達和希爾維奧,所有的人都體現出本身的丑角性因素。由于《丑角》技法上的獨特性,造成了空間上戲劇與現實的錯位,致使劇中觀眾的愚昧顯現。結合當時意大利具有批判現實主義風格的“真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以及意大利矛盾交織的社會背景的特殊性,不難想象,作者也展現出人民大眾的丑角性心理,所隱喻的是人民大眾的悲哀。或者正是帶著真實主義文學“流露出的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不可避免地悲觀失望”⑧風格,又或者瓦格納悲觀哲學對于萊昂卡瓦羅的影響,作曲家揭示了人性中具有“丑角”特征的一面,正是人自身的“丑角性”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由于萊昂卡瓦洛對卡尼奧的人物及其命運悲劇的社會成因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困感和迷惘,卡尼奧的悲劇一方面來源于“他重返戲劇音樂的絕望企圖。”更重要的是,他已經意識到自己就是生活中的帕里亞喬,無論生活還是舞臺,自己都是個丑角。在他人心目中,卡尼奧首先是一個歌手,其次才是一個人,這是他根本的悲劇。這就展開了對人類自我生命價值的追問,對生活本質
的探尋。
2.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
由于《丑角》悲劇主題的哲學意蘊,作者展開的是對人類生命價值、生活本質的追問。萊昂卡瓦洛以悲劇的角度刻畫世界,把他對于“丑角”悲劇的哲學理解貫穿在整部歌劇中。那個由二度級進音程構成的“丑角”動機在序曲中作了初步呈現之后,一直伴隨著卡尼奧貫穿全劇的始終。《丑角》骨子里流淌的是古希臘悲劇的哲理性與悲劇精神,它宣泄凈化人們
思想的同時,更讓人們反思。
《丑角》作為真實主義歌劇的代表作,體現著對小人物的終極關懷。作者以女主角內達的死來推進男主角卡尼奧的悲劇性,把卡尼奧塑造成反對社會虛偽道德的形象。音樂在“丑角”動機的反復下使人們陷入悲痛陰郁的綿延之中,意味深
長。死亡即意味著失去,內達的死并不能化解卡尼奧心中的仇恨,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卡尼奧內心的傷痛。
在《丑角》中,“人物”與“戲劇”發生錯位,通過立與破的統一,悲與喜的交融,美與丑的對立的悲劇性塑造,歌劇以人與現實、自我與假面丑角的沖突為主題,表現置身于紊亂的客觀現實里的人被迫帶上種種面具,在虛幻中尋求真實,卻永遠失去自我,被現實所拋棄的悲劇。這種戲與人生的錯位,產生對錯綜復雜社會的展示與質問,對生活本質、生命價值的追尋。由于《丑角》這種悲劇主題的哲學意蘊,它與觀眾是共時的同時又是歷時的。它所揭示的是人類社會錯綜復雜的社會本質,展開的是對人類自我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具有時代
的特殊性,又兼有歷史的普遍性。
結 語
無論是戲劇名稱自身的寓意,還是特性音樂語匯以及套疊戲劇結構造成的深層哲理升華,《丑角》都必然使成為歌劇史上經久不衰的劇目。其深刻的悲劇性凸顯出人類對自我的追尋,進而引發人們對當下的思考。人類成就了社會,卻又成為它的犧牲品。人性被壓抑著而扭曲了本來的面目,我們在扮演著不為人知、不為己知的角色。誰又能否認在自我的多重身份中不曾扮演過“丑角”身份呢?可是,你會為你的丑角身份痛苦嗎?會為自己是帕利亞喬而憂郁嗎?這一系列的疑問正是《丑角》帶給觀眾更深層的精神震撼,隨著不同時期、不同審美主體以及不同審美角度的切入呈現出意義的多解性。內達的死并不意味著卡尼奧人生悲劇的結束,那么,如何理解人生的“丑角”?當我們正處在自我“丑角”身份的時候,是以阿Q精神重返“喜劇”之中進行自我蒙騙,還是要沖破牢籠進行自
我破解?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