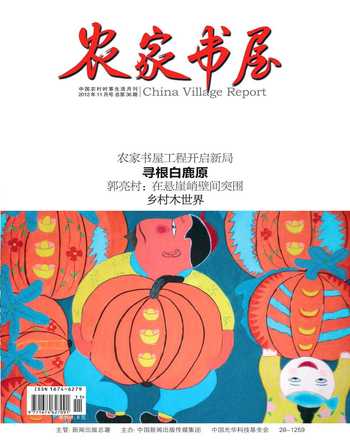吃面
蕭丁
中國的北方人,吃飯一般不吃米飯,故只以吃饅頭、饃饃為吃飯。而南方產稻地區民眾一般一日三餐離不開大米,不愛吃面食。我雖南人,卻有點北化。因為少時窮困,老吃南瓜、山芋、雜糧,故與面食有緣。現在我的早餐,不是餛飩,就是面條。
中國人吃面始于漢代,那時面的形態不是細長而是扁平,屬于面片一類的,叫作湯餅。以至古時風俗,生了男孩都要舉行湯餅會。關于湯餅,古書記載很多,唐代劉禹錫和宋代蘇東坡都曾經寫過吃湯餅的詩。不過他們所說的湯餅,恐怕已不是面片,而是面條了。因為到了晉代,湯餅已經是條狀了。而至宋代,就正式有了面條這一名稱。
鄙人見少識淺,不知天下之大,但自己吃過、印象深刻的面條也有以下幾種:
一是云南的過橋米線。這是由蒸熟的米粉在篩網上擠出的粉條。美在湯中。傳說古代有位秀才為專心備考,都在村邊的小亭中復習功課,飯盒都由娘子送去,送飯路不短,要過一座橋。秀才娘子怕飯涼。特用雞湯為汁。雞湯不易散熱,雖過橋而不涼。現在吃的過橋米線保持了這個特點,只是湯料更加考究。客人落座之后,店家會先端上一大碗調好料的雞湯,再用生切的薄如厚紙的雞片肉片魚片和新鮮蔬菜及米粉面條,在雞湯里溫上幾秒鐘,即溫即吃,妙處只有一個字:鮮!
二是雙鳳羊肉面。這許是太倉雙鳳鎮那家鄉村小店的特產,很不起眼,面條的澆頭也僅是紅燒羊肉。我們去時受到優待,每人一只羊蹄膀,又酥又黏又香又糯,這哪里是在吃面?分明在吃羊蹄膀!我的食量雖然不淺,還是只恨胃小,沒能把這碗美食全部裝下。
三是昆山的奧灶面。奧灶面的奧妙在于灶。奧灶同吳下方言之鏖糟、齷齪諧音,是不潔的意思。據說乾隆下江南的時候,看到村前有位老嫗正在操勺燒面,那灶頭齷齪異常,因為正在饑腸轆轆之時,也顧不得,只好屈尊懇請老嫗賜食。但吃了一口,便覺味道甚佳,遂賜名奧灶。奧灶面的特色在于紅油面湯、紅油爆魚和白汁鹵鴨。這魚湯不問來歷倒也罷了,問起來歷,確有鏖糟之嫌。因為它是用青魚的魚頭、魚血、魚肝、魚鱗加上各種香料、雞汁、中藥燴制而成。這紅油面湯的鮮度香度,可想而知。爆魚用陽澄湖的鮮活青魚批薄,在姜、蔥、醬和曲酒內浸漬半小時,再放入旺油鍋中汆至嫩黃,再加姜、黃酒、冰糖燴成。這種爆魚,色澤棕紅,味道鮮香。鹵鴨則采用當地名種大麻鴨,加上陳年老鹵、祖傳中草藥配方精心烹制,鹵味醇香撲鼻,鴨塊皮嫩肉酥,肥而不膩,難怪奧灶面從清代流傳至今,一直被人們奉為江南名點。
四是杭州魁元館的片兒川,這是咸菜筍片肉片面,平常不過了。但是我吃遍滬上各店的咸菜面,竟沒有哪一家堪與片兒川相比,真是奇怪。其實,片兒川的味道一在于湯鮮,二在于面硬,這種面只有杭幫菜館有,上海人好像做不來。當然也有例外。在上海的面館中,老半齋酒樓的雪菜燴面就久負盛名。據說,它的雪菜要用中火經過三個小時的炒制,面湯要用肉骨頭、老母雞、黃鱔骨、蛤蜊等吊制五個小時才成。更讓人傾心的是,其面雖工而價不貴,又善待老人,故每天早晨老客盈門。
中國文化涉及方方面面。吃有吃的文化,面有面的文化,真可謂各有功夫不同,例如燒面的功夫,一在湯上,二在澆頭上,三在面的本身。但依我之陋見,不論這種面那種面,有了好湯就有好面,清人袁枚最善作“鰻面”,以大鰻一條,拆肉去汁熬湯,湯中再加雞汁、火腿汁、蘑菇汁,面放在這種湯里,會不好吃嗎?但現在上海的面店,大多不把功夫放在湯上,而是放在澆頭上,那樣的面,又會好吃嗎?確切地說,那不是請客人吃面,而是吃菜了。
同是清人,李漁與袁枚不同,他主張功夫要放在面上。他說,味不在面而在湯,等于沒有吃面。他自己就創造了兩種面。一種叫五香面,一種叫八珍面。五香面用椒末、芝麻粉拌入面粉中,再用醬、醋、筍汁、菇汁、蝦汁和面,不再用水。八珍面是用雞、魚、蝦之肉曬干了,研成碎末,與香菇、鮮筍、芝麻、花椒之末及蝦汁與面粉拌在一起搟成的面條。這種面條之研究,簡直像《紅樓夢》里老祖宗吃的茄鲞,味道肯定是好的,但誰有閑功夫這樣做面條呢?所以只見之于記載,未見之于實踐,早就失傳了。
這種面那種面說了半天,在我看來,都不及敝鄉的雞子面,這種面以雞蛋作水,和粉調成搟薄切細,現搟現下,面條硬扎,久煮不爛,湯水索清。澆頭則用冬筍、香菇、金針、肉絲、豆干、油泡、腐衣,再加幾顆純精肉做成的小紅棗那么大的“肉丸棗”,以肉骨、雞汁熬湯,這樣的面,難道您不想吃?我是家常便飯了。每次我從家鄉一買就是20斤這樣的雞子面,曬干了,裝箱到上海。然后每天早餐就吃此物,澆頭親自烹制。朋友們如果口饞,不妨到舍下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