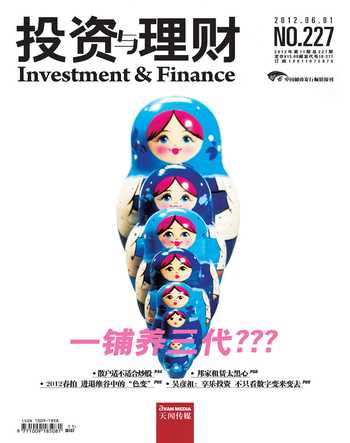禪意之美妙無(wú)言
拙父

在“銅道”藝術(shù)館,有一枚沈陽(yáng)造幣廠韓曉生先生的名作——以《禪》命題的大銅章,引來(lái)無(wú)數(shù)觀賞者駐足凝思。
大家知道,“禪”字的出現(xiàn),既不是對(duì)印度佛教中某一概念的音譯,也非意譯,而是在翻譯中的借題發(fā)揮、有意識(shí)地取《莊子》之辭,寓意于華妙難知,玄奧深解之思,而進(jìn)行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
禪宗思想原初的思維模式, 即本體無(wú)相,即體即用,靜虛空靈,佛性本有,頓悟成佛。后經(jīng)歷代禪師在理論上進(jìn)一步推促其向“心性論”方向轉(zhuǎn)化,至慧能,終于形成以《壇經(jīng)》為代表的系統(tǒng)的禪宗思想。禪對(duì)外境而不執(zhí)著于外境,由心發(fā)端而不著守自心。安心無(wú)為而任自然,任自然而不執(zhí)一端,不執(zhí)一端必超越相對(duì),超越相對(duì)則可涵蓋無(wú)限。禪就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和這種思維方式所通達(dá)的意境。從思維上講,它是經(jīng)驗(yàn)的;從意境上看,它則是哲學(xué)的和審美的。
要把經(jīng)越千年滄桑的“ 禪” , 藝術(shù)的具象的表現(xiàn)出來(lái), 尤其是在只有80mm的大銅章上表現(xiàn)出來(lái),其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有觀賞者駐足凝思亦不足怪矣。
韓曉生先生的創(chuàng)作之妙,在于得禪說(shuō)禪,“心之妙,妙萬(wàn)物而言”,“不可以語(yǔ)言傳而可以語(yǔ)言見(jiàn)”,以銅說(shuō)話(huà),講禪“對(duì)外境而不執(zhí)著外境”,選大眾傳知的達(dá)摩為具象,妙大眾自心體認(rèn)之辯證思維。大銅章正面,達(dá)摩一手持念珠托腮,閉眼抿嘴,做沉思狀(禪不在思,離思無(wú)禪),印堂中聚攏的紋理正在消退,悟到的明慧在眼角處化作瞬間即逝的滿(mǎn)足與愉悅,參透的機(jī)緣在嘴角留下了矜持狡黠的笑意。若將韓曉生雕塑的達(dá)摩與羅丹雕塑的《思想者》的表情做一比較,思想者是正在思考,而達(dá)摩是想透了而不說(shuō)(禪不可說(shuō),不可說(shuō)非禪)。唯獨(dú)達(dá)摩的一張臉一只手,無(wú)能所、無(wú)對(duì)應(yīng)、孑然獨(dú)有,靈光獨(dú)耀,表現(xiàn)出了非有非無(wú),非色非心,非言語(yǔ)可表,非思想可及的意境。真是悟者尚有言跡,證者空痕也無(wú),完全是禪的意境與審美。更有禪意的是韓曉生將現(xiàn)代電影的動(dòng)態(tài)表現(xiàn)手法在此雕塑中靜態(tài)的借用了一把,達(dá)摩的左邊頭顱似乎在快速分解風(fēng)化,似為禪之借殼、離相、離念,卻又于風(fēng)化分解物中析出,形成了由小到大無(wú)數(shù)閃光的球珠,星星點(diǎn)點(diǎn)可獨(dú)成一個(gè)宇宙。其中寓意與背面雕塑的意蘊(yùn)前后呼應(yīng),虛實(shí)相生,自然映襯,心至無(wú)疆,包容萬(wàn)象。背面是萬(wàn)千盤(pán)根錯(cuò)節(jié)的藤枝喬木圍籠而成的窩,中間放著一枚蛋,蛋上寫(xiě)著一個(gè)禪字。那萬(wàn)千藤喬顯然不是無(wú)根之木,給人以生命盎然、紛雜而有序之象。只有如此強(qiáng)大的文化叢林才能孵化和孕育、創(chuàng)造和誕生禪宗之禪。至此,韓曉生先生的《禪》,細(xì)細(xì)看來(lái),“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wú)非般若。”
一枚銅章,仔細(xì)品味,令人折服。掌股間竟能承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美好的故事,如此深刻和玄奧的思想!與其說(shuō)我欽佩韓先生的雕塑,不如說(shuō)我欽佩韓先生的禪意。禪意美,妙無(w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