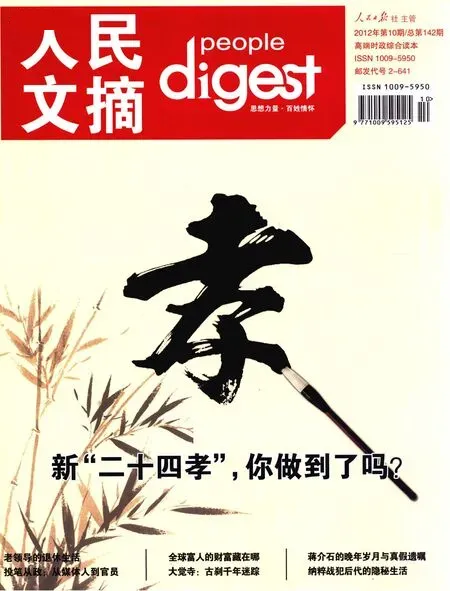王蒙的仕途與人生
陳濤
“這么大歲數了,沒有像我這樣有肌肉的吧。”在北戴河“政協(xié)浴場”的海灘上,戴上泳鏡,王蒙就直接撲向海里,越過在淺海套著救生圈的年輕游客以及撲騰著水花的孩童。
這天下午,風浪很大。78歲的王蒙說:“再大的浪我都見過。”
政治和文學這兩個“風浪”交織于他的人生。
中庸/協(xié)主席唐浩明說:“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學史。”
對于這種說法,王蒙解釋道:“也談不上,當然現在來說,我經歷過的事情也比較多。”他喜歡用這樣婉轉的方式回答問題,“我并不否認我的中庸對一切都不抱幻想。”
“文學史”得有作品,王蒙有“干貨”。他的創(chuàng)作已有60年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作品“有一定的響動”。“到現在為止,我的寫作還在積極地運轉著。相對于其他作家,有的人是前段寫,后面一段不寫了,也有的從新時期開始寫。從時間長度上他們不好跟我比。”王蒙說。
新書《中國天機》在近期又開始“響動”。他認為,當今人們對政治的熱情和關注日益增加,但是淺薄與情緒化的見解太多。
事實上,近年來他也未中斷過對政治、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發(fā)聲,他說:“我有巨大的政治責任感,因為首先我自幼就熱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為一個接地氣的人,我從基層的團委、人民公社干部都當過,還當過中央委員、政協(xié)常委;第三,我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被提拔過,被毛主席多次點名,也被打人過歷史的另冊;另外,我還去過境外60多個國家,也見過國外諸多國家領導人,有一些交流經驗。”在他看來。這是《中國天機》的出版緣由。
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作之家”休養(yǎng),著手創(chuàng)作該書。從10多年前開始,他每年夏天都會到此避暑。在“創(chuàng)作之家”,從安保人員到管理層,他們對王蒙已經很熟悉,都叫他“部長”。在位于北戴河康樂路的“政協(xié)浴場”,管理人員和救生員也很熟悉“部長”,王蒙每天下午3點左右都會來游泳。
仕途/文學癖
20多年過去了,“部長”的稱謂還在。從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王蒙擔任文化部主要領導職務三年零五個月。上任部長那年,王蒙出版了小說《活動變人形》,反思現代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下的心靈沖突,被譽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變形汜”。
事實上,王蒙本人也是作協(xié)的“主要領導”,從1986年至2006年擔任副主席。還有傳言,王蒙也曾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諾獎的提名是一個說不太清楚的事情,它是封閉的,怎么提名,怎么評的,什么都不對外界公開的。”王蒙解釋說,“瑞典文學院在過去也給中國作協(xié)發(fā)過信,希望可以推薦。中國作協(xié)提名過巴金、丁玲等,另外國外一些大學,也有這種提名。我想,提過我也不足為奇,我說的主要是國外的一些機構。”
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王蒙說自己的“熱度”,顯然在后者。“與純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我有文學癖好,我從來沒有追求過哪怕一星半點的‘仕途。”他說。但如今,“想否認也不可能了”,王蒙說,“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就是生活,就是命運,就是故事”。
保護/批評
“打人另冊”,王蒙這樣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么政治還是要有個鐵飯碗,有個吃飯的過硬家伙。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拐點,我寧愿回歸到文學里面討生活。”王蒙說。
1956年4月,22歲的王蒙寫了個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9月發(fā)表在《人民文學》上。雜志社的工作人員騎著摩托車將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這樣的稿酬在當時“也夠驚天動地了”。
但很快《文藝學習》雜志展開對該小說的討論,王蒙在《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朋友也找來,說該文已經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論了,要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準備。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匯報》發(fā)表了長篇文章,批評《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王蒙很快給周揚寫了封信,請求指示。主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叫了王蒙談話,說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說,不贊成將其完全否定。“我那個小說,毛澤東前前后后講了六七次。”王蒙回憶說,“總的調子就是,一保護,二批評。”
王蒙雖然沒有當面聽到毛主席的點評,但聽過錄音,“毛主席親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點評青年作家,“在當代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憶。
新疆/北京
“相對于其他老作家,你受過的苦不算嚴重吧?”有媒體問王蒙。
“對,那當然。一切都是看比較,相對來說,我不算特別嚴重。”王蒙回憶,“一是我的工資沒有降,當時在北京我是87塊錢每個月,在年輕人里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補貼,一下子變成124塊,開玩笑,那算不錯了。再一個,我沒有被毆打過,也沒有戴高帽子游街,也沒進監(jiān)獄。”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傳三部曲”。第一部中記錄了他到新疆的詳細過程。去新疆是他主動申請調去的,甚至“極其興奮”,并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調到了新疆文聯工作。
“老王,千里為官只為錢啊。”一個從安徽到新疆的農民對王蒙開玩笑說。王蒙笑道:“‘大躍進之后,安徽的生活特別困難,他們聽說新疆好點,就跑來丫。他意思說,你北京那么遠都跑來新疆,反正就是為了錢嘛。我也沒法跟他解釋。”
思想/愛情
但王蒙并非只沉浸在舊時光中,他甚至愿意去看看《失戀33天》《男人幫》這樣的影視劇,“各種現代建筑,城市風光,汽車多了,霓虹燈也多了。另外,它們的共同點就是現在人們對愛情的態(tài)度,更務實一點,不那么悲情了,不考慮你死我活那種勁兒了,不行就拉倒,還能怎么辦。這也是更豁達和更健康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他說。
在自傳中,王蒙也曾寫過自己的愛情,在北京東四區(qū)委工作時認識的初戀崔瑞芳,日后成了自己白頭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兒3月23日去世,”王蒙沉重地說。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干革命工作,“一個人怎么發(fā)展,是各種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后來有很大變化,也可能最后沒變化。”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本投降,大家對國民黨抱的希望特別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貪宮污吏什么的。”王蒙回憶起自己的革命出發(fā)點及與政治的結緣。當時,王蒙從五年級直接跳過六年級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國時期中學有打壘球的傳統(tǒng),三中有一個矮胖、愛笑的“體育明星”,專門打后衛(wèi)的,王蒙還記得那是一個叫何平的高二學生。而王蒙自己剛參加了全市的演講比賽,是個“演講明星”。
一次在操場上碰面,何平問:“王蒙,你最近在看什么書呢?”王蒙說了幾本書名,但隨后他又突然說:“我現在,思想左傾!”回憶起來,王蒙也覺得當時“非常奇怪”,“在國民黨時期宣稱自己思想左傾是有一定危險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黨員,“他眼睛頓時睜大,高興得不得了,讓我上他家玩去。他家里擺的都是一些蘇聯小說,左翼的這些東西,還有上海出的一些罵國民黨的書,他們家變成了我的學習室。”
王蒙回憶說:“如果我不是偶然說出思想左傾,他不會那么快對我宣傳共產黨的方針理論。”那一年,王蒙11歲。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2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