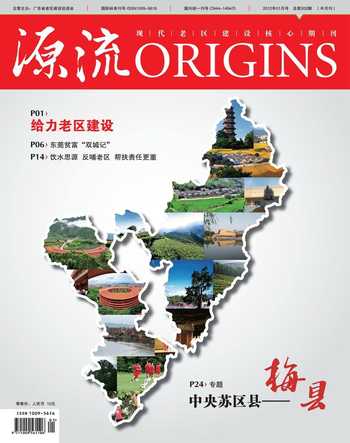但得夕陽無限好
梁水良
這是位可親可敬的老人。
1993年,他從海豐縣縣長位置上離休后,陸續擔任了縣老促會會長、縣老干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會長、縣兩縱老戰士聯誼會副會長、縣老齡委名譽主任等多個被冠以“老”字的職務,被朋友們戲稱為“老字號”。
如今,髦耋之年的他仍為發展老區奔走不息、鞠躬盡瘁,他就是海豐縣老促會會長、原海豐縣縣長曾向奇。
晚來偏愛“老字號”
海豐縣海城鎮。陳炯明都督府邸。
這座黃色外墻的西式建筑,與北側宏偉氣派的紅宮紅場,遙遙相對。昔日的名人府邸如今己掛上琳瑯滿目的“老字號”牌子,有縣老促會、縣關工委、縣“兩縱”(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老戰士聯誼會、縣老年體協等單位。縣老人書畫協會、馬思聰學術研究會等團體也在這里辦公。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這里儼然成了曾向奇的第二個“家”。
15年來,不管春夏秋冬,也無論寒來暑往,除了外出辦事,他每天都準時到這里上班,風雨無阻。誰也想不到,離休后的曾向奇會與眼前這座見證民國風云一段歲月的府邸緊密相連。
老促會是曾向奇一直傾力做好的工作。
二樓右側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是老促會的辦公地點,也是曾向奇去得最多的地方。狹窄的空間,簡陋的陳設,除了兩架資料木柜和四張破舊的辦公桌外.再也沒有什么別的東西,就連泡茶的用具也沒有。
“來這里主要是處理事情,并不是來享受,有個地點就行了。”曾向奇不介意辦公條件的簡陋,面對外人不解的眼光.總是報以會心的一笑。
采訪中,不時可見其他協會的人員進來找他匯報工作。曾向奇告訴記者,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老部下.都是德才兼備之人,只是望著這些熟悉的面孔,他有時會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之中。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上世紀八十年代,坐上縣長位置的曾向奇,與縣新一屆其他領導班子成員發現,他們面臨的是一個極其嚴峻的局面。當時的海豐縣還沒有完全從文革劫難中恢復,又陷入“走私重災區”的陰影。雖然不能說滿目瘡痍,但起碼稱得上是百業待興。他和班子成員審時度勢,抓住當時最迫切的縣城“用電難、行路難、通信難、飲水難、上學難”等“五難”問題,逐一解決。
于是,一系列被后人稱為“爬坡”的舉措,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1989年,海城穿城路,即廣汕公路海豐段改擴建工程順利竣工。這是當年全省第一家采用民辦公助模式修建的路段,開風氣之先。省委省政府因此特地將“全省公路建設現場會”選在“條件最差困難最多成績最大”的海豐縣召開。
同年,縣政府籌集50萬美金從德國買回技術先進的電信設備,又使海豐成為當時全國第一個開通萬門程控電話的縣。
隨之而來,三個11萬伏大型變電站投入使用,名園自來水廠和青年水庫自來水擴建工程竣工,一批中小學校建設工程上馬,用電難、用水難和入學難等問題也得以及時緩解。
兩屆縣長,6年任期,2000多個工作日,當曾向奇還沒來得及將目光投向心之所系的廣大農村時,驀然發現,己是“人到碼頭船靠岸”。他就像一個戰場上的將軍,正蓄勢而發,拔劍出鞘,親自帶領著自己的部隊沖鋒陷陣之際,卻得到自己必須離開戰場的通知一樣。
理解了戰場上的將軍,你也就讀懂了當時的曾向奇。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其名篇《岳陽樓記》里提到的一句名言。但在共產黨員曾向奇的眼里,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干部,既沒有“廟堂之高”,也不會有“江湖之遠”。職務可以退.但為人民服務的事業不能退。他甚至找出“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生”這句入黨誓言,來印證他自己的觀點。
這大概也是他晚來偏愛“老字號”的原因和永不停歇的動力吧。
“良心”彰顯愛心
面對耄耋老人的非常之舉,或許您會有諸多的疑問。
但答案極其簡單——“臺下的我只是想補償臺上應當辦而沒能辦的事。”
細心的人發現,從縣長位上退下的曾向奇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農村,他經常深入邊遠山區,就如何發展當地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進行調研,回來后寫成書面報告送給縣委縣政府領導作為決策參考。擔任老促會會長后,他察看了全縣230所小學,行程近10萬公里。在老促會的爭取配合下,省撥資金2220萬元,社會集資3900萬元,改造破危小學74所,新建校舍38000 平方米。
老促會還在省、市老促會和縣委縣政府關懷下,多方籌資150多萬元,資助1400名烈士后裔就讀大專院校。協助有關部門先后組織輸送四批其220名貧困生,到廣州等職業技術學校接受免費培訓,以期達到“培訓一人,輸出一人,脫貧一戶”的目標。
談話至此,曾會長意味深長地說:老區的廣大農村更需要外人關注。
地處偏遠山區的公平鎮余坑村,是大革命時期彭湃鬧革命的“堡壘村”,解放后一直存在路難行的局面。曾向奇兩次實地調查,與當地政府商量解決辦法,終于讓一條硬底化水泥公路通到該村村口。
平東鎮衛生院一度被人戲稱為“三無醫院”:沒有固定的病房和辦公地點;沒有固定的駐院人員,醫生是從相鄰的公平鎮衛生院派人過來承包的,沒有基本的醫療設備,全院只有“一支聽筒和一支溫度計”。如今,在老促會的協助下.已經建起了氣派的手術室和辦公大樓,派駐有12名醫護人員,設備齊全,達到“小病不出鎮”的要求。
聞名遐邇的黃羌虎噉黃花菜,也是在老促會幫助下發展起來的。一次,老促會到黃羌調研,得知當地種植的黃花菜市場潛力大,為形成規模效益,老促會配合有關部門在當地開辦免費的農民技術培訓班。
海陸豐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誕生地,是農運領袖彭湃的故鄉。為了挖掘革命歷史史料,同時也是為了教育激勵后人,曾向奇與林澤民等人還發起了“老戰士尋訪革命遺址”大型戶外活動。在革命老人的努力下,朝面山紅二師改編地、紅軍戰壕、抗日自衛隊總部、徐向前指揮戰斗過的遺址等一大批革命遺址終于呈現在世人面前。
老促會還專門組織了編審組,與縣黨史研究室、縣關工委等單位聯合,編寫出版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考證》、《海陸豐革命歌曲選輯》、《近代海豐名人(一)》、《名人名句擷英》等一大批書籍,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革命史料。
前進路上,投來眾多旁人的目光,有贊許,有不屑,但更多的是不解。但曾向奇全然不顧,因為他已堅定了自己未來的方向。
回想剛離休的頭幾年,特區有幾家民營企業開出豐厚的條件,想聘請他前去當顧問,但他都婉言拒絕,他從不后悔,他說留在家鄉發揮余熱,是對老區的補償,也是對自己人生的“補課”,他甚至認為自己所作的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民心工程”。
養生秘訣“三忘記”
善于忘記,有時也是一種幸福。
八十高齡的曾向奇容光煥發,精神飽滿,神采奕奕。他談吐思維敏捷,說話聲音洪亮,行走健步如飛,絲毫不亞于年輕人,除了頭發灰白外,一點都不顯老。
這得益于他的“三忘記”養生哲學。
所謂“三忘記”,曾向奇是“忘記年齡,忘記官位,忘記恩怨”。
每個人都有三個年齡層次,即實際年齡、心理年齡、生理年齡。有人把年齡當作秘密,不喜歡告訴別人自己的真實年齡,而事實上即使知道了一個人的實際年齡,你也不一定能知道他的“心理年齡”,這代表一個人心理成熟的程度,比如說,30歲的人由于經歷的事情較多,很可能擁有40 歲的成熟的心;而80歲的人也可能會像“老頑童”一樣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老當益壯的曾向奇,常常忘記自己的實際年齡——因為他擁有一顆年輕的心。
曾向奇的一生亦可以“少年坎坷;青年拼搏;壯年任重;老齡奉獻”概之。少年時逢日寇侵略中國,家鄉倫陷,人民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1949年剛成年就投身革命隊伍,毅然參加粵贛湘邊縱隊東江一支隊五團,從小戰士逐步成長為團文書。
1982年,戰爭年代歷經磨練的他挑起全國聞名的走私嚴重的沿海重鎮田墘鎮黨委書記,正因曾向奇同志在反走私的戰場上力挽狂瀾,成績顯著,1982年被指名與廣東省組織部負責同志一共三人參加全國組工會議,并安排第七位在大會發言,介紹整黨、反走私斗爭典型材料。1985年,正當壯年的曾向奇同志被任命為四鎮合一的海城鎮黨委書記,在任上被推選為六年之久的海豐縣副縣長、縣長。1993年離休后牢記自己是一名永不退休的共產黨員,代表黨的良心,勇當黨、政的參謀、助手和橋梁。
從縣長到會長,一字之差,卻是兩個不同的角色。前者位高權重,后者可能只是一個無權又無錢的“虛職”,曾向奇坦言自己早就實現了角色轉換,忘記從前當政府“一把手”的身份。他現在思考得最多的是如何當好領導的參謀,更好地搭起領導與群眾溝通的橋梁。
人是感情動物,有自己的喜怒哀樂,生活中或是工作中難免有磕磕碰碰,是非恩怨,尤其是從“文革”中過來的那一代人,歷史的誤會或多或少都會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陰影。只有忘記生活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以豁達大度對待一切,才能摒棄心靈之累……。
說這話時,曾會長將眼光投向海闊天空云卷云舒的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