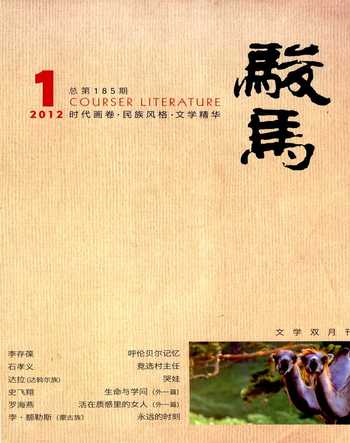生命與學問(外一篇)
史飛翔
1977年生,陜西省乾縣人。1994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后在《山東文學》《東京文學》《延安文學》《駿馬》《西部散文家》《中外文藝》等文學期刊及全國各大報刊發表文化散文、學術隨筆100余萬字,并被《讀者》《青年文摘》《書摘》《讀書文摘》等知名雜志大量轉載。出版散文隨筆集《為靈魂尋找鏡子》《紅塵心語》《讀書與冥想》《有一種沉默叫驚醒》等。有多篇作品先后入選《大學語文》《高中語文閱讀欣賞》等大中小學教材及各種權威選本。獲美國《世界華人周刊》“世界華文成就獎”。
生命與學問
作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書的自序中曾這樣發問:“我們這些人,為什么稍稍有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么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么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么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游戲總是對立,那么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與秋雨先生一樣,近年來我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生命與學問。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年來我先后慕名拜訪了國內不少學術大家,所得是主要的,但困惑同樣存在。在與這些名流的接觸中我發現,如今不少學人,學問固然做得很好,但身上總有一種叫人難以言喻的官場氣、商場氣、學閥氣、市儈氣,油腔滑調、兩面三刀、阿諛奉承、八面玲瓏,很有政客、商人、公關家、外交家的風度。除了那一個個耀眼的光環和虛假拿捏的舉止,在這些人身上你嗅不到任何學問與生命的氣息。失望之余,難免要感慨,不知從何時起文字變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學問竟演化成一種單純的利祿工具?
孔子有一句話叫“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在我看來,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古代學者學習的目的在于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而現代學者的目的卻在于裝點門庭、好為人師。學術究竟是為己好呢,還是為人好呢?這實在是不好一概而論。有道是“著書皆為稻粱謀”,如今能在為學的同時依然堅守為道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中國傳統學術的精神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識。中國知識分子的成就也在于行為而不在知識。中國人讀書不是為了知識,而是為了完善道德人格。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人各以其一身挑盡古往今來的擔子,以養成涵蓋萬匯的偉大人格。這說明,在中國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追求自然界的純知識的為物之學,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命、生活的重道德的為己之學。
梁漱溟先生說過這樣一番話。有學問的人,沒有覺得學問是復雜的,在他們身上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很輕松,真是虛如無物。如果一個人覺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學問的樣子,則這個人必非學問家。不僅如此,梁先生還結合自己的治學心得,進一步說,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學問家。真學問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獨到處,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在學問上結論并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并不重要一樣。在學問里面你要能自己進得去而又能出得來,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是被書本知識所壓倒。若被書本知識所壓倒,則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古人云:灑掃、應對、進退,即是形而上學。又云,下學而上達。故,凡對人情事理有所悟者,就是很大的學問。梁先生不愧是真學問家,他的這番話真是見道之言。費孝通先生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談到梁漱溟先生何以能成為思想家時說,做學問其實就是對生活中發生的問題問個為什么,然后抓住問題不放,追根究底,不斷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學問的目的不在其他,不是為生活,不是為名利,只在對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個究竟。
近代學者王韜曰:“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中國學術與西洋學術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于,中國學術是要使生命成為一種智慧,而非智慧奴役于生命。這既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藝術——一種人生的藝術。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是如何讓生命活得更舒適、愜意。
讀了三十多年的書,到今天才算是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人世間所有的學問歸根結底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換句話說,叫學為自得。
學問與氣象
英國哲學家培根在他那篇著名的論說文《論學習》中寫到:“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培根這話扯出一個問題——學問與氣象。學習究竟能不能陶冶性格,或者說學問是否真的就可以改變氣質呢?
古往今來的學人或專一史,或守一門;或發前人之覆,或成一家之言;或觸類旁通,或高瞻遠矚;或獨辟蹊徑,或開疆破土;或成專家,或為匠師;總之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就喜好而言,有人喜體大思精、茹古涵今;有人愛蓽路藍縷、起例發凡;有人善縱橫百家、洞燭幽微。學術規范是共性的,但學術精神的外在表現則明顯是帶有個人色彩。比如,同為“五四”時期的人文學者,胡適清澈、周作人駁雜、錢玄同高古、劉半農有趣、沈兼士平淡、廢名神異、俞平伯平實,差異竟如此之大。其實這還是就正常的一般差異而言,若論一些怪異之舉,則更是標新立異、驚世駭俗。比如:阮籍的青白眼,溫庭筠、柳永的放浪形骸,徐文長的殺妻,李贄的自殘,米芾、倪云杰的潔癖,陳獨秀、郁達夫的嫖妓,辜鴻銘的怪誕。今天的學人雖不至瘋狂如此,卻也時有令人心痛之處,那就是學問的異化。
人世間的學問原本只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使人更能像一個人那樣體面而有尊嚴地活著。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今天學識已等同于迂腐、教養已演變成鄙俗、智慧已異化為狡詐、德行已淪落成虛偽。看看我們今天的一些學者,謙謙君子、溫文爾雅,動輒以思想者、公共知識分子、某某形象代言人、某某學派、某某主義自居,頻頻出現在報刊雜志、網絡電視上,面對公眾口若懸河、神采奕奕,再加上隔三岔五地出上那么一兩本暢銷書(多為“米不夠水來湊”),簡直堪稱是“道義的良知”、“學問的化身”。然“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察其言、觀其行,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讓人覺著不舒服。仔細一想,不對呀,這個人的文品與他的人品不一致呀!類似這樣的“人格分裂”,你能說還少嗎?
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界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說法:“自從明朝結束,乾嘉學問(派)形成后,中國的學統就斷了。清朝以來,全部學問都沒有了,只剩下《說文》《爾雅》。《說文》《爾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學、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嗎?都不能。那中華民族的生命憑藉什么來應付環境,應付挑戰呢?所以恢復這生命的學問,恢復這中國老傳統、大漢聲光、漢家威儀的,是熊先生;把從堯舜禹湯文武一直傳下來的漢家傳統重建起來,是熊先生的功勞。”熊先生的學問一向被稱為是“生命的學問”。熊十力先生在一封寫給張立民的短札中這樣說:“中外古今學者殆無不經過從不知天高地厚傲然自足之中、忽起空虛與恐慌、然后向上求進、以成就其人格與學問者。唯在空虛與恐慌之階段、卻甚危險、非有大量、即不能向上求進以生、只有陷入空虛恐慌以死。”熊先生所講自是體悟之言,可惜今天的學人只怕是少有“空虛與恐慌”,更遑論“人格與學問”。同樣,朱光潛先生在《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一文中也說到:“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一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所觸藉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獨到的風格,世間也只有這種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朱先生這里談的雖然是文學,但學問亦是此理。
學問要轉換成氣象關鍵是要在“濡養”二字上下功夫。北大教授袁行霈認為構成學者個人氣象和風范至少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敬業的態度,對學問十分虔誠,一絲不茍;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長,不攻人短,不存門戶之見;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潛心學問,堅持真理,堂堂正正。這三句話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古人常說的:“學問深時意氣平,精神到處文章老。”
(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