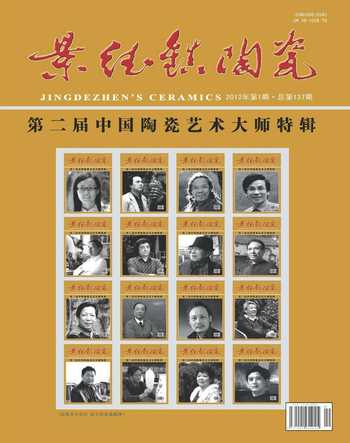略談粉彩花鳥畫創作
程美華 傅小平
景德鎮粉彩瓷創造于康熙末年。粉彩藝術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步入民國一直延續至今,不停地吸收借鑒著其他藝術營養得以更好地發展。它是一種非常柔和的色彩表現,在色彩層次上,抓住了自然界色彩變幻的根本,強調色彩過渡這一特征,粉彩藝術的興起同歷史的發展密切相關,粉彩在人物、山水、花鳥、走獸等領域各具自身的藝術風格。他們共同之處在于注重工藝的完美結合,注重文化素質的積累。粉彩花鳥畫創作和其他畫種一樣,要經過生活實踐、題材構思和藝術塑造等幾個主要步驟。
首先要求創作者必須熱愛大自然,經常不斷地深入大自然,體驗生活,熟悉生活,以敏銳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及時發現和捕捉那些曇花一現稍縱即逝的花鳥生活形象。還要結合進行一些必要的速寫與默寫,以積累素材,為創作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所謂:“身所盤恒,目所綢繆”,“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宋?宗炳《畫山水敘》)就是這種意思。
創作一幅粉彩花鳥作品,主要有立意、構圖、創作、整理幾個步驟,要確立賓主、虛實空間、疏密得當。題材的構思,最講究表達畫者的“意境”,要求“意在筆先”。“意”是指通過對花鳥藝術形象的塑造所表達產生的藝術效果,就是“意境”。所謂“意境”,是一種內蘊的美,貴在含蓄。但這種含蓄,并非隱晦,它雖藏猶顯,能使人味而得之。好的花鳥畫意境,能使作品余韻繞梁,耐人尋味,發人深思。傳統的花鳥畫善于“以無寫有”,在畫面上給觀眾留下想象的余地,讓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去尋找“景外之趣”。賓主關系是說一幅畫上的景物要有主次。方能層次分明。賓是為了陪襯主的,有主無賓的孤立一朵花固然不好,主次不分的一律平均對待,也不能引起美感。如果把次要的東西放在突出的位置,反而忽略了主要東西當然是不可取的。瓷畫構圖中正確的賓主關系,應該恰如其分,相得益彰。在表現方法上,主,必須居于顯著而突出的地位,突出的方法,或以色彩、或以動態,把觀者的視線吸引過去。賓,要作為主的陪襯,切忌喧賓奪主。在位置擺布上,主,不一定都要放在畫面的中間,有時可放在畫面的一角,這時大面積的“賓”運用構圖的動勢,把觀者帶到“主”的一角上去,這樣更有趣。“主”有時面積很少,地位不顯眼,但運用得靈活巧妙,會感到很有情趣。虛實關系,沒有虛實就不成畫面,畫面虛實關系處理好了,就層次明晰,有深度。虛實關系是瓷畫構圖中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虛實是一個概括說法,具體地講它應該包括:多與少、疏與密、聚與散、繁與簡、清與濁,甚至用筆的輕與重,強與弱,用墨的濃與淡、枯與潤,無一不與虛實有關。虛與實的關系,在傳統的畫論中叫“虛實相生”。如畫面上只畫幾根蕭疏臨風的蘆葦,一對凌空鼓翼的歸雁,就會使人聯想到秋水長天;只畫一樹蒼松挺秀的紅梅,數竿枝葉灑脫的墨竹,就會使人聯想到豐年瑞雪。這些能讓人產生的“意境”,會讓觀者感受到些許趣味,如果面面全盤托出,畫得滿滿一覽無余,反而會降低這種“妙在畫外”的藝術效果,反會使人產生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的反感。
傳統的粉彩花鳥畫創作對花鳥的形色特征、對畫面的處理都很考究。要求畫者在主題內容及藝術形象表達上,都要符合生活的真實,中國畫史上有許多這方面的生動故事記載。這樣做是科學的,也是必要的,但在花鳥畫創造“意境”上,并未完全被這種生活的真實所約束。對畫面處理,則強調借景抒情,把畫者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見解,貫穿于整個對客觀事物的表現過程,不管主題內容或藝術形式,都允許跨越和突破生活的真實,發揮想象。如牡丹象征富貴,與白頭翁合畫稱為“富貴白頭”;松鶴象征長壽;鴛鴦象征愛情;鴿子象征和平;綬帶鳥諧音為壽帶;飛鷹象征“鵬程萬里”;喜鵲表示喜慶,與梅花同畫則為“喜上眉(梅)梢”,或“雙喜迎春”等等,都融合了強烈的花鳥畫內在意蘊。那些歡樂相聚的山雀,相尋相覓的小鳥,戀歌起舞的孔雀和呼喚春意的雪雞,以及鼓浪而起的鯤鵬,都在大自然中的舞臺演繹自己的故事。如果離開這些情趣和意境,粉彩花鳥畫裝飾性的追求就會失去光彩,失去詩意,變成單調的裝飾畫了。當然,如果一種形式不能表現意境,那就意味著這一形式本身需要更新與發展,這才有創新的必要與可能,這就是我們對花鳥畫創新的思考動機。意境和形式的高度統一,強調意境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創作方法,道出了東方藝術的千古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