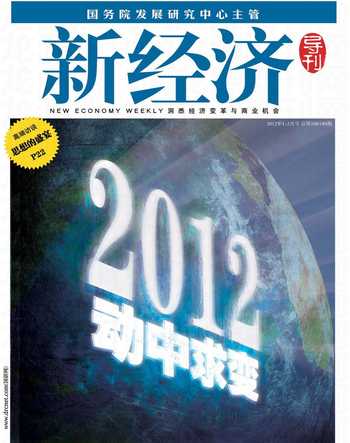2012:動中求變
朱敏



[年度特輯]
全球經濟從波瀾不興到驚濤拍岸,漸成動蕩之勢,而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變革之需益發迫在眉睫
對于2012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主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為四個字:“穩中求進”。這一表述不難理解,就是在實現宏觀環境保持相對平穩(經濟“軟著陸”)的前提下,側重于結構調整和改革突破即“調結構、抓改革”。有所巧合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在對2012年中國經濟進行展望時,我也想到了四個字——“動中求變”。
值得一提的是,“動中求變”雖然乍看與“穩中求進”在字面上有所不同,實則基調與之并無二致:“動中”是對外部動態環境的客觀描述,“穩中”則是宏觀政策力求達到的一種取向;而“求變”與“求進”在此則是同一個意思,即變革、改革、轉型之意。
其實,本刊2009年新年特輯的關鍵詞就是“重構規則”。我在前言中寫道:經歷了2008年經濟社會接踵而來的突發變故之后,格局的洗牌和規則的重構,更成為一種物極必反般的必由之徑。并斷言,“變革”定會是2009年的中心語:“要變革現狀,就必須重構規則。由此,變革與重構,便成為2009年經濟社會的精神內核,以及商業創新的有力支點。”
彼時正是國際金融危機發軔與蔓延之時。至今三年間,全球經濟從波瀾到驚濤,漸成動蕩之勢,“變革”之需益發迫在眉睫。2012年元旦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湖南調研經濟運行時強調,“穩中求進”的“穩”不是不動,而是要穩定增長,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同時還要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步、技術改造的進步、管理和效益的進步、改革開放的新突破。
有關改革或發展方式轉變,近些年流行一個詞叫做“綠色轉型”。那么,中國經濟怎樣才算綠色轉型?除了通常所說的環保、低碳等訴求外,以我的理解,就是轉到讓人們不光“吃得飽”,還要“睡得香”。在今日中國,作為財富創造者的企業家,雖然不乏有人在收益豐盈的狀態下將收獲的財富投入慈善事業或社會公益、讓更多人分享其快樂,但蕓蕓“飽食者”之中,又有幾個人敢說自己睡得香、晚上還能美夢連連?
“睡不香”還算好的,要是“睡不著”就更麻煩了。中國不在少數的企業家現在處于“睡不著”的狀態,這就非常麻煩。沒錢的時候煩,煩肚子餓;賺錢的時候也煩,要動手動腦;有錢的時候可能還更煩,煩的是沒有財富安全感,煩的是從身體到心理存在著一種亞健康,煩的是各種各樣的危機,尤其是企業永續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危機,或者二代接班的困惑,出現迷惘、麻木、焦慮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早在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發布的“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家有時出現或經常“煩燥易怒”的占70.5%,“疲憊不堪”的占62.7%,“心情沮喪”的占37.6%,“疑慮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強”的占28.6%,“悲觀失望”的占 16.5%……盡管企業家群體積累了超出常人難以想象的財富,他們卻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樣幸福。
經濟轉型的核心,很大程度上要看企業生存狀態能否得到改善。換句話說,首先要實現企業家的心智與精神狀態的健康轉型。那么,究竟如何綠色轉型、健康轉型?可能會有很多路徑,卻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但是,所謂經濟社會的轉型,除了發揮政策的正確引導以外,這時我特別想強調一個觀點:還要充分信任企業家、尊重企業家,營造一個陽光的企業家成長氛圍,自主發揚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及企業家的創業精神。而且,也只有發揚“企業家精神”,我們才能在經濟舞臺上各司其職唱好這出“主角”的大戲,跟上新時代浩浩蕩蕩的經濟潮流。恰恰在這一點,在我們急功近利的氛圍內,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實際上,“企業家精神”不光是對經濟轉型的中國經濟非常重要,對全球來講都非常重要。最早強調“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家是熊彼特,在學術領域里面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那就是: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長期擁有活力,根本就在于創新。而這個創新的來源,究竟在哪里呢?這可能就涉及到剛才說的“企業家精神”,他著重強調的正是這個。與此同時,他也創造了一個“創造型毀滅”的詞語,來描述市場活力來源和經濟發展規律。他率先把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引入到經濟學當中,最早闡述了創新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值得一提的是,“企業家精神”不僅僅是產生于像微軟、摩托羅拉這些富有能量和規模的大公司,實際上,甚至像諸如大學宿舍、地下車庫等等毫不起眼的地方,也可以產生“企業家精神”。
中國明確提出的目標,可能是10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要成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我們對創新的投入其實也非常巨大,在產業扶持、人才引進等政策上,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支持。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際上創新是一個結果意義上的東西,而非手段,如果只靠大量的資源資金的投入,既是不夠的、也是浪費的。問題其實還是存在于機制上面。更本質來講,可能有更為鮮明的一個觀點,那就是創新其實是無法人為地、主觀地造出來的,創新應該是市場需求與“企業家精神”結合的產物。當我們蜂擁搶購蘋果iPhone手機,驚嘆于技術的創新和神奇的創意,我們應該深深地知道一點,它是如何拿捏市場的需求;同時,我們千萬不要忽視喬布斯們留給世人的非物質遺產,只有它——“企業家精神”,才是那只“看不見的手”背后另一只無形的“幕后推手”,控制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優化配置資源,它才是市場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因此,企業家無疑是市場當之無愧的主體、理所應當的主人。可惜的是,并不像“看得見的手”投入的資源、資金和產出的GDP那樣易于量化,“企業家精神”很難量化。盡管如此,仍有不少學者在嘗試做基于實證的數理研究,為“企業家精神”獲得更多認同提供理據支持。
“企業家精神”是誘發和促進制度變遷的基礎因素,也是技術創新的巨大動力,我們應著力從制度安排上來培育“企業家精神”。尤其在當下“中國特色的凱恩斯主義”如此強而有力的情勢之下!談到這里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傾向或誤區,就是有些人坐井觀天,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中國特殊制度的優越性,認為自己沒有受到正面沖擊,而且比美國等國家更能應對自如。實則不然,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商榷。不妨打一個比喻:你看到別人游泳時不小心嗆水,就為自己不會游泳而竊喜。這種價值判斷本身,我不認為是一種健康的心態。殊不知,你沒嗆水是因為你不會游泳,是由于你落后啊。中國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沒有受到正面沖擊,道理不也是這個嗎?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都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為優勢總結。在全球化大潮里,“游泳”的本領你是必須學會的。
今天,我們仍然要補市場經濟的課。所謂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通過權力的層層干預,追求經濟增長的規模與速度;而市場經濟的要義,則是在保障私有產權的前提下,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實現財富創造的持續與共享。但凡市場競爭充分、產權結構清晰的國家,必是市場成熟、社會多元、權力受限的國家;而集權傳統濃厚的國家則會通過權力干預的途徑壟斷社會財富。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競爭、權力制衡基礎上的政經體制,方可適應日益開放和多元化的大勢,激發企業家、管理者、技術精英、生產者們的創造才能,并通過基于自愿、協商的“動態和諧結構”,協調該體系內人們各種才能和積極性,也就是“企業家精神”或者叫企業家才能。
然而,依然存在的林林總總對企業的制度性強制或管制,以及愈演愈烈的政府競爭模式和官商結合模式,正是阻礙和抑制“企業家精神”的主要因素。這無疑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重視。
2009年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低谷,開始復蘇回暖;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這些停留在速度和總量層面上的利好數據,只是由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制造的數字神話,不但對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改進民生沒有更為實際的意義,且與高層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包容性增長(共享式發展)也是非兼容的。關于政府競爭的模式,可以通過類比的方式來理解:如果說,土地交易是房地產業的一級市場、房地產開發建設只是二級市場,那么政府競爭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級市場,而市場競爭只是二級市場。這種政府競爭模式和凱恩斯語境下的宏觀調控有著本質的區別。凱恩斯的宏觀調控本來只是反危機的一系列強有力措施、一時的應對之策,但政府競爭模式卻把它常態化了。
在政府競爭模式下,各級黨政機關不但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個以黨政一把手為核心的強制運行體系,直接參與微觀層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輿論媒體、社會公眾的有效監督往往“被缺位”,市場的自我修復功能往往“被缺失”,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微觀企業,只能跟著一只“看得見的手”(或被這只“手”牽著)走。
政府競爭模式有兩個層面的邏輯解釋。一種是由官方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延伸出的“用發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另一種是“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官員升遷規則,但兩者導致的結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為特征的掠奪式發展。在實踐中,地方政府官員之所以沒有做到科學發展,并非因為官員本身存在認知上的缺陷,事實上,官員如何會不明白土地財政、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危害或“后勁”呢,只不過,在決定他們命運的選官體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為之”。
盡管在法律上官員是由人大選舉產生的,但實際中,人大往往只在組織部門做出任命決定后履行一個法律程序,更何況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主任和黨委一把手本來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屆地方政府都喜歡搞“三高一低”、“鐵公基”這些皆大歡喜而又立竿見影的工程,根本沒有動力去發展科、教、文、衛這些“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長期事業,豈能不知改變一個國家命運的乃是科學與教育?特別是基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創新型國家建設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尤為重要。
在此過程中,土地、財政、工商、稅務等部門往往較為強勢,而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則被冷落。與此相應,在全國范圍內,每個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異,有自然資源的地方通過企業改制招商引資,沒有自然資源的則從歷史上找文化資源,歷史上實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西門慶故里”之類,居然也爭先恐后地要打造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資源或文化資源之外,還可以先制造出類似于“經濟圈”的概念,先通過概念抬升土地價格,然后順理成章地大興土木。可見,在政府競爭模式之下,中央調控房價變成“空調”、節能減排變成“拉閘限電”、拉動內需變成“屢拉不動”等現象,其實不難解釋;而資源賤賣、環境污染、產能過剩、安全隱患、土地財政、形象工程、貪污腐敗等問題頻頻發生,也就不足為奇。
政府競爭模式造成兩個非常嚴重的后果:一個是生產要素價格被制度性強制扭曲后的貧富懸殊問題,以及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另一個是對社會矛盾長期的“封堵”,為大規模社會矛盾爆發埋下隱患。
土地、資源、環境、勞動力、技術是發展經濟最主要的要素,經濟要素的價格應由市場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決定。但在現實之中,土地和行政資源因政府壟斷而價高不下。產業結構直接由政府決定,導致勞動力和技術價格無法反映市場需求。土地在一級市場的招拍掛制度,從表面看似由市場定價,實則這種單一供給模式抬高了土地價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尋租空間。這種一級市場政府壟斷,二級市場、三級市場則市場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結合的直接誘因,也是政府競爭的直接動力。
在政府競爭模式下,資源和環境經常被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砝碼廉價出售(甚至無償使用),當這種掠奪式開發的后遺癥開始顯現時,從中受益的官員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來,問責制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了。由于政府直接決定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其實相當于間接決定了要素價格。但是,教育的結構調整和市場的自發調整機制往往趕不上政府改變政策的步伐,從而導致就業市場的大起大落和要素價格的畸形。全國的現狀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過剩、政府投資的“鐵公基”項目過剩、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嚴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領過剩導致的工資水平偏低和嚴重的大學生失業,另一方面是藍領短缺引發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資本和技術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層次邏輯,正是經濟社會活動中的行政干預所造成的非兼容問題之冰山一角……
與此同時,在近些年的“官進民退”背景下,政府通過行政壟斷,將銀行、石油、電信、電力等真正值錢的產業都掌握在手,私人企業要么經營鞋、服裝、電器等低附加值,且無須權力、資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權力,與政府官員或者國企領導編織一條“食物鏈”,比如經營房地產,或者石化、金融等壟斷行業的下游產業。然而,低附加值的行業不但不易賺錢,而且備受需求市場的影響,相反依附于權力卻能獲得無風險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江浙粵等地大量虧損的實業資本轉入房地產后,在接下來的房產大牛市中賺了個盆滿缽滿,其實就是從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權力不直接創造財富應是常識,市場經濟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識,但權力通過壟斷能讓自身成為最“貴”的要素,這種權力造成的財富逆向分配反過來強化了官商結合的模式。
“官進民退”造成國企改革的倒退,這也是權力越過界限,導致市場經濟與強權政治產生非兼容問題的明證。現在許多人寄望于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深化改革,但有一點不可忽視:事實上,國企改革的首要問題,并不是國企作為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的改革,而是國企經營管理權的改革,亟需解決國企的定位與監管問題。
不妨以通過發生在過去一年里的兩件熱門事件說明這個問題:2011年初,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涉嫌違紀被免職,隨著他的落馬,中國高鐵“大躍進”熱潮開始降溫。劉志軍無疑只是中國落馬的腐敗官員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國鐵道部的行政首長,還是政企不分的“鐵老大”的大老板。雖然這樣的雙重身份也意味著他有雙重目標:既要提高鐵路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為鐵路企業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實上,由于國有資產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運行過程中的監督缺位,這兩個目標他都可能無法實現、也不必實現,轉而追求個人短期利益目標。
另一件事,則是中石化廣東分公司的“天價酒”事件。換個角度看,此類事倘若發生在私企會是怎樣,無論私企發生這種事情概率多么小。如果是中國一家上市私企,為不影響股價也可能會做內部處理,但對當事人絕不可能降職留用,對“泄密者”則一定會有所獎勵,無論泄密者出于何種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業,一定會通過司法途徑追回損失,并將當事人繩之于法。但這種邏輯在中石化卻變成了自查自清和嚴懲泄密者。更奇怪的是,這樣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億元的利潤躋身“中國五百強”之首。同一個市場,不同的游戲規則、不同的利潤回報,究其原因,當然應該看到,國家將具有巨大經濟價值的資源無償或低償授予了壟斷國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資源稅和資源使用費。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在于:權力集團為了完成對超級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權貴資本和家族壟斷。
事實上,官商結合模式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政府本身就是“商人”,直接經營企業;另一個是,政府雖不直接經營企業,但卻越過市場,直接決定資源與財富的分配。因此,從廣義上看,“官進民退”不但指國企和私企的進退關系,也包含公權力膨脹、私權利萎縮,這是一種結構上非兼容造成的問題。在官商結合的模式下,無論企業還是個人,最大的動力不是發揮自己才能和積極性去創造財富,而是通過接近權力、綁上官員直接食利,這種與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非兼容的模式難以造就優秀的企業家,但卻會形成一個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權貴資本集團。它不但破壞市場規則,而且逐漸成為一股能夠左右歷史走向的強大勢力。
因此,回過頭來,我們要說,企業的永續經營,經濟的長足發展,終究都要靠“企業家精神”,才能永葆活力。我之所以如此強調“企業家精神”,實在是因為國內對這一塊的重視不太夠,我們的所謂創新一直處于自上而下的供給狀態,往往不是從現實的或潛在的市場需求出發。我們也呼吁能夠從創新制度、創新體制上改變,使我們的政策盡可能朝向市場需要的導向出發,真正服務于企業家,激發“企業家精神”,從而使“看不見的手”背后這只無形的“幕后推手”源源不斷地優化資源配置。今天,中國發展新經濟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絕不能忽視“企業家精神”對真正意義上的創新的價值。
可以斷言:對中國經濟而言,不論是短期的2012年實現“軟著陸”,還是中期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十二五”綠色轉型,抑或是長期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無不有賴于激發“企業家精神”,無不有賴于營造一個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而要從根本上達成這一目標,必須重啟改革,進行大刀闊斧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創新,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以壯士斷臂的決心告別由來已久的政府競爭模式和官商結合模式,讓中國經濟社會走上真正的現代化坦途。這是我思考“動中求變”的應有之義,也可視作對“穩中求進”一種心懷期許的解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