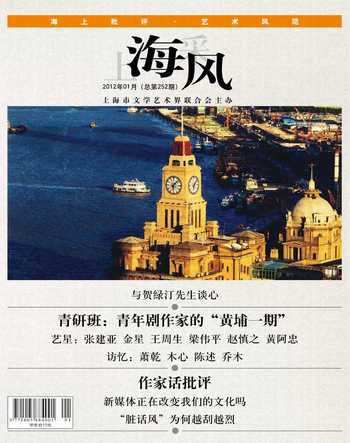作家話批評
劉莉娜

作家閻連科曾經就作家和批評家的互動關系說過一段有趣的話:“批評家讀作家的書是公開的;作家讀批評家的書卻是偷偷的。作家議論批評家,都是掛在嘴上,而且還多在批評家不在場的飯桌上;批評家議論作家,不僅掛在嘴上,還多公開在筆下的紙上。”不過最近,在上海作協的一樓大廳里,一批滬上知名的作家和批評家們卻坐到了一起,為上海作協和上海文藝出版社聯合推出的一套《新世紀批評家叢書》展開討論。不同于之前諸多場“批評家們談批評”的純理論型研討會,這次的研討會因為作家們的參與而不再顯得高深晦澀,作家們從自身的閱讀、創作體驗出發——甚至是“被批評”的體驗,更為直觀地分析了當下批評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亦更為詳實地描繪了作家們心中所期盼的健康批評生態的理想圖景。
文學評論要有年輕人的聲音
最近,上海作家協會和上海文藝出版社聯合推出了一套《新世紀批評家叢書》,在它的作者名錄中,出生于1973年的巴金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立民屬于最為年輕的,而常常被媒體稱為“青年批評家”的葛紅兵,其實已經年屆43歲,稱他為“青年”實在有些勉為其難。當代的作品誰來評判?文學評論有沒有年輕人的聲音?誰來發現更年輕的文學批評家?當社會生態發生變化時,這些出現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新現象,生成了縈繞文學界的新疑問。
趙長天:對這套叢書最希望的是我們能夠盡量發現更加年輕的批評家,現在還把像葛紅兵這樣的說成是“年輕的批評家”已經比較勉為其難了,因為葛紅兵也算中年批評家了,當然我們就更是老年人了。我們那個時代年輕人跟中老年人倒是差別不大的,但現在整個閱讀的狀態都不同了,年輕人的閱讀跟中老年人的閱讀完全不是一類的東西。
有一次《萌芽》要招大學生兼職編輯,面試的時候有應聘者非常自豪地說,我看了很多書,南派三叔(《盜墓筆記》作者)的書我全部都讀過……近百人里面只有一個人表示讀過周作人的散文,還有一個讀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書。我現在沒有資格來評判這樣的閱讀狀況是好還是不好,但如果要寫南派三叔的評論,肯定要80后的批評家吧,我們現在在座的批評家講的東西年輕作家不一定接受,因為不同年齡看法上的距離非常大。但現在沒有年輕人的聲音,80后的批評家基本上沒有。而我們非常希望的是,能有年輕人對當前的這樣一種文學創作和閱讀的狀態做一點判斷,這樣一種批評的力量,我們上海能不能有?
陳村:有很多年輕人的在線瀏覽不能說閱讀,但是從我看到的狀態講,文學有一些變化,網絡的發表變得容易。以前文學作品的發表非常困難,現在所謂的發表就是你自己網上發個帖就叫發表,現在從文學生產到所謂發表流通到實體發行在網絡上都能完成,已然實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循環。我曾經主持過2010年盛大文學所謂全球華人的原創文學大賽,在那里,一個作品可能就幾百萬字——這樣篇幅的作品在傳統文學界已經算是一個大系列,可是在那里,有那么多小青年就寫得很長,而且很受追捧。而現在的傳統文學界已經變成小說都沒有什么人看了。所以我很強調,文學批評作為工作肯定要做下去,作為學術肯定要做下去,特別是有年輕人來做下去。
上海有個年輕的小說家叫小白,到現在為止在《收獲》雜志上發表了兩部長篇小說,都是寫上海的故事:《局點》是八十年代的故事,《租界》是三十年代初的故事。這樣的作家、作品,有些年輕的批評家們,如果說你是住在上海的,也比較關心上海的,或者跟上海人結為親戚的,哪怕只是在上海付房租的,都應該關心一下。我覺得批評家的出現比小說家容易,因為每個人都在批評,在社會中批評,批評是人的天性,但創作不是人的天性,不是每個人都能創作的。就中國的年輕人來說,除了在網上做創作的那些,作協系統下的那些人的創作其實是比以前弱得多。那天看到的一個數據,上海作協45歲以下的會員只占10%,35歲以下的就更不多了,我覺得這個是有危機的。
王周生:信息溝通也是有問題的。比如找批評家開會,老的批評家沒時間,年輕的三四十歲的又不知道他們名字。其實有些老批評家,本身工作也多,或者很有名的,身價又很高,很難合作,倒不像年輕人非常認真,特別對年輕作者的作品會很有看法。我聽他們講的時候,進行過比較,我覺得年輕批評家的言論對我的啟發就很大。
文學批評不能只“說長”不“道短”
事實上,在當今網絡文化的時代,各種不同意見的發表并不難,簡單地說,“只要有良知,只要有承擔精神,就能夠發出聲音”。不過,現實中具有使命感的批評家和學者并不多。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楊劍龍教授表示:“文學批評,通俗一些來說就是對一部作品‘說長道短。”現在可見的情況卻是,大家都只“說長”不“道短”:一部新作出來,說好話的大有人在,提出值得改進和商榷意見的人卻十分罕見。文學批評喪失了辣味,淪為一道灑滿味精和蜜糖的無營養晚餐。
楊劍龍:一些學者私下里很敢言,講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立場分明。但請他寫成文章發表意見,批評者的態度就會頃刻發生變化。說白了,是因為不愿意得罪人。尤其是同行之間、圈子之內,說好容易說壞難,健康的批評總是很難形成風氣。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就是,出版了長篇小說《金牛河》以后,大概有十五六篇評論我小說的文章,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還是不盡興。不盡興的原因是,那些文章都是說我好的,幾乎沒有說壞的,根本沒有人告訴我,我的文章還有哪些是需要改進的。但寫評論就是要說長道短啊,以前我曾經給一位作家朋友寫評論,說長道短,說了他不少短處,結果讓我感動的是,他把評論拿到《解放日報》發表,把說他“長”的都刪了,說他“短”的都沒刪。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評家都要有寬廣的胸襟,因為他們是一起成長的。
王周生: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丁玲憑借《莎菲女士的日記》登上文壇后,很多人對她作品中鮮明的女性主義與個性主義姿態頗為贊賞,形容她有如一陣清新之風刮過。當時,馮雪峰卻以一個文學批評者的身份,對丁玲的作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毫不留情的、嚴厲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絲毫沒有影響現實生活中這兩人之間的情誼。一個有胸襟的作家應允許別人“道短”,并對批評意見抱有熱情的態度和善意的理解。
現在的批評家實際上還是太講面子了,當然我也是喜歡聽好話的,比如有小說出來也希望你們講好話,但是我更希望聽見真話。以前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批評家和作家之間可以講一些很厲害的話,甚至批評起來都是“上綱上線”的,可是并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友誼。現在還沒有這樣的一個氣氛,也不怪我們的批評家,是社會氛圍引起的。有句笑話說,不做壞事的干部就是好干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說,現在不收紅包的批評家就是好批評家。
潘向黎:我倒是覺得上海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比上海的文學創作要領先一些的,為什么是這樣,有一次在王紀人老師那里聽到的一些話,可能可以作為答案。王老師說上海的作家比較遵守游戲規則,比較老實本分,不會異想天開,這大概也是上海這個城市和上海人本身的文化基因。對于作家們來說,不夠個性化是一種集體性的隱患,尤其對于真正出大作品來講肯定是有不利的影響。但是在批評界同樣的文化基因發作出來,卻可能帶來比較客觀、冷靜的效果,形成相對來講比較平和公正的氣質。
大家都說北京比上海熱鬧,但我覺得北京熱鬧里面也不都是好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批評界跟寫作界的關系就似乎過于親熱,太兄弟姐妹了,一個禮拜要一起吃好幾頓晚飯,比和家人一起吃的次數都多。確實是很熱鬧,很愉快,但對嚴肅獨立的批評卻不是很好。上海的氣氛則屬于淡淡的君子之交,是若有若無的情誼,但有時候適當的距離才能帶來清新的空氣。這一點上我覺得上海的批評界不必妄自菲薄。
趙麗宏:文學批評一直是上海的一個傳統,好的文學批評對作家的創作是一種引領。但純粹的文學批評現在越來越少,很多批評家轉向對文藝、社會現象甚至時尚話題的批評。除此之外,過去的批評家如程德培,為了寫幾千字的文章,要花很多心血,做大量的閱讀。但另外有一些“有水平”的批評家,不讀作品或者瀏覽一下就可以寫評論文章,這是不能寫出真實的文學批評的。當今的文學批評沒有權威性,上海需要純粹的文學批評家,捧殺或棒殺都不是真正負責任的批評。只有讀了作品,才有資格來說話。
趙長天:剛才趙麗宏說的程德培那樣的批評家確實是比較少,全國能夠超出他的批評家我想不出第二個。有的批評家,名頭大了,被到處請,全國到處飛來飛去,參加研討會拿報酬,還有多少時間能踏踏實實地讀作品?當然,他們拿高的報酬也是應該的,批評家現在報酬是不合理的,只有在北京基本能達到比較合理的一個狀態。批評家做的是看幾十萬字寫兩千字的事情,如果只按照普通千字百元的稿費收入,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