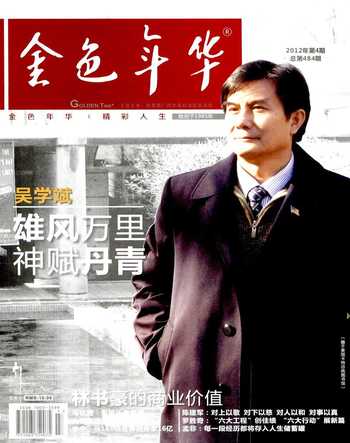潘石屹:我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吳虹飛
在中國,再沒有哪個地產(chǎn)商有比潘石屹更高的曝光率了。作為SOHO中國的聯(lián)席總裁,除了具有時代符號般效應(yīng)的SOHO現(xiàn)代城,在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出盡風(fēng)頭的“建筑師走廊”、在海南一度引發(fā)空前熱銷的“博鰲藍色海岸”別墅區(qū)、各種論壇、藝術(shù)展覽、模特大獎賽、時尚品牌發(fā)布會……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幾乎他的每一句發(fā)言,都會成為第二天網(wǎng)站上的文章標(biāo)題;幾乎每一個禮拜,潘石屹都會在《SOHO小報》上進行一次網(wǎng)上聊天,參加聊天的網(wǎng)友包括公司的員工、各個媒體的記者以及天南海北的擁躉們。
潘石屹確實是很謙和的,這一點并不是任何人上一期紳士訓(xùn)練班就能速成的。潘石屹氣質(zhì)中最難模仿之處就在于,他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名人,而且沒有架子。
1984年第一次坐電梯
去年,潘石屹被某周刊評為“飄一代”代言人。
而這一稱呼并沒有給他帶來太多感覺,思索了片刻,他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飄一代。”
SOHO中國的辦公室的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成片的高樓拔地而起,密布聯(lián)綿,見證著北京這座現(xiàn)代化都帝廉人的發(fā)展速度,而他正是這現(xiàn)代化場景的創(chuàng)造者之一。
接流行的說法,從祖輩開始,潘石屹的血液里便已經(jīng)流淌有“飄一代”的氣質(zhì)了。
根據(jù)潘石屹的敘述,潘爺爺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和村子里的親戚闖世界了,先在北京上了一個北洋政府的警官學(xué)校,之后受辛亥革命的影響,從天津坐船到廣州,成為黃埔軍校第五期的學(xué)員,結(jié)交過許多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回到村里。“不過爺爺在我出生前就過世了。”潘石屹想了一下,補充說,
“其實,關(guān)于他的好多故事也都是村里流傳下來的。”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位于甘肅與陜西的交界處,雖地處偏遠,卻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傳說中伏羲、女媧的故鄉(xiāng)、風(fēng)景秀美的“塞外江南”。
“小時候在地里干活,天晴的時候,能看清麥積山。”潘石屹對童年的印象還很清晰,“每家都收集字畫,窮得叮當(dāng)響的,也有古董、古畫。”
童年是潘石屹最樂意演繹的話題。最后,一個不怎么會講普通話、視吃飽飯為理想的窮小子形象恰如其分地出現(xiàn)在你面前。
“1984年是我第一次來北京,以前還從來沒有見過電梯,下了車進到北京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電梯。”潘石屹的敘事風(fēng)格很生動,對于細節(jié)的記憶也讓人欽佩。“那時北京站電梯只有上,沒有下,不像現(xiàn)在的電梯有上有下。我就從樓梯上走下來,再上去,走下來,再上去,連續(xù)坐了好多次。”
那時才是飄一代
1987年,在機關(guān)已經(jīng)呆得很安穩(wěn)的潘石屹,毅然辭職下海。
第一個落腳點是深圳。對于一個初次越過長江的北方人來說,氣候、飲食、語言、工作壓力,不適應(yīng)感來自方方面面,據(jù)潘石屹說,那是自己最不愉快的一段時間。
“剛下海時,幾乎所有人都勸我回頭,只有一個在伊拉克做過工程的朋友跟我說,計劃經(jīng)濟沒出息,你堅持往前走,哪怕要飯也不要往回走,他是唯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來到海南,經(jīng)人介紹認(rèn)識了海南省體改所負(fù)責(zé)人,加入其下屬機構(gòu)“農(nóng)高投”——海南農(nóng)業(yè)高科技聯(lián)合開發(fā)總公司,在那里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當(dāng)時的“農(nóng)高投”聚集了好幾位如今在北京商業(yè)圈叱咤風(fēng)云的人物,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陽光100集團董事長易小迪,還有在做風(fēng)險投資的王功權(quán)……
“馮侖以前是做體制研究的,喜愛社交,開始時主要務(wù)虛,他又是我們幾個人中年紀(jì)最大的,我們都聽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幾個月主要是王功權(quán)在做業(yè)務(wù),后來他在開會時極力推薦我,說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熱情,這種人不做業(yè)務(wù)做什么?”
王功權(quán)也許沒有想到,幾年后,潘石屹正是憑借具有“革命”、“前衛(wèi)”精神的SOHO現(xiàn)代城成為中國房地產(chǎn)界最有影響力的開發(fā)商。
或許時間沖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風(fēng)淡云輕。問他為何選擇去海南時,潘石屹輕松地笑了,回到開始時的話題,“那時候才是飄一代呢,當(dāng)時拿個身份證,錢也沒有,想走哪就走哪去。現(xiàn)在飄的話,不還有很多負(fù)擔(dān)嗎?”
與.com失之交臂
經(jīng)歷了海南的熱潮和“萬通”的風(fēng)云,如今,潘石屹還一如既往地“賣房子”,不過相比其他同行,又帶些“異類”的氣質(zhì)。
“在中國,我可能是最早接觸互聯(lián)網(wǎng)的。”
1993年,在美國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紹了當(dāng)時還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聯(lián)網(wǎng)雛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業(yè)感很好”,希望與他合作。朋友舉了半天的實例向潘石屹解釋投資機會,說“信息高速路”就好比機場高速路,
“網(wǎng)關(guān)”就好比收費站,可老潘怎么也聽不懂。沒轍,朋友后來找到了四通集團,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現(xiàn)在新浪網(wǎng)的前身。
“要是我當(dāng)時明白了,比新浪還早一年成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過,我也不后悔,我辦事的原則是我聽不明白的東西,就不能投。”
“賣房子”是潘石屹不離不棄的主業(yè),但除此之外,對其他一些領(lǐng)域他也興致盎然,比如現(xiàn)代藝術(shù)。
進入SOHO中國辦公室的一層,第一眼就看到空曠的展示廳里擺放著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經(jīng)在去年上海雙年展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內(nèi)冰冷冷的白色調(diào)的映襯下,迸發(fā)出撲面而來的視覺震撼力。
潘石屹指點,這些照片是剛剛運到的,而且“貴得不得了”,“費了好大的勁”。
潘石屹并不認(rèn)為自己是不務(wù)正業(y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在東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東方文化才有這樣的智慧,而且只有東方人才能體會這種智慧。”他說,“管理公司,攝影,寫文章,與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是相信命運的
實業(yè)做大了,通常就超脫起來,潘石屹也不例外。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現(xiàn)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現(xiàn)在)各種各樣的誘惑、信息非常的多。我相信一句話,空的大腦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腦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實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但一旦你空靈了,放開了,就是神在幫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這樣闡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他說,“做事情要舉重若輕,做大事情要像做小事情那樣才能做好。”
潘石屹的深入淺出與平和心態(tài)是讓人折服的,盡管事后會覺得有些遙遠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又總會彌補這些。
想從潘石屹的言談里捕捉往日驚濤駭浪的痕跡是困難的,對于一個喜歡老子的人,人生本應(yīng)是江上扁舟股的淡然與濕潤。從農(nóng)村窮小子到億萬富翁,當(dāng)所有的人沉醉于生動的小故事中時,他戛然而止,說出一句“我是相信命運的”。
就像小說中慣用的手法。“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注定要在這個時代發(fā)生,而命運剛巧選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