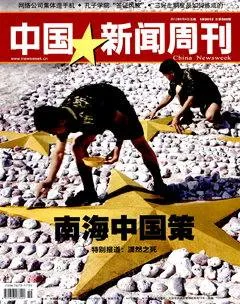三好生制度是如何煉成的


1953年,13歲的馬珮進(jìn)入女12中(即現(xiàn)在的北京166中學(xué)),成為一名初一學(xué)生。
父親馬敘倫工作忙,身體也不太好,馬珮跟他很少交流,也不會(huì)知道,這位曾任南京國(guó)民政府教育次長(zhǎng)的新中國(guó)第一任教育部長(zhǎng),所關(guān)注的一個(gè)問(wèn)題正在影響著中國(guó)的教育走向。
那是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學(xué)生學(xué)習(xí)負(fù)擔(dān)過(guò)重、營(yíng)養(yǎng)不夠、健康水準(zhǔn)有所下降的報(bào)告,擺在了馬敘倫案頭,深感憂(yōu)慮的他向毛澤東做了匯報(bào)。
學(xué)習(xí)負(fù)擔(dān)過(guò)重,從來(lái)不是困擾馬珮的問(wèn)題。她承認(rèn)自己當(dāng)年不是好學(xué)生,太淘氣,愛(ài)玩,功課只是過(guò)得去。她這一生中,從來(lái)與三好生等榮譽(yù)無(wú)緣。
對(duì)她的興趣志向,父親從不干涉,但父親對(duì)她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她至今記得,父親的《論詩(shī)九首》里有一句:“入耳不出則為奴。”“他原來(lái)針對(duì)書(shū)法寫(xiě)的,但我覺(jué)得這是他整體的思想。他就是這樣。我覺(jué)得人不能給你灌了什么想法就是什么,必須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馬珮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對(duì)馬敘倫的建議,毛澤東隨即指示:“健康第一。”他還提出,學(xué)習(xí)時(shí)間宜大減。不久,毛澤東再次致信馬敘倫,信中說(shuō),學(xué)生的健康問(wèn)題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學(xué)習(xí)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見(jiàn)中國(guó)新民主主義共青團(tuán)第二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主席團(tuán)成員時(shí),毛澤東做了講話:“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祝賀他們身體好;二,祝賀他們學(xué)習(xí)好;三,祝賀他們工作好。”他還說(shuō):“14歲到25歲的青年們,是長(zhǎng)身體的時(shí)期……就是要多玩一點(diǎn),要多娛樂(lè)一點(diǎn),要蹦蹦跳跳。”
由此,“三好”成為全國(guó)教育界的主旋律。
從三好指示到五四決定
毛澤東發(fā)出“三好”指示后,1953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局長(zhǎng)孫國(guó)隨即在全市的中學(xué)干部會(huì)上做了傳達(dá),要求各校積極貫徹。
時(shí)任北京市101中學(xué)教導(dǎo)主任的蕭沅出席了這次會(huì)議。在他的印象里,孫國(guó)很有口才,是那種“能逗得人哈哈大笑,還把領(lǐng)導(dǎo)的意圖貫徹了”的能干領(lǐng)導(dǎo)。
1980年代后擔(dān)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zhǎng)的楊玉民當(dāng)時(shí)是北京五中的數(shù)學(xué)教師,他也聽(tīng)過(guò)孫國(guó)的傳達(dá)。1953年十一期間,他參加在中央團(tuán)校禮堂召開(kāi)的青年教師培訓(xùn)會(huì),“政治上一把好手”的孫國(guó)在會(huì)上做了講話:“今天我們要響應(yīng)毛主席的號(hào)召,要教育學(xué)生做‘三好’,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我就向彭真同志匯報(bào)。”底下的三四百人熱烈鼓掌。
孫國(guó)講話之后,蕭沅隨即在101中學(xué)的校行政例會(huì)上做了傳達(dá),要求師生緊跟形勢(shì),抓緊落實(shí)。
“其實(shí)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包括了解放初期學(xué)蘇聯(lián)的那些內(nèi)容。”蕭沅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的提法是:共產(chǎn)主義教育是由智育、技術(shù)教育、德育、體育和美育五部分組成的。
北京101中學(xué)是中共創(chuàng)辦于革命老區(qū)并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xué)。當(dāng)時(shí)的101中學(xué)可謂高干子女云集,毛澤東、劉少奇等領(lǐng)導(dǎo)人的子侄都曾就讀于該校。
對(duì)101來(lái)說(shuō),貫徹三好,學(xué)習(xí)是第一位的,因?yàn)閷W(xué)生來(lái)自老區(qū),基礎(chǔ)較差。“真有因?yàn)閷W(xué)習(xí)過(guò)分勞累而得病的。”蕭沅說(shuō)。
但1953年的高考,北京還是失利了,78%的考生平均分?jǐn)?shù)不到60分,低于天津。北京市委第一書(shū)記彭真親自到學(xué)校調(diào)研,在座談會(huì)上尖銳指出,北京應(yīng)該是“首都”,而不是“尾都”,北京市中小學(xué)教育應(yīng)當(dāng)站在全國(guó)的前列。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過(guò)了《關(guān)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學(xué)教育質(zhì)量的決定》(即五四決定)。決定中提出:“貫徹全面發(fā)展的教育,使學(xué)生切實(shí)做到身體好、學(xué)習(xí)好、工作好。”7月,教育部向全國(guó)教育部門(mén)通報(bào)了《五四決定》,希望各地參照?qǐng)?zhí)行。8月,中共中央批轉(zhuǎn)了這一決定。
“五四決定是一把火,要貫徹決定、貫徹三好。”蕭沅說(shuō)。
“三好學(xué)生”出世
五四決定之后,一些學(xué)校率先開(kāi)始了三好學(xué)生的評(píng)選,有風(fēng)向標(biāo)作用的101中學(xué)自然走在了前面。
時(shí)任101中學(xué)語(yǔ)文教師、班主任并兼任校長(zhǎng)秘書(shū)的汪瑞華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101中學(xué)的三好評(píng)選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由班委會(huì)、團(tuán)支部和班主任一起提名,形成名單,報(bào)到學(xué)校審批,再綜合平衡。評(píng)出來(lái)的三好生以干部和黨團(tuán)員居多,會(huì)考慮學(xué)生的政治表現(xiàn)、集體榮譽(yù)感等,但不會(huì)看家庭背景。“葉劍英的兒子年紀(jì)很小,很聰明,很調(diào)皮,就沒(méi)有評(píng)上三好。”她說(shuō)。
據(jù)《中國(guó)新聞周刊》多方調(diào)查,1950年進(jìn)入101中學(xué)的劉天曉可能是新中國(guó)最早的三好學(xué)生之一。1953年5月,周恩來(lái)和鄧穎超視察101中學(xué),當(dāng)時(shí)就讀初三的劉天曉作為學(xué)生會(huì)副主席,參加了接待工作。
劉天曉對(duì)《中國(guó)新聞周刊》回憶,他是1954年(至遲1955年)被評(píng)上校三好生的。但因?yàn)樯眢w原因,劉曉天沒(méi)能接受面訪,詳細(xì)回憶評(píng)選過(guò)程。
1953年進(jìn)入101中學(xué)的王同庚也是50年代的三好生。
為了確切地回憶自己究竟是哪一年被評(píng)上三好的,王同庚特意找出了50多年前的成績(jī)冊(cè)。成績(jī)冊(cè)顯示,1954年,他獲得了“學(xué)習(xí)好、工作好”的評(píng)語(yǔ),但是沒(méi)有“身體好”這一條,顯然,不是三好學(xué)生。
之后,王同庚努力鍛煉身體,還參加了10公里馬拉松的長(zhǎng)跑,被評(píng)為“三級(jí)馬拉松運(yùn)動(dòng)員”,最終通過(guò)了“勞衛(wèi)制”評(píng)級(jí),于1956年,被評(píng)為了校三好生。
那一年,他獲得的操行評(píng)語(yǔ)是這樣寫(xiě)的:該生學(xué)習(xí)努力,作業(yè)認(rèn)真,注意實(shí)事,遵守課堂、睡覺(jué)、課外活動(dòng)、飯廳的紀(jì)律,積極鍛煉身體,參加建校勞動(dòng),積極工作,工作負(fù)責(zé),是團(tuán)支部委員,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影響全班,但還不夠。
1955 年2 月和5月,“身體好、功課好、品行好”正式進(jìn)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學(xué)生守則》和《中學(xué)生守則》第一條。評(píng)選“三好學(xué)生”的活動(dòng)逐漸在北京市屬重點(diǎn)中學(xué)中推開(kāi)。
楊玉民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1955年左右,他所在的北京五中開(kāi)始評(píng)選三好。他在班會(huì)上告訴學(xué)生:“一好不算好,得三好。”他原創(chuàng)的順口溜“德不好是殘品、智不好是次品、體不好是廢品”,逗得同學(xué)哈哈大笑。
根據(jù)北京市教育局的報(bào)告,1956年,北京的中學(xué)里已出現(xiàn)了300多個(gè)優(yōu)秀班集體和大批的三好學(xué)生。4月14日,北京市舉行了中等學(xué)校“三好”表彰大會(huì),全市共有1295名三好生受到表彰。
101中學(xué)檔案處的工作人員王冬向《中國(guó)新聞周刊》介紹,在初中階段連續(xù)3年被評(píng)為三好學(xué)生的,初中畢業(yè)時(shí)將獲得北京市頒發(fā)的銀質(zhì)優(yōu)良中學(xué)生獎(jiǎng)?wù)拢辉诟咧须A段連續(xù)3年被評(píng)為三好學(xué)生的,高中畢業(yè)時(shí)將獲得金質(zhì)優(yōu)良學(xué)生獎(jiǎng)?wù)隆?/p>
高校:對(duì)“三好”的各自表述
貫徹三好的活動(dòng)也在高校中展開(kāi)。不過(guò),如何貫徹三好指示,成為高校各自解讀、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團(tuán)北京市委大學(xué)工作委員會(huì)1953年10月一份名為《人民大學(xué)、鐵道學(xué)院、航空學(xué)院在貫徹“三好”中存在的問(wèn)題》的工作總結(jié)顯示:
在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身體好”得到了普遍重視,每天參加文體活動(dòng)的人數(shù)增加了,社團(tuán)增多了。雖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強(qiáng)迫性”,點(diǎn)名、吹哨子甚至鎖門(mén),非把人趕到操場(chǎng)去。
學(xué)業(yè)繁重的航空學(xué)院則更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好”,這導(dǎo)致學(xué)生的“休息時(shí)間被擠掉了,參加課外活動(dòng)的機(jī)會(huì)被剝奪了,黨團(tuán)活動(dòng)也被擠得很少”。
在北京大學(xué),系與系之間存在不同的理解:生物系認(rèn)為,身體好放在前面,所以“身體第一”;化學(xué)系認(rèn)為,學(xué)生的任務(wù)是學(xué)習(xí),所以“學(xué)習(xí)第一”。
在這些高校中,清華大學(xué)爭(zhēng)三好的氛圍最濃厚的。校長(zhǎng)蔣南翔剛上任清華不久,就率領(lǐng)校黨委積極貫徹“三好”號(hào)召和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的教育方針,以培養(yǎng)紅色工程師為目標(biāo),抓大學(xué)學(xué)習(xí)方法,開(kāi)展全校勞衛(wèi)制鍛煉,舉辦各級(jí)運(yùn)動(dòng)會(huì)和各種文藝社團(tuán)活動(dòng)。
1953年9月,17歲的俞國(guó)寧來(lái)到清華報(bào)到,進(jìn)入動(dòng)力機(jī)械系燃?xì)廨啓C(jī)專(zhuān)業(yè) 58屆3班。一進(jìn)校園,她就感到了“爭(zhēng)先進(jìn)”“創(chuàng)三好”的熱烈氛圍。
清華園里,每天晚上剛響過(guò)下晚自習(xí)的鈴聲,人們總可以在一、二號(hào)樓之間欣賞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織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宿舍里傳出的各種軍樂(lè)號(hào)練習(xí)聲,而周末則是學(xué)生們最愉快的時(shí)刻。一到下午4點(diǎn)半,學(xué)校操場(chǎng)上的喇叭就響起來(lái)了,把大家都轟出去鍛煉。高年級(jí)同學(xué)每人穿一件紅領(lǐng)襯衫(紅領(lǐng)是自己到學(xué)校統(tǒng)一染的),列隊(duì)在操場(chǎng)上跑圈。
激動(dòng)不已的俞國(guó)寧很快便投身其中。她被選為班長(zhǎng),因?qū)W習(xí)成績(jī)優(yōu)秀獲得了獎(jiǎng)學(xué)金。她參加了學(xué)校中長(zhǎng)跑代表隊(duì),身體變健康了,體重由36公斤增加到46公斤。她還參加了合唱團(tuán)、戲劇社,后來(lái)又擔(dān)任了政治輔導(dǎo)員,組織全校學(xué)生的文娛活動(dòng)。“在清華學(xué)習(xí)的階段真是得到了全面的培養(yǎng)和鍛煉。”俞國(guó)寧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1954年3月,清華大學(xué)土木系出現(xiàn)了第一個(gè)“先進(jìn)集體”。1955年,評(píng)出了第一批三好學(xué)生。5月4日,清華大學(xué)三好生積極分子代表大會(huì)在校禮堂舉行,816位代表參加了大會(huì),俞國(guó)寧成為其中之一。
1956年4月,青年團(tuán)北京市委召開(kāi)北京市高等學(xué)校三好學(xué)生大會(huì)。會(huì)議通知明確規(guī)定,三好學(xué)生評(píng)選的標(biāo)準(zhǔn)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dòng)和社會(huì)工作”“學(xué)習(xí)成績(jī)優(yōu)秀”和“勞衛(wèi)制鍛煉成績(jī)優(yōu)秀”。通知還規(guī)定了評(píng)選程序:班級(jí)團(tuán)支書(shū)、班會(huì)聯(lián)合提名,經(jīng)系行政、團(tuán)總支審查同意后,再交由群眾醞釀?dòng)懻摚ㄗ⒁獍l(fā)揚(yáng)民主),最后由校評(píng)議委員會(huì)批準(zhǔn)。
最終,全市1500名三好學(xué)生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huì)。《中國(guó)新聞周刊》記者在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的名單里看到,俞國(guó)寧的名字排在清華大學(xué)動(dòng)力系的第一個(gè),是班級(jí)中唯一的與會(huì)代表。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guó)務(wù)會(huì)議上做了《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wèn)題》的講話,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yīng)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fā)展,成為有社會(huì)主義覺(jué)悟的有文化的勞動(dòng)者。”這一方針,被稱(chēng)為是“全面發(fā)展教育”的方針。由此,評(píng)選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這年夏天,王英民從101中學(xué)高中畢業(yè),遺憾的是,他從來(lái)沒(méi)有被評(píng)上三好生。他達(dá)到了工作好和身體好兩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但因有一兩門(mén)功課不是5分,還是沒(méi)能評(píng)上三好。“三好學(xué)生有機(jī)會(huì)成為校旗手,在凱旋曲中升旗,非常隆重。大家那時(shí)候都羨慕極了。他們是大家的一面旗幟。”王英民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王英民的同班同學(xué)、后來(lái)成為著名音樂(lè)家的施光南和成為畫(huà)家的李問(wèn)漢,當(dāng)年也不是三好生。
“施光南當(dāng)時(shí)就是一心搞創(chuàng)作。比如和你一起走的時(shí)候,摟著你走著走著,手指頭就彈起鋼琴來(lái)了。”施光南還在課桌下畫(huà)上鍵盤(pán),老師講課,他在底下彈琴,對(duì)于提問(wèn),一臉茫然。“當(dāng)時(shí)大家都覺(jué)得他是不對(duì)的,對(duì)他有意見(jiàn),所以他當(dāng)時(shí)入團(tuán)比較晚。”
李問(wèn)漢曾是王英民的同桌,1955年入中央美院附中就讀,1958年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深造。“其實(shí)我當(dāng)時(shí)畫(huà)畫(huà)和他不相上下。他現(xiàn)在是畫(huà)家,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覺(jué)得不一定非得門(mén)門(mén)突出。人的精力有限。我們是太求全面發(fā)展了,我就上當(dāng)了。”王英民半開(kāi)玩笑地說(shuō)。他中學(xué)畢業(yè)之后,留在101任教,之后進(jìn)入中國(guó)旅游學(xué)院,從事外事工作。
1957年以后,受形勢(shì)影響,貫徹“三好”的工作開(kāi)始遭遇困境。
“一開(kāi)始對(duì)‘三好’是絕對(duì)服從的,并不感覺(jué)它有什么問(wèn)題。后來(lái)學(xué)來(lái)學(xué)去,提了一條,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曾任101中學(xué)教導(dǎo)主任的蕭沅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1958年9月,國(guó)務(wù)院發(fā)出《關(guān)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教育必須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服務(wù),教育必須同生產(chǎn)勞動(dòng)相結(jié)合”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針。蕭沅介紹,之前號(hào)召同學(xué)從事勞動(dòng),是貫徹三好號(hào)召,后來(lái)組織學(xué)生勞動(dòng),變成了安排學(xué)生的手段。這其中的變化,跟大的形勢(shì)有關(guān)。“這么多學(xué)生畢業(yè),怎么安排工作?這個(gè)問(wèn)題越來(lái)越突出,后來(lái)就安排學(xué)生到農(nóng)村的廣闊天地去。”
1959年之后,國(guó)家進(jìn)入困難時(shí)期。“老百姓開(kāi)始餓肚子了,還評(píng)什么三好啊?”蕭沅說(shuō)。
文化大革命開(kāi)始后,“三好生”成為“白專(zhuān)生”的代名詞,三好學(xué)生的評(píng)選也被廢止。在文革結(jié)束后的撥亂反正中,才重新恢復(fù)。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團(tuán)中央聯(lián)合發(fā)出通知,公布《關(guān)于在中學(xué)生中評(píng)選三好學(xué)生的試行辦法》。至此,評(píng)選三好成為遍及全國(guó)各地的活動(dòng),并且開(kāi)始與升學(xué)掛鉤。
進(jìn)入2000年之后,中國(guó)教育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顧明遠(yuǎn)等學(xué)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學(xué)生評(píng)選,上海、武漢、貴陽(yáng)等多地已相繼改革三好生評(píng)選制度,或代之以“優(yōu)秀隊(duì)員”“優(yōu)秀團(tuán)員”稱(chēng)號(hào),或與升學(xué)時(shí)的政策性加分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