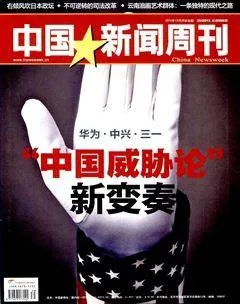不平等條約的由來
處在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時(shí)期,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xiàn)和失誤,其實(shí)都是那個(gè)大變動(dòng)時(shí)代的一筆精神財(cái)富,值得珍視與寶貴,不必總是以后見之明去指責(zé)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
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的起點(diǎn)無疑是《南京條約》。這個(gè)條約規(guī)定五口通商,擴(kuò)大開放,盡管這些規(guī)定對(duì)中國來說是被迫是無奈,但五口通商,擴(kuò)大開放,對(duì)中國來說不是壞事。
然而,中國沒有善待五口通商帶來的發(fā)展機(jī)遇,沒有下工夫引導(dǎo)中國利用這個(gè)機(jī)會(huì)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將農(nóng)業(yè)文明轉(zhuǎn)軌到工業(yè)文明;也沒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機(jī)會(huì)去耐心引導(dǎo)消費(fèi),培育市場,培育中國人新的消費(fèi)習(xí)慣和消費(fèi)理念。中國在經(jīng)歷了鴉片戰(zhàn)爭短暫痛苦后,很快回到享受農(nóng)業(yè)文明好處的狀態(tài)。
或許是因?yàn)橹袊鐣?huì)的惰性,或許是因?yàn)榻y(tǒng)治者無知、自私,中國沒有從五口通商走上世界,反而以擴(kuò)大通商引誘國人抱怨西洋人。以為五口通商是對(duì)中國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傷害。至于在五口居住、營業(yè)的外國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權(quán)更是對(duì)中國的不尊重。
根據(jù)《江寧條約》《虎門條約》,所謂“治外法權(quán)”,就是在五口或中國內(nèi)地,外國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國法律進(jìn)行約束和制裁,而是交給英國法庭,運(yùn)用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個(gè)規(guī)定后來被中國人和中國歷史教科書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嚴(yán)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司法主權(quán)的喪失。
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中國,中國人雖然見過不少外國人了,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遠(yuǎn)鄉(xiāng)村,外國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見,西洋人與中國人也并不總是處在沖突狀態(tài)。但是,怎樣管理這些在中國的西洋人,中國政府似乎并沒有想好,他們不是愿意讓渡自己的司法權(quán),而是不知道怎樣運(yùn)用這項(xiàng)權(quán)利。他們能想到的簡單辦法就是古代中國的“以夷制夷”,讓洋人自己管理自己,總比讓中國人去管理更省心。這既是后來外國租界、租借地或外國人集中居住區(qū)的起源,也是“治外法權(quán)”的落實(shí)。中國人不愿直接管理外國人,愿意誰的孩子誰抱走,自我管理,大家都相安無事。
至于那個(gè)一直被后世中國人視為不平等的“協(xié)議關(guān)稅”。其實(shí)與“治外法權(quán)”同等性質(zhì),同一個(gè)原因。都是因?yàn)橐⌒模跃椭鲃?dòng)放棄了這些權(quán)利。
參與《江寧條約》《虎門條約》談判的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并非等閑之輩,他們不僅有著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jīng)歷,而且深知中國體制之弊與體制之優(yōu)。他們還深知鴉片戰(zhàn)爭之前廣東地方政府與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發(fā)這場戰(zhàn)爭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因而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gè)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他們真誠希望英國人同意用一個(gè)具有包干性質(zhì)的固定稅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強(qiáng)勢(shì)官員的胡作非為。他們想到了協(xié)議關(guān)稅,因?yàn)檫@種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種貨物應(yīng)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無誤地寫在條約里,中外雙方因此減少了沖突和爭執(zhí),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論怎樣強(qiáng)勢(shì),也沒有辦法額外加稅。這既是一個(gè)關(guān)稅包干、財(cái)政包干的笨辦法,但在這些制度設(shè)計(jì)者看來,一舉數(shù)得,清廷的財(cái)政收入不會(huì)因此減少,新稅則的“值百抽五”在事實(shí)上比先前的稅率略有提高。又因?yàn)橛辛诉@個(gè)數(shù)額、比例的制度約束,地方政府、強(qiáng)勢(shì)官員無計(jì)可施,不能稅上加稅。
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屈辱或吃虧,但在當(dāng)年,不論談判者,還是朝廷,都認(rèn)為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他們不愿徹底打開國門介入全球經(jīng)濟(jì)一體化,但他們也不愿意英國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shí)占盡便宜。當(dāng)然,從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和國際貿(mào)易理論,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績是虛假的,是不足信的,犧牲了國家主權(quán),貽害不少。他們爭來了不當(dāng)爭、不必爭的東西,恰恰又放棄、犧牲了不應(yīng)該放棄的權(quán)利和利益。只是歷史主義地看待1840年代中國外交,那時(shí)的中國畢竟剛剛開始被動(dòng)地與近代國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敗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其經(jīng)驗(yàn)、智慧、眼光,當(dāng)然沒有辦法與一個(gè)成熟的國家去比較,甚至沒有辦法與幾十年后的中國相比。直至1882年,當(dāng)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進(jìn)行修好通商條約談判時(shí),方才有機(jī)會(huì)仔細(xì)檢討40年前“協(xié)議關(guān)稅”“治外法權(quán)”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外交事務(wù)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勸說朝鮮在與美國談判通商條約時(shí),既不能像朝日《江華條約》那樣不定稅則,喪失利益,且為各國所竊笑,也不能像《南京條約》那樣固定稅則,一勞永逸,而是談出一個(gè)公平章程,約定大致原則,浮動(dòng)稅率,定期修約。這就是關(guān)稅自主原則。如此簡單的一段話,中國人用了近半個(gè)世紀(jì)方才明白,我們有什么理由去指責(zé)伊里布等人失誤或不察。
處在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時(shí)期,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xiàn)和失誤,其實(shí)都是那個(gè)大變動(dòng)時(shí)代的一筆精神財(cái)富,值得珍視與寶貴,不必總是以后見之明去指責(zé)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地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話,那是因?yàn)闀r(shí)代,因?yàn)闊o知。因?yàn)橹袊菚r(shí)還沒有現(xiàn)代意識(shí),遠(yuǎn)遠(yuǎn)不是一個(gè)現(xiàn)代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