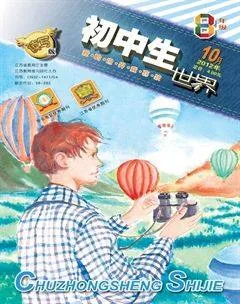如果我一直很乖
侯文詠,臺灣大學醫學博士,曾為麻醉科主治醫師。侯文詠曾有4年時間承擔一項為晚期癌癥患者進行“疼痛控制”的工作。4年中,侯文詠送走了500位病人。這段經歷讓他開始懷疑曾經篤信的價值觀,認識到追求物質、追名逐利的生活,讓他與快樂漸行漸遠。想通了的侯文詠在36歲那年毅然辭去醫院的工作,開始了職業作家的生涯。代表作品有:《大醫院小醫師》《危險心靈》《白色巨塔》。
小時候上作文課時,老師要我們讀故事寫心得。故事的內容是抗日戰爭期間,女童軍送國旗給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守軍。照說,這個關于榮譽、愛國、奮不顧身的故事,心得一點也不難寫。不過那時我故意唱反調,寫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詳細的文字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意是:
(一)如果不能打勝仗,送國旗也沒用;如果能打勝仗,國旗過幾天再掛也沒關系。
(二)如果打敗仗還掛國旗,老百姓會誤以為打了勝仗,錯過了逃亡的黃金時機。
(三)國土失掉了,還可以收復,但女童軍命沒了,就無可挽回了,因此還是命比較重要……
我還寫了不少理由,總之,結論就是大唱反調。可以想象,在那個國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師約談了。
老師問我:“老師平時對你好不好?”
我說:“好。”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聽老師的話,別人怎么寫,你就怎么寫。”老師停了一下,又說:“大家會怎么寫,你知道吧?”
我點點頭。
“你相信老師,這是為你好。你聽話,以后才有前途。”
“噢。”
我相信了老師,從此我的文章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種是公開的、“聽話”的文章,像是作文課的作文、比賽的作文、考試的作文、貼在墻報上的作文。另一種是偷偷摸摸的、“不聽話”的文章,像是傳小紙條的文章、寫情書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了我長大之后,我母親還很喜歡數落我小時候多么頑皮、多么不乖的事跡。當然,四行倉庫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對我來說,那些其實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話,或者誠實地說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當時我一點也沒想過,那就是所謂的“不乖”。
依照那樣的定義,我這一輩子其實還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時沒有郵資,偷爸爸的郵票;像是為了讓稿子內容更精彩,編出許多學校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像是,為了看電影,偷偷翻墻爬進電影院,被老板拎著耳朵拉出來……
或者,像是在實驗室做研究時,明明大家都覺得異想天開、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試;或明明大家覺得是沒有機會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辭去了醫師的工作,成為一個專職作家,成為一個編劇、廣播主持人、電視連續劇制作人……
回想起來,是這些“不乖”“不聽話”的作為或決定,一點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決定性的部分。
有時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時候放棄了“不聽話”的文章,只寫“聽話”的文章;或者因為沒有零用錢買郵票,因此放棄投稿;或者……少了這些“不乖”,我的人生會變成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師講的一樣,所有要我乖的人幾乎都是很善意地為我好。我也相信,聽話的人的確會有前途。那時候我并不明白,不聽話的人,長大一樣會有前途的——差別只是,聽話的有聽話的前途,不聽話的有不聽話的前途。
回想起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讓那個年輕、不乖又有點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知道:
別擔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繼續努力,用力讓自己長大成心中想望的樣子,一切都會很好的。
(選自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一書,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