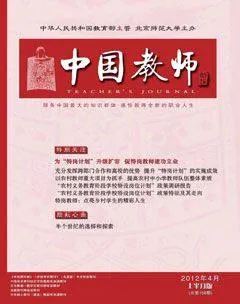在“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中促進幼兒教育實踐者的專業發展

“假設教師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不會對教與學產生多大影響,那么教師在教學中通常是政策的傳達者而不是參與者、行動者……”[1]這一假設意味著教育實踐者只需履行固化的教學程序,其工作并無專業性可言,其專業發展也便無從談起。因此,教學在多大程度上或能否成為一門專業,其首要標準就是要有完善的專業知識體系作為教育實踐者從業的依據,從這個意義上,教育實踐者的專業發展就是不斷組織與完善專業知識體系的過程。那么如何提升教育實踐者的專業知識水平?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與石景山區幼兒園通過建立“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對解決這一問題進行了探索。本文從“北京—深圳兩地園長工作坊”(北京—深圳兩地幼兒園園長工作坊”是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石景山區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實施活動之一。工作坊由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北京市石景山區教育委員會與深圳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幼教管理中心聯合舉辦)活動切入,以幼兒園園長為分析對象,從知識視角解釋了伙伴合作機制促進教育實踐者專業化發展的基本路徑,即從知識內涵上,重新定位幼兒園實踐性知識的價值;從知識學習上,為幼兒教育實踐者提供情境性、主體性和平等性的建構主義學習模式。
一、重新定位幼兒園的實踐性知識
以往的高校—幼兒園合作項目幾乎都要面對“優勢知識”的矛盾——高校生產的正式的、基于學術基礎的知識要優于蘊涵于園本文化和日常教學實踐中的幼兒園知識,[2]在合作中,高校專家往往把握著合作過程、事務決策等方面的絕對話語權,幼兒教育實踐者要么過度依賴學者力量,要么應付了事,致使合作表面化,兩類知識的不平等違背了伙伴之間平等共商、合作共建的本質,最后往往導致合作關系的破產。本研究建立的伙伴關系充分肯定了兩種機構的知識,尤其是幼兒園園長、一線教師在日常實踐中形成的專業知識得到了認可并被整合到項目中。
1.以園長主題報告為載體總結提煉幼兒園實踐性知識
活動開始前,專家組要求園長們通過PPT、圖片、音像等資源呈現幼兒園的發展歷程,目的是促使園長總結提煉幼兒園的實踐性知識,幫助園長重新審視自身的經驗與不足。園長們準備的主題報告涉及園本課程開發、教師專業引領、園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實踐經驗,例如,在“課程與教師”專題中,深圳范園長從課程目標、內容、組織以及評價等方面詳細介紹了幼兒園園本課程“慧智童心——多元智能做中學”;深圳何園長講述了幼兒園教師經歷四大階段“艱辛中帶著喜悅”的專業成長之路;北京左園長闡釋了為教師提供有效引領和支持,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種種創新;北京徐園長則報告了自己如何根植于教育實踐,推動園本研究的進行。這些主題報告是園長們實踐智慧的集中體現,工作坊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高校專家不僅設計了工作坊的實施框架,還與園長們一起準備了專題報告,實現了實踐性知識和學術性知識的共享。
2.在一日活動中體現幼兒園實踐性知識的主體價值
在工作坊一日活動中,幼兒園園長的知識主體地位十分凸顯。園長的12場主題報告貫穿始終,他們分別闡述了園本課程開發、教師隊伍建設等問題。在深圳五所參觀園現場觀摩中,園長自帶相機記錄印象深刻的教育片段;在“北京園長的眼睛”環節,園長選擇某些照片解釋其背后的教育價值;在頭腦風暴式的集體研討中,園長們對同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與思考。盡管來自地域不同、關注問題層面不同、解決問題方法不同,但園長的實踐智慧在工作坊中得到了交流與碰撞、融合與提升。例如,在“園長領導力”專題中,深圳一位園長分享了她對教師和課程關系的感悟,即“支持教師,成為課程敏感的發現者和積極的參與者;激發教師,成為課程的研發者和實踐者;成就教師,成為課程發展的推動者和傳播者……”另一位園長說:“我看到了一個孩子自己在墻上涂涂畫畫(可擦掉重畫)的時候,內心很感動,它既體現了幼兒園對空間的利用,又體現了環保教育、綠色教育;不僅可以節約紙張,而且尊重了孩子的天性……”與此同時,工作坊也充分利用專家資源發揮學術性知識的引領作用,例如,在“課程與教師”討論后,北師大霍力巖教授指出,優質的課程與教師是幼兒園教育改革的關鍵著力點,是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根本保障;在“園長社會責任”討論中,馮曉霞教授解讀了園長領導力的輻射路徑,即園長不但要領導幼兒園的教育改進,也應該關照整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專家知識的傳遞不同于脫離情境的學術報告、講座,而是在幼兒園現場討論后直接進行點評,更能夠促進園長結合實際從學理層面思考幼兒園改進、教師發展等問題。
3.以園長反思報告為工具提升幼兒園實踐性知識
活動結束后,北師大專家為園長們提供了后續任務——書寫個人反思報告,目的在于讓園長梳理在活動中產生的直覺與感悟,將其轉化為個人的教育智慧和切實的幼兒園改進行動。例如,北京某園長通過對兩地幼兒園的差異比較,引發了這樣的思考:“適合孩子的教育,需要構建什么樣的園本課程?適合孩子的教育,需要怎樣成就教師的專業發展?適合孩子的教育,我們如何提高自身的領導力?有了思考,便有方向;有了問題,便有了動力。深圳一行,引領我在‘辦有文化、有品質的幼教’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建立更為完善的科學實踐行動……”對于每位園長的反思報告,專家又會給予提煉提升和資源支持,如專家會將某些園長的反思報告進行修改并以論文形式發表。
總之,“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重新定位和解釋了幼兒園實踐性知識的獨特力量,“通過在現實的學校和班級情境中的持續對話,幼兒園實踐者的聲音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權威,并經常對大學教授們所代表的更為正式的知識基礎形成挑戰”,[3]這從根本上打破了以往合作雙方的地位差異,使兩種知識的作用都能得到發揮。
二、支持幼兒教育實踐者的知識建構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是把外部知識直接輸入到大腦的過程,而是主體以已有的經驗為基礎,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于人際間的協作而進行的意義建構過程。為此,“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主張為幼兒教育實踐者提供情境性的學習環境、主體性的學習方式以及平等協商的學習氛圍,從而有效支持實踐者的知識建構過程。據此我們建立了“知識建構模型”(如下圖),并在工作坊中進行了應用。
1.情境性的學習環境調動園長的已有知識經驗
建構主義指出,已有的知識經驗是一切建構學習的基礎,新的知識經驗需要從已有經驗中生長出來。園長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實踐性知識,這類知識就應成為新知識的生長點,為此工作坊安排在幼兒園現場進行,通過真實的教育情境迅速激活園長們的已有經驗,從而幫助園長順利同化或順應新知識和新觀念。例如,通過參觀園所環境、觀摩教學活動,引導園長們思考“我們看到了什么?我們看到的與原有的做法有何不同?”這種活生生的教育現實能夠快速啟動園長的原有經驗,引發對教育現象的思考。在“北京園長的眼睛”環節中,園長們通過照片聚焦于某些教育片段來描述與澄清焦點問題,學習某項關鍵的知識。另一方面,在“活生生的”教育現象面前,專家理論能夠很快得到教育實踐的反哺,園長更有可能對理論知識產生共鳴。
2.主體性的學習方式幫助園長成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是知識的單向傳遞,而是學習者自主建構知識的過程。為此工作坊的每一活動避免了專家講座、報告等學習方式,主張園長在參與活動與討論中、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學習新知識、新經驗。例如,在“觀察與描述”環節,園長們自己用觀察、實物收集、作品分析等方法感知與理解幼兒園教育現象,專家是園長們的支持者;在“分享與鑒賞”環節,雙方園長通過個人報告互相鑒賞,彼此之間進行知識的討論與創生,專家是園長的欣賞者;在“變革與行動”環節,通過園長、專家一起對某一問題進行頭腦風暴式研討,促使園長互相激勵變革并形成對實際行動的思考,專家是園長的合作者。在工作坊一日活動中,園長們始終是學習的主體,她們不是在被動地吸收信息,而是主動地完成新知識的意義建構,高校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為教師“自學”提供支持、引導與合作。
3.平等的學習氛圍促進園長專業知識的改善
知識的學習更容易在平等對話的過程中發生,在我們的設計中,高校專家與園長們是學習伙伴,她們在平等協作的氛圍中分享與學習專業知識。例如,在“分享與鑒賞”環節,專家與園長們的報告共同面對大家的質疑與欣賞、批判與吸收;在“融合與升華”環節,專家的點評能夠從實際出發,引導兩地園長從具體的教育現象走向對普遍性問題的規律性、對地域性問題的多元化認識,專家代表的學術知識與園長代表的實踐智慧達成了融合與升華。在平等關系中,專家代表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優勢知識”,園長們的實踐性知識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達,這種平等性更有助于園長與專家在課程與教師發展、園長領導力等重要問題上深層互動,從而促進園長們專業知識、專業實踐的改善與提升。
三、結論
時至今日,“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已經持續了一年多,這一機制一方面通過平等定位幼兒園實踐知識與學術性知識,將幼兒教育實踐者的專業地位加以認可,這使得實踐者與專家很自然地拉近了距離,其零散的實踐經驗更容易在專家引領下轉化成系統的理性認知;另一方面,通過建構主義學習模式有效支持實踐者將原有經驗合法化并完成對新知識的建構,從而促使實踐者不斷完善知識結構,提升專業水平。從工作坊后續反饋來看,它對實踐者的專業發展有著顯著的推動作用。當然,幼兒教育實踐者的專業發展并非一蹴而就,這就要求這一合作機制具有較長時間的持續性,但伙伴合作機制涉及“更為多樣的關系模式、更為豐富的信息資源、看待問題的更多樣化的視角、整合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多樣化方式以及組織內部和組織機構之間更大自由的獲得……”[4]其結構的復雜性、實施的困難度以及面臨可能障礙的多重性是不言而喻的,為此,全面、深入地思考與研究“高校—幼兒園伙伴合作機制”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1][3]DarlingˉHammond,L.美國教師專業發展學校[M].王曉華等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
[2]Gilbert.J.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in the Discourse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1994,16(5).
[4]伍紅林.美國大學與中小學合作教育研究的歷史、問題、模式[J]. 比較教育研究,2008 (8).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前教育研究所)
(責任編輯:劉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