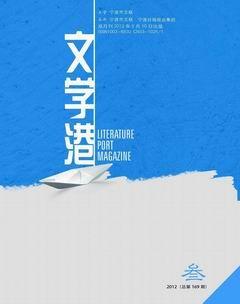實在的故事
鄭煬和
英國現代小說家伊舍伍德曾經說道:故事與故事不同,有好多極好的故事,只是故事而已,別無其它。你聽了以后會說:“真緊張,”“真可笑,”或者說:“我真沒想到是那樣的結尾。”你可以用自己的話給朋友重講一遍,也沒有什么兩樣,只要你記住所有重要情節,次序不弄亂。但是另外一種故事,你用自己的話永遠表達不盡。這種故事實際上是一個世界的有機部分,在那里,每個句子都有助于喚起人物的話音,勾勒出環境、背景的氣氛與感覺。這種故事大于生活,它是一個門徑,由此進入作者的世界。
我想,伊舍伍德所說的后一種故事其實就是優秀的小說。小說離不開故事,但小說不僅僅是編故事。看完楊卓婭的小說集《八重櫻》,我有點激動,這就是小說,這是個聰明而有趣的作者。作者的名字聞所未聞,于是輾轉得到了聯系電話,想進一步了解創作動機、構思過程等。電話那頭說馬上從象山過來,想當面談。原以為是位時髦、健談的女性,見面發現是位樸素、謙虛、不善言辭的同齡人,而且對自己的作品沒有多大的信心,非常誠懇地要我提出批評意見。我極力讓她相信,我沒有其他的專長,但鑒賞力還是有的,我認為好的作品肯定是好的。我指出小說集中《今晚沒有月光》一篇相對弱,而且我猜測她以前應該寫過詩。楊卓婭大笑起來,說我怎么像個算命先生,那篇確實是處女作,她以前確實寫過詩,但幾乎沒人知道。她反復說如果寫評論不要講好話,她會難為情的,多提意見,那樣她才會進步。她告訴我,她是想把自己認識的世界告訴大家才寫小說的,但如何得心應手地把自己的認知寫出來,還是個問題,還要不斷學習,她現在對自己的作品還是不滿意的。我想,寫評論不是評論者講作者的好話或者講壞話,其實是評論者以文本說話,來闡述作品是不是好的詩或小說,好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我告訴楊卓婭,我給她寫評還是有點私心的,我想以她的小說為解剖對象,來闡述什么是小說,好的小說好在什么地方。世界上的名作自然不少,但我想以這樣一個普通的作者的作品為對象,更有現實意義。
《八重櫻》收錄了6篇中篇小說,基本上都是寫小人物的生活和命運。也許是作者有過做醫生的經歷,她的小說要么主人公是醫生,要么小說的主線是人在身體出現危機時對人性的考驗。與書名同名的小說《八重櫻》講了拒拿醫藥回扣的正直醫生姜怡青面對醫藥代表的強烈進攻和同事們的冷嘲熱諷及丈夫在購房款上的步步緊逼時的無奈和無助。在全社會都在追逐物質的時候,甚至以房子的大小、存款的多少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時候,以救人扶傷為天職的醫生這個特殊的職業群該如何選擇?拿高價回扣,會損害病人很多是并不富裕的病人的利益和健康;不拿回扣,成為異類,同時忍受清貧。選擇前者,是社會道德底線的不斷下滑;選擇后者,不僅得忍受孤獨,同時還有親人的不理解。作者把浮躁的社會用姜怡青這個兒科醫生的遭遇和矛盾來反映,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是的,生活自身雖然并不直接“講”故事,但的確在提供著各種能被小說家用來創造成為“故事”的素材。回扣蔚然成風,醫患矛盾早不成新聞,社會道德底線不斷探底,作者成功地把看來雜亂繁復的生活素材提煉為具有意義和清晰的邏輯結構,這時她就獲得了故事。換言之,現實生活中只有各種“事件”而沒有“故事”,“故事”是由作者在生活素材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以“事件”為零件,包含有一個相對完整的邏輯結構并且因此而擁有對生活的某種發現的話語現象。《八重櫻》這個中篇反映的現象非常普遍,無所不在的腐敗侵蝕著這個社會的肌體,但當作者以不動聲色的筆調把它從一個基層醫生的心靈掙扎中寫出來,還是不由得讓人震撼。當守衛良知變得如此之艱難時,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在很多地方出問題了?作為個人,我們該怎么辦?作者沒有提供答案,其實她也沒法提供答案,作者在小說中放棄傳統的道德判斷和說教,把主人公的困惑交給了讀者。這也就是那些優秀故事的魅力的奧秘所在:它是對生活的一種本體化表現,生活是多維度多向性的,因而凡是能夠提供這種展現的故事,它對人生經驗的啟發和提示也相應地具有一種無窮感。因為它并不是對某種固定的、抽象意義的形象圖解。讀者其實也更喜歡這種“生活化”的小說。海明威在讀了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后談了一番體會:“一切好書在這一點上都是共同的:它們比實際可能發生的生活更加真實,在你讀完后,你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覺得書中的一切都是你親身經歷的事,從此以后,這一切——好事和壞事,狂喜、悔恨與憂傷,人物和地點以及天氣情況——都屬于你了。”《八重櫻》便是這種既“高于生活”,是對生活的一種審美概括,又具有高度的“生活化”,使人產生一種“這便是現實”的錯覺的作品。讀者有可能是從事各種行業的,但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姜怡青的痛、無奈和掙扎。
所以,寫出一個優秀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求作者不僅需要有對生活深入的體驗,而且還要求作者有深厚的藝術修養,能夠體會出事件的各種意味。
楊卓婭的小說都是用極普通的手法寫極普通的事,既不靠趣味性來征服讀者,也不以風味感來使我們流連忘返,而是以對生活意義的獨特發現讓我們咀嚼再三。讀著這些小說,雖然沒有那種特別有趣的細節和新鮮的風俗人情,而只是一些凡人瑣事,但透過敘事主體那流暢平靜的語調,有一種東西扣動著我們的心弦,這就是一種意味。這種意味來自作者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提煉,使我們掩卷之后忍不住要反復回味,去重溫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人生的辛酸。
意味是區分作品夠不夠優秀的衡量標準之一。因為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的好奇心的深層結構,正是一種反思癖。對人來說,了解世界的現象的目的是從規律上認識它的本質。所以,“反思癖與好奇心和游戲欲一樣,不僅是一種人的需求,而且是真正意義上屬于人的需求”,這種需求的存在決定了對意義的把握雖然不見得輕松,但對人而言未必完全是一種苦事,尤其當這種把握被置入一種形象體系,以一種情感體驗的方式來進行時。因為通過對意義的提取,人得以在觀念上表現對世界的俯視,對具體存在時空限制作出超越和對自身命運作出某種掌握。所有這些,充分體現了“人”這種生命現象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無疑是人類引以自豪的一個理由,因而能在這種把握實現之時,帶給主體以極大的快感和欣慰。所以“藝術對真理并不是漠不關心的,它實質上是對于真理的追求”。藝術作品中的真理性作為“意義”的一種晶化形式,是為了滿足讀者對小說的審美反思的需要,這種需要構成了小說的意味,擔當起對人生之謎和存在價值作出自己的解答這一責任。以意義為內核的“意味”是小說審美品格的一種基本構成,它根植于審美接受主體對自身命運的關注。
因而“意味”作為小說中藝術思想的一種反映,它的價值也不在于深度而在于新鮮,因為這是小說家自己以其全部的主觀性對生活的獨特發現。小說家以他們的這種發現贏得我們的尊敬和喜愛,小說的意味在這種敬愛和愛意之中繁衍滋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家就像哥倫布,所寫的每一作品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遠航。因為只有這種東西才能帶給我們一種發現的快感,意味便是這種快感在我們的藝術直覺中閃現的一個精靈。
楊卓婭的小說《黑眼睛》同樣寫的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的命運,這樣的人、這樣的命運在農村真的太普遍了,以致我們常常熟視無睹。但在看了楊卓婭的小說后,我忽然發現:生存,這個不起眼的詞,讓多少人的人性為此扭曲,讓多少親情變得一文不值。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像小說中的“姨媽”也會覺得半同情半厭惡,小氣、封建、認命、愚昧,從不會去想她們為什么會這樣,只會覺得她們就是這樣的。但楊卓婭讓我們看到了生存這只老虎如何在吞噬人性的光亮。龍應臺說:“文學,使你‘看見。”她又說:“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種吧!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憫。這是三個不同層次。”楊卓婭還夠不上偉大,但她確實在發現并讓讀者“看見”。她摒棄了女作家往往自戀的毛病,這一步已讓她脫離了壞作家的行列,因為愚昧往往因無知無趣自戀所導致。她冷靜、包容地寫下她所熟知的人物,同時寫出了她對這世界的思考,意味也由此而生成。
成功的人物塑造與成功的故事編造同在。因為故事不是別的,它就是人物的各種行動的組合。在這里,“行動不僅形成事件,而且也塑造了參與事件的人物”,所以,寫好故事也就成了創造出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的先決條件。事實證明,一個小說家只有在占有了許多很好的細節的同時,還能恰到好處地安排好情節,他才能夠真正寫好一個故事。概括地來看,如果說作家寫好一個細節的關鍵在于充分地體現出生活味,那么創作出一個出色的情節的關鍵則在于掌握住偶然性的分寸。偶然意味著各種巧合,沒有這種現象,作品會缺少一種獨特的吸引力,但巧合的事件太多,就顯得假。在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小說中,事情必須看上去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性既來自于細節方面的生活化,同樣也來自情節方面的現實感。
還是以《黑眼睛》為例,“姨娘”在丈夫溺水去世后查出患了糖尿病,因缺乏醫學知識,更主要是經濟困難,“姨娘”沒有積極治療,結果加重了,非打胰島素不可了,但她還是不肯,因為“我”給她算了一筆賬,光是藥水費、針筒、藥棉什么的加起來,每月費用就要三百以上,但不打,并發癥一個個會拖出來。姨媽聽后,說,三百元啊!“她把‘三字咬得特別狠特別有力,好像手里揮著一把鐵錘,每說一次都向她自己重重地砸一下”。“她很有把握地對我說:‘小嫣,不打胰島素,姨娘照樣把病情控制住!”“我們都沉默,包括我的表哥表姐表妹們,集體沉默。表面上,他們是生氣的,是堅決反對的,拼了命也要說服姨娘吃藥打針的。但話說回來,假如真說服了又怎樣?糖尿病是終身性疾病,注射胰島素會使人產生依賴性,一旦用上,沒到最后一刻,就是想停也停不下來。我姨娘是個農村老太太,一沒積蓄,二沒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什么的,這日積月累的,醫藥費誰出?大家心知肚明。從表面看,表哥表姐們都義正詞嚴,他們斥責姨娘不聽醫囑,不認真治病,其實又何嘗不是暗暗慶幸有這塊面紗遮自己的臉呢?”當“姨娘”因并發癥眼睛看不見再來就醫時,醫生告訴她,如再不采取措施,兩只眼睛恐怕就要徹底廢掉。“姨娘徹底灰了,癱坐在門診椅子上,好長時間都沒有聲音。許久,才回過神,乞求似的問我:‘小嫣,姨娘的眼睛還有的治嗎?”聽說可以激光治療,“姨娘抱著最后的一絲希望說:‘有多貴?琢磨著得好幾千吧?老專家詫異地笑了。‘幾千?他說,‘兩只眼睛幾個療程下來,起碼要幾萬。至此,姨娘的表情迅速平靜下來,就像吹過湖面的風,倏忽消失無蹤。她扯扯我的衣角起了身,客氣地對老專家說:‘醫生,這事我得跟孩子們合計合計,妥當了再找您幫忙。我順手操起診桌上的處方,那是老專家替我們寫的省激光中心的聯系電話、地址及交通路線。姨娘一把搶在手里,急急地把我往外扯,邊扯邊低聲道:‘呆大囡,沒聽見嗎?幾萬元,吃人呢,傻子才上那個當!”“我掰開她的胳膊,生氣地說:‘姨娘,你又固執了。這次不由你,激光非做不可!姨娘說:‘呆大囡啊,姨娘就是賣了也不值那個錢!老骨頭一把,扔都扔了,還激啥光啊。我說:‘這事我跟表姐表哥他們說,你辛辛苦苦養大他們,現在是報恩的時候了。我來打電話。”“姨娘把我的手攥住了,緊緊地。她用那失去光亮的眼睛牢牢地‘盯住我,異常堅決地說:‘小嫣,算姨娘求你一回,這事還是讓姨娘自己定吧。就算決心去做,也得回趟家,大家坐下來商量商量嘛。”大女兒一聽說此事,“刷地瞪起一雙大眼,斥責姨娘說:‘說什么呢,背時!不醫,不醫行嗎?你可是有兒有女響當當的,你不醫,人家還當是我們不給醫呢。她轉過臉,對大表哥說:‘哥,你給說說。娘這眼睛,醫還是不醫?照我說,別說咱們現在還有幾塊錢,就是沒錢,砸鍋賣鐵也得醫。不醫,我們幾兄妹在村里丟不起那個臉。今天當大哥的面,我的態度就一個字,醫!她說得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余地。……但大女兒走的時候說:“娘,就這么定了吧。我是沒空了,還得麻煩小嫣帶你去看病。你放心,你有兩個兒子呢,兒子挑大頭,女兒拔拔腳,幾萬元還愁拿不出?”“我注意到,表姐這么一說,大表哥的臉登時灰了。”最后,在一次意外的糾紛中,姨娘“突然沖上去抓住那人的手,用力向自己的眼睛戳去。霎時,兩只眼睛山崩似的淚如泉涌,淚,夾著鮮紅的血;血,染紅汪汪的淚,沿著蒼老而麻木的臉頰迅速墜落。”“我”去醫院看姨娘,姨娘“一字一頓地說:‘姨娘聽你,從今天起好好醫眼睛。”
整篇小說讀來非常真實,就如讀者親身經歷。王蒙曾說:“小說之吸引人,首先在于它的真實。其次(或者不是其次而是同時),也因為它是虛構的。如果真實到你一推開窗子就能看到一模一樣的圖景的程度,那么我們只需要推開窗子就可以看到小說了,何必還購買小說來讀呢?如果虛假到令人搖頭,又令人作嘔的程度,又怎能被一篇小說感動呢?”可見,小說中真實與虛構的關系是一種張力現象,真實不是如實紀錄,虛構也不是胡編,好的小說是虛構到真實。因為生活并不是講故事,生活是混亂的、易變的、任意的,它遺留下成千上萬的解不開的頭緒,參差不齊。作者從生活中抽出一個故事,只有通過嚴格的、細致的選擇。這需要虛構。所以,虛構其實意味著一種理性因素的滲透,其結果是某種秩序感的形式和確立,表現在具體作品中便是所謂藝術結構和形式的誕生。
而作者實現這一平衡的一個具體手段和方法,則是對小說文本結構的不同處理。即以精心設計的故事來安排小說的深層結構,使各部分之間處于相互依存的關系。但是小說的表層結構,即我們實際讀到的可見形式,卻是松散的。換言之,表層結構服從于無序性,深層結構體現出有序化,以此來達到作品真實和虛構的統一。《黑眼睛》中,從表面看來,大姨媽是矛盾的,既想把眼睛看好,又不想拖累兒女,對自己的病,大姨媽一會兒是豁達的,一會兒又有本能的害怕;兒女也是矛盾的,都希望留住自己的臉面但又不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作為姐妹的“我娘”也是矛盾的,既留存了一份手足之情,但那是在惠而不費的情況下。而“我”對他們的選擇是困惑的,無法做出評判,似乎誰的選擇都有理由,都可諒解,但事情一直在朝壞的方向發展。所有的這些無序性其實都服從了小說的深層結構——人的生存之困惑。好的小說都需要這兩種結構形成的張力。
至此,我們可以說,小說是一個有意味的、大于生活的故事。自然,要達到這個目標,作者的語言也非常重要。我一直認為,詩、小說和散文中前兩者對語言的要求是很高的,某種程度上說,是需要天賦的。我之所以斷定楊卓婭寫過詩,是因為她的語言是創造的,而不是轉述的,這對小說來說很重要,它們常常可以超越具體的描述,以一種張力場的方式存在,使得“你用自己的話永遠表達不盡。”“在那里,每個句子都有助于喚起人物的話音,勾勒出環境、背景的氣氛與感覺。”簡單舉個例子,《八重櫻》中,姜怡青去開會,“會場氣氛馬上活躍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空氣中嗡嗡嗡的,撞來撞去的都是人聲”,這不僅寫出了大家的浮躁,而且也刻畫出姜怡青內心的煩躁。
小說還有很多要素,譬如節奏、趣味等等,但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故事講得實在。有一篇名為《編故事也要實在》的小文章給我較多啟發,內容大致如此:
銷售葡萄酒的商人與葡萄酒品鑒家在交談。
商人:“外國紅酒為什么那么貴?用的不也是那種葡萄嗎?”
品鑒家:“一瓶3000元的酒味道值1000,故事值2000;一瓶10萬元的酒,味道值1萬,故事值9萬。”
商人:“這樣啊?那我也好好編故事就是了。”
品鑒家:“你編的故事,有整有零,值32塊5毛4。人家的故事有兩個特點:1.有基本的事實依據;2.故事的整理和傳播,更多地遵循文化價值而不是商業價值。為了銷售而現編的故事,是賣不出價錢的。”
我想,寫小說編的故事也是一樣,用的都是新華字典里的字,但寫得好的作者有自己對這世界的理解,故事的整理,更多地遵循美學規律,審美法則。楊卓婭的小說就是這樣實在的故事。■
責編 曉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