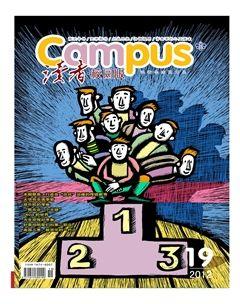輕功
成超

1994年,我上小學四年級,我哥上初一。那時候,我倆攢錢匯款買了一本武功秘籍,準確地說,是一本輕功秘籍。書的封面上畫著個和尚,他半蹲在一個大水缸的邊緣,好像是剛從地上飛上去的。我說:“這大缸太牢固了,司馬光絕對砸不爛。”我哥說:“咱們開始練習吧。”
照著書中的要求,我們購買了兩套綁在小腿上的沙包。我和哥哥開始每天綁著沙包上學,于是上學的腳步變得極其沉重。我練習很用心,出家門和快到學校大門的時候,都是跑步?jīng)_刺。那時我家在四樓,我們開始在上樓梯時采用雙腳跳躍式,從一開始的一次跳兩級臺階,慢慢變成跳三級,有時候想挑戰(zhàn)一下跳四級,但我怕變成“四級殘廢”,基本上都選擇放棄。
那是一個晴朗的周末,我和哥哥站在乒乓球桌旁,將小腿上的沙包卸下。我們毅然決定“起飛”一次—原地雙腳起跳,征服乒乓球桌。
哥哥先在原地垂直起跳,然后“噌”的一下就跳上了球桌。哥哥居高臨下,說:“弟弟,你上來,就像我這樣。”我一邊原地起跳,一邊想了想我的同桌晶晶姑娘,可能要永別了,課桌上的“三八線”可以抹去了。我雙腿一用力,腳尖一彈,眼睛一黑,小腿脛骨直接撞上球桌邊緣,跪倒在桌上。哥哥趕緊給我查看傷勢,說:“破了點皮,沒事。”我說:“哥,你輕功好,以后我們打壞人時你攻上,我攻下。”
現(xiàn)在想來,當時的我們其實已經(jīng)進入了飛檐走壁的最初級階段,看到墻我們都會利用速度在墻上留下一串弧形腳印。嘴里哼哼哈哈,似乎在唱Rap。
在一次體育課上,體育老師做了一次百米跑測試,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跑過來與我惺惺相惜,他說:“差點就被你追到,不然我的輕功就白練了。”放學后,他拉著我到了一個角落,從書包里抽出了他的輕功秘籍。“啊!大缸!”我喊道。
我急匆匆趕回家,向哥哥匯報情況。哥哥默而不語,閉著眼躺在床上,沒脫鞋。錄音機里正放著一首男女對唱的歌,男人的聲音比較柔。后來,我才知道他叫張信哲,而那首歌叫《有一點動心》。接下來的日子,哥哥常常那樣躺著聽歌。對此,我有點耿耿于懷,開始懷念起與哥哥一起練習輕功的日子,開始痛恨那些綿軟無力、不知所云的情歌。
那仍然是一個晴朗的周末,我再一次站在乒乓球桌旁,一只鳥站在電線上看著我。
當我站在乒乓球桌上時,耳垂下有風刮過,一種站在世界肩膀上的感覺頓時占領了我的整顆心臟。我迫不及待地沖回家,哥哥仍躺在床上聽歌。我說:“哥,我成功了!”哥哥輕聲說:“弟弟,你過來,躺在這里。”我走過去,躺下,十指交叉放在肚臍上,眼睛剛閉上,音樂就流淌進我的河灣。那些歌詞、那些旋律讓我有點措手不及,聽到副歌部分時,晶晶姑娘的樣子竟然在我腦海中成為一幅純美的簡筆素描。
我跳了起來,拿起沙包奪門而出,在院子里跑出一身汗。
時光毫不猶豫自顧自地埋頭前行,整個初中階段,由于我的輕功基礎,只要是用腿的體育項目,我都表現(xiàn)不錯,聽過終點線旁女生的尖叫,吃過三級跳時揚起的沙子,擋過對方前鋒的重炮轟門。到了高中,練習輕功的時間越來越少,隨著學習任務日益加重,我深刻感受到:輕功能讓我步履輕盈、健步如飛,但無法讓我的學習突飛猛進,為了學習,我甚至要把自己的青春暫時活埋。
工作后應酬很多,今年有一天,我們公司請某局領導吃飯。這位領導很有個性,一坐下來就叫服務員把酒全撤了,他說他不喝酒這個習慣惹毛了很多領導。他笑著說他從小就喜歡運動,小時候還練過輕功。我第一個大笑起來,他也大笑起來。我明顯地看見,他眼里泛著一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