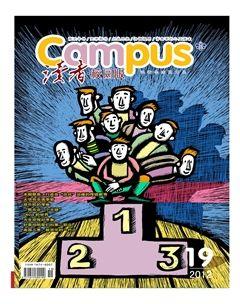夏日的蟬
王祥夫

我一直以為,如果聽不到蟬叫,整個夏天就算是白過了。
在夏天,起碼有兩種鳴蟲是越熱越能叫:一種是俗名“叫哥哥”的蟈蟈,另一種就是蟬。蟬是集體大合唱,一旦唱起來就不停不歇,而蟈蟈卻是叫叫停停,就會感覺它像是懂得休養生息。蟬的叫聲里像是有金屬的味道,只要你閉上眼睛仔細聽,就會感覺像是有千百只手在那里抖動碎鐵片。如果和蟬相比,蟈蟈的叫聲就“渾”了許多,若說“渾厚”倒又不對了,只是一個字—“渾”。一過立秋,蟈蟈的叫聲就變了,不再興致勃勃,而是有些疲憊,像是累了,再接下來,節令一入“白露”,如它還活著,叫聲就更加不堪,“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有氣而無力。各種蟈蟈中,我比較喜歡綠蟈蟈,好看,迎著太陽,幾乎是半透明的。鐵蟈蟈的顏色差一些,但叫聲卻頗高昂,像是京劇中的銅錘花臉,它若開唱,哪怕是一大片的蟬鳴也蓋它不住。我家在冬日曾蓄養過兩只蟈蟈,放在離暖氣近的地方,每每半夜就毫不客氣地叫起來。那天在院子里碰到住隔壁的鄰居,這位七老八十的鄰居問我:“你們家怎么半夜還在拉鋸?”我就忍不住笑了,那兩只蟈蟈同時叫起來,一來一去,在隔壁聽,可不像是木匠在拉鋸。
山西的北部蟬很少,山里的小綠蟬比大馬蜂大不了多少,叫聲尖厲而短暫,“吱”的一聲,已經不知到了哪里;又“吱”的一聲,也許是從別的地方又飛了過來。這種蟬只在山里有,城里就見不到。
古人對蟬是滿懷敬意的。古玩店里有賣玉蟬的,大一點的是含蟬,人死后把它含在嘴里,希望自己重生。小的玉蟬是佩蟬,作為一種裝飾,鄉下老頭的煙鍋子上有時候亦會出現一兩個,也許是鋤地得的,也許是家里傳下來的。蟬在中國,有幾分像屎殼郎在埃及,地位相當高。
中藥里有一味藥是“蟬蛻”,赭黃的,空空的那么一個殼兒,治什么病?不知道。得病而不吃中藥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有時候還是喜歡去中藥鋪看看,中藥的藥名挺好玩,有些像是人名:王不留行、劉寄奴。
河北一帶的兒童游戲粘知了:先找一根老長的樹杈子,然后再找蜘蛛網,把蜘蛛網一擰兩擰擰到樹杈子上—這也是個技術活,不能把蜘蛛網弄得一團糟—然后再循著蟬的叫聲去找,把樹杈子慢慢地伸過去,“吱”的一聲,那只蟬還沒等起飛就已迫降,早黏在蜘蛛網上了。這樣的蟬七個八個地給粘回去,八九不離十是被他們家的大人用油炸了下酒。
關于蟬的叫聲,古人曾以四字形容:“蟬鳴如雨。”閉上眼聽聽,還真像,而且是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