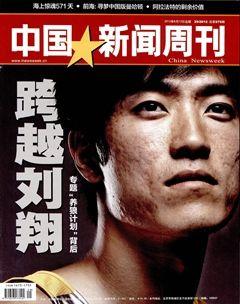前海:尋夢(mèng)中國(guó)版曼哈頓
閔杰
今年6月底獲批的深圳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或?qū)⒊蔀閲?guó)內(nèi)外夢(mèng)想家和投資者的又一塊熱土。在前海享有的22條優(yōu)惠政策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屬國(guó)內(nèi)首創(chuàng),比如在前海建設(shè)深港人才特區(qū)、金融業(yè)改革示范窗口、人民幣創(chuàng)新業(yè)務(wù)示范區(qū)等,深圳市也有意借此把前海打造成中國(guó)的曼哈頓。但是,前海在深港合作、人民幣國(guó)際化方面享有先行先試權(quán)力的同時(shí),同樣還面臨一定的風(fēng)險(xiǎn),從確立前海的管理體制到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都已涉入改革的深水區(qū),要求對(duì)相關(guān)體制進(jìn)行調(diào)整。
因此,目前在相關(guān)細(xì)則尚未出臺(tái)的情況下,前海能否給中國(guó)改革闖出一條新路,還有待時(shí)間的校驗(yàn)。
15平方公里的猜想
如何充分發(fā)揮香港在前海開放中的獨(dú)特作用?如何形成兩地產(chǎn)業(yè)互補(bǔ)、經(jīng)濟(jì)一體和社會(huì)共融的局面?這些問題,將始終伴隨前海的后十年,甚至更長(zhǎng)時(shí)間
2012年的仲夏末,中國(guó),深圳,前海,這片被認(rèn)為是中國(guó)未來曼哈頓的15平方公里的土地,眼下還是“一片荒蕪”。
由于填海造地的原因,80%的土地已經(jīng)完成軟基處理,正在等待緩慢的土地沉降。整個(gè)海岸看上去很空曠,只有一座橫跨前海灣的跨海大橋形影相對(duì)。大規(guī)模建設(shè)還未展開,在這里看不到任何施工圍欄、塔吊,也沒有工人,看上去有些荒涼。
以前,地處深圳南山半島西側(cè)的前海,是深圳珠江口東岸陸域的西部邊界,發(fā)電廠、污水處理廠身處其間,高壓線比比皆是,再往西便是大片的灘涂和無盡的海面。“領(lǐng)導(dǎo)找我談話的時(shí)候,我都不知道前海在哪,深圳也沒幾個(gè)人知道前海,”前海管理局局長(zhǎng)鄭宏杰對(duì)《中國(guó)新聞周刊》回憶起2010年初到前海時(shí)的情形。
6月27日,在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國(guó)務(wù)院正式批復(fù)了關(guān)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以下簡(jiǎn)稱前海)開發(fā)開放的有關(guān)政策,前海將擁有一個(gè)光明的未來:到2020年,這里的GDP產(chǎn)值將達(dá)到1500億元,換算下來,每平方公里的GDP產(chǎn)值將達(dá)100億元,是深圳的20多倍,比香港還多一半。
創(chuàng)造這些產(chǎn)值的,是來自前海先行先試政策所涵蓋的六大領(lǐng)域:金融、稅收、法律、人才、醫(yī)療及電信。國(guó)務(wù)院的一紙批文,在深圳這個(gè)特區(qū)中再造一個(gè)特區(qū),不僅讓前海成為目前內(nèi)地開放程度最高、創(chuàng)新空間最廣、優(yōu)惠幅度最大的區(qū)域之一,同時(shí)還擔(dān)當(dāng)了深圳香港兩座城市合作交流的試驗(yàn)田。
但是,如何充分發(fā)揮香港在前海開放中的獨(dú)特作用?如何形成兩地產(chǎn)業(yè)互補(bǔ)、經(jīng)濟(jì)一體和社會(huì)共融的局面?這些問題,將始終伴隨前海的后十年,甚至更長(zhǎng)時(shí)間。對(duì)于鄭宏杰來說,破解所有這些問題的辦法是——雙方最大的誠(chéng)意。“如果沒有誠(chéng)意,那就全是困難。有誠(chéng)意,就都不是困難,一定能找到共同點(diǎn)。”規(guī)劃出爐始末
在深圳的發(fā)展道路中,一直主打兩張牌,一個(gè)是改革開放,另一個(gè)是深港合作。
“最早的時(shí)候搞了一個(gè)‘深港創(chuàng)新圈,是政府提出來的,意在將深圳的科技產(chǎn)業(yè)和香港的大學(xué)研發(fā)能力進(jìn)行優(yōu)勢(shì)互補(bǔ)。”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常務(wù)副院長(zhǎng)郭萬達(dá)對(duì)《中國(guó)新聞周刊》說,當(dāng)時(shí)深圳市政府大力推動(dòng)這一構(gòu)想,但后來效果一般,主要是“圈的概念很虛,沒有明確的界限來劃分。”
后來進(jìn)入視野的是“一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區(qū)”,這是1997年深圳河治理中由于河道改造而形成的一塊土地,但此后一直處于荒置狀態(tài),還形成了土地所有權(quán)屬深圳、管理權(quán)歸香港的特殊產(chǎn)權(quán)狀態(tài)。“兩地一直在談規(guī)劃,談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但香港一直不積極,因?yàn)樗麄冇X得這塊地方生態(tài)和環(huán)境的價(jià)值更重要。”郭萬達(dá)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按照香港的規(guī)劃,要到2020年才會(huì)有實(shí)際的開發(fā),且多是以教育、科技為主。
由于“河套地區(qū)”開發(fā)需要漫長(zhǎng)等待,而且空間太小,而下一個(gè)浮出水面的正是前海。
郭萬達(dá)說,當(dāng)時(shí),前海主要有招商局所屬的一個(gè)約3平方公里的保稅物流園區(qū)和一些物流公司的倉(cāng)庫(kù),規(guī)劃師后來發(fā)現(xiàn),通過填海,在前海還可以發(fā)掘出約15平方公里的成片土地,引起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重視,“在上報(bào)給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后,他很重視,指示可以探索搞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示范區(qū)。”
“隨著深港合作的不斷深入,提升合作的層次、尋找實(shí)實(shí)在在的合作載體勢(shì)在必行。”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綜合處副處長(zhǎng)孫華明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在深港合作上大膽創(chuàng)新符合中央和省委對(duì)深圳的一貫要求。
2009年是前海規(guī)劃開始集中醞釀的一年。年初,國(guó)務(wù)院年初批準(zhǔn)《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要求加快規(guī)劃建設(shè)深圳前后海地區(qū)。5月,《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獲批,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jìn)前海地區(qū)的規(guī)劃建設(shè)和體制創(chuàng)新”。這一年,深圳市與香港特區(qū)政府進(jìn)行了溝通,兩地就前海合作達(dá)成了共識(shí)。
據(jù)資料顯示,時(shí)任香港特區(qū)政府政務(wù)司長(zhǎng)的唐英年認(rèn)為,在前海建立發(fā)展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示范區(qū)對(duì)香港是寶貴的契機(jī)。而時(shí)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現(xiàn)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huì)主任劉玉浦組織召開了多次會(huì)議,專題聽取前海地區(qū)規(guī)劃總體方案匯報(bào)。
對(duì)前海研究頗深的孫華明親歷了前海規(guī)劃出臺(tái)的過程,“這是一個(gè)很長(zhǎng)的過程,先后反復(fù)多次征求國(guó)家相關(guān)部委的意見,方案是集中各方智慧的結(jié)晶”。
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經(jīng)濟(jì)特區(qū)30歲生日當(dāng)天,作為一份“生日大禮”,國(guó)務(wù)院批復(fù)同意《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總體發(fā)展規(guī)劃》,明確把前海建設(shè)成為粵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創(chuàng)新合作示范區(qū),并明確前海的定位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區(qū)、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發(fā)展集聚區(qū)、香港與內(nèi)地緊密合作先導(dǎo)區(qū)、珠三角地區(qū)產(chǎn)業(yè)升級(jí)引領(lǐng)區(qū)。
“剛開始有很多大膽的設(shè)想,例如參照蘇州和新加坡工業(yè)園區(qū)的合作模式,由兩地政府間直接合作,或者干脆把土地交給香港來運(yùn)作,移植香港的一整套法律和經(jīng)濟(jì)制度。”郭萬達(dá)說,由于兩地在法制和體制上的明顯差異,這類大膽提議在早期就排除了。
孫華明研究認(rèn)為,除了背負(fù)深港合作的新命題,前海得以提上議事日程的另一個(gè)大背景是,國(guó)家當(dāng)時(shí)正在制定中的“十二五規(guī)劃”明確提出,要轉(zhuǎn)變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更明確地說,就是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前海可以在這方面先行先試。
隨著中國(guó)全方位對(duì)外開放格局的形成,深圳在全國(guó)整體發(fā)展格局中地位和優(yōu)勢(shì)已不如以前明顯,“特區(qū)不特”,與北上廣等中心城市的差距在逐漸拉大,并遭遇天津、蘇州、重慶等后發(fā)城市趕超的可能。對(duì)于香港而言,要保持國(guó)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新加坡、首爾等城市相比,在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等方面也存在“短板”。
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概念的出爐,無疑為深港兩地都注入了一劑“強(qiáng)心針”。深圳市市長(zhǎng)許勤曾概括道:“前海地區(qū)將成為一個(gè)‘雙跳板,深圳利用這個(gè)跳板,可以走向國(guó)際;香港利用這個(gè)跳板,可以走向內(nèi)地。”
“路線”選擇
對(duì)于前海來說,香港的制度借鑒價(jià)值無疑是巨大的。如何充分發(fā)揮香港在前海開發(fā)中的獨(dú)特作用,如何“學(xué)習(xí)香港”,成為前海開發(fā)中的核心命題之一。
被稱為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經(jīng)濟(jì)特區(qū)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條例》(簡(jiǎn)稱《前海條例》),也曾經(jīng)歷過一系列“香港風(fēng)波”。
2011年6月27日,《前海條例》獲深圳市人大常委會(huì)表決通過。這是涉及深港合作的第一部法規(guī)。
“深圳市人大、市委、政府都希望在前海的管理上,探索出一種新的模式來,一切依照法律辦事,法律先行。”全程參與了《前海條例》制定的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huì)副主任委員周榮生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在這種思路下,前海管理局根據(jù)《前海條例》而設(shè)定,成為中國(guó)大陸地區(qū)第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法定機(jī)構(gòu)。法定機(jī)構(gòu)在國(guó)外普遍存在,都是根據(jù)個(gè)別條例立法而成立并受有關(guān)機(jī)構(gòu)條例的監(jiān)管,在美國(guó),這種機(jī)構(gòu)被稱為“獨(dú)立機(jī)構(gòu)”,法國(guó)稱為“獨(dú)立行政機(jī)構(gòu)”,而在以效率著稱的新加坡和中國(guó)香港,則稱為法定機(jī)構(gòu)。
“這個(gè)機(jī)構(gòu)不是依據(jù)行政命令而產(chǎn)生的,它不是行政管理機(jī)構(gòu),但是又有行政管理職能,不是一個(gè)企業(yè),但又有企業(yè)的管理性質(zhì)。”周榮生說,前海管理局應(yīng)該是一個(gè)高效,同時(shí)充分吸收各方智慧的這樣一個(gè)機(jī)構(gòu),而傳統(tǒng)行政機(jī)關(guān)完全是行政化管理,不符合前海的定位和需求。
不過,在治理結(jié)構(gòu)方面,最初關(guān)于設(shè)立前海設(shè)立理事會(huì)的設(shè)想?yún)s并沒有實(shí)現(xiàn)。按照設(shè)想,理事會(huì)中香港理事不少于1/5,重大事項(xiàng)應(yīng)當(dāng)經(jīng)理事會(huì)全體成員過半數(shù)通過,特別重大的事項(xiàng),應(yīng)當(dāng)經(jīng)理事會(huì)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shù)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中帶有較為明顯的香港色彩。
“由于多種原因,目前沒有設(shè)立。在現(xiàn)有的部際聯(lián)席會(huì)議制度等的安排下,我們擔(dān)心,設(shè)立理事會(huì),會(huì)讓效率減慢,因此暫時(shí)沒必要設(shè)這么多機(jī)構(gòu)。”周榮生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
最終通過的《前海條例》中有20多處提到香港,明確提出堅(jiān)持與香港的緊密合作。但也有媒體指出,從初稿到最終的表決稿,《前海條例》逐漸淡化了香港的概念,條例中有關(guān)“香港”的內(nèi)容從三稿的27處減少為22處。
“從總體來說,認(rèn)為‘國(guó)際化色彩和‘港味變淡是外界的一種誤解。具體條文的調(diào)整在立法中是很難避免的,但跟香港的聯(lián)系和合作不會(huì)因此而減少。”周榮生回應(yīng)說,在現(xiàn)有的中國(guó)法律體系下,也不能為了改革的需要,把舊有的一切都“歸零”,然后另起爐灶,“以這種思路來考慮,會(huì)有一個(gè)嚴(yán)重問題,就算境外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進(jìn)來以后能否適用是一個(gè)未知數(shù),如果強(qiáng)行拿來,也許會(huì)面臨更大的風(fēng)險(xiǎn)。”
創(chuàng)新力考驗(yàn)
從國(guó)家總體戰(zhàn)略上看,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福建平潭已經(jīng)成為面向港澳臺(tái)的三個(gè)重要平臺(tái)。而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香港服務(wù)業(yè)需要加大經(jīng)營(yíng)半徑,需要內(nèi)地產(chǎn)業(yè)支撐。在鄭宏杰看來,這樣的戰(zhàn)略構(gòu)想正是前海的一個(gè)機(jī)遇。
從前海到深圳,再到廣東,一個(gè)宏偉設(shè)想是,在蛇口改革引領(lǐng)全國(guó)改革30年后,前海要引領(lǐng)今后30年的改革發(fā)展。改革和創(chuàng)新,依然是前海的關(guān)鍵詞。
而此次國(guó)務(wù)院批復(fù)的賦予前海的六大領(lǐng)域共22條優(yōu)惠政策中,也體現(xiàn)了這一思路。7月16日,深圳市政府在香港舉辦了前海深港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合作區(qū)政策宣講暨招商推介會(huì),赴港的中國(guó)國(guó)家發(fā)改委地區(qū)司司長(zhǎng)范恒山在會(huì)上詳細(xì)解讀了前海政策。
范恒山指出,國(guó)家賦予前海的政策具有領(lǐng)先型、超前性,很多方面是國(guó)家第一次賦予一個(gè)地區(qū)。這包括,第一次明確將前海建設(shè)成為中國(guó)金融業(yè)對(duì)外開放試驗(yàn)示范窗口,第一次提出在前海構(gòu)建跨境人民幣業(yè)務(wù)創(chuàng)新試驗(yàn)區(qū),第一次允許取得中國(guó)注冊(cè)會(huì)計(jì)師資格的香港專業(yè)人士擔(dān)任內(nèi)地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合伙人,第一次強(qiáng)調(diào)支持前海建設(shè)深港人才特區(qū)等。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國(guó)家賦予前海的不僅僅是優(yōu)惠政策,更是在諸多領(lǐng)域的探索空間和試驗(yàn)權(quán)力。
“這一次推出的政策中,有19個(gè)支持,5個(gè)允許,5個(gè)探索,2個(gè)進(jìn)一步,在18個(gè)方面推出了創(chuàng)新提法或政策舉措。”前海管理局經(jīng)營(yíng)發(fā)展處處長(zhǎng)王錦俠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此次前海政策釋放出的一個(gè)明確信號(hào)是,前海要集中探索的方向就是突破傳統(tǒng)體制、機(jī)制性的障礙,“表現(xiàn)為三類,一類是需要放權(quán)的,一類是基于接軌國(guó)際的考慮,還有一類是充分發(fā)揮地方,包括政府、市場(chǎng)、社會(huì)自主探索積極性的。”
對(duì)于前海來說,構(gòu)建深港人才特區(qū)、建設(shè)金融業(yè)改革示范窗口、構(gòu)建人民幣創(chuàng)新業(yè)務(wù)示范區(qū)等都是大概念,其中的空間恰恰給了地方很大的探索自主權(quán),“這次的政策可以分為兩大塊,一大塊是有形的,還有一類是無形的,就是鼓勵(lì)前海發(fā)揮‘先行先試試驗(yàn)田的作用來自主探索。”王錦俠說。
另一個(gè)超常規(guī)的機(jī)制創(chuàng)新是前海的部際聯(lián)席會(huì)議制度。這是由國(guó)家發(fā)改委牽頭,24個(gè)部委與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qū)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共同參與的國(guó)家級(jí)政策扶持平臺(tái),“我們今年2月3日就22條政策召開了專門的協(xié)調(diào)會(huì),會(huì)后又專門把會(huì)議討論的內(nèi)容發(fā)給各部委征求意見。”
“在前海管理局自身運(yùn)作上,怎么把政府的傳統(tǒng)職能,和市場(chǎng)化的運(yùn)作、企業(yè)化的管理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我們將經(jīng)歷一個(gè)成型、成長(zhǎng)、成熟的過程。”王錦俠介紹,前海管理局將分三步走,目前初步構(gòu)建了一個(gè)行政管理體系、市場(chǎng)運(yùn)作體系、公共服務(wù)體系、決策咨詢體系,正在構(gòu)建人事薪酬體系、社會(huì)監(jiān)督體系,而社會(huì)管理體系是第三步考慮的事情,“在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將來前海的社會(huì)管理必然明顯不同于其他區(qū)域,可能會(huì)成為我國(guó)從相對(duì)封閉到有限開放、再到完全開放條件下,接軌國(guó)際的社會(huì)管理。前海在這方面也要探索經(jīng)驗(yàn),積累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的實(shí)施路徑。”
在王錦俠看來,國(guó)家在前海政策上制度創(chuàng)新的力度之大,創(chuàng)新之多,超乎了一個(gè)地方的常規(guī),“前海的探索承載的國(guó)家使命是多層次的,目前的前海政策還只是冰山一角,沒有完全揭開前海探索改革開放新路子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