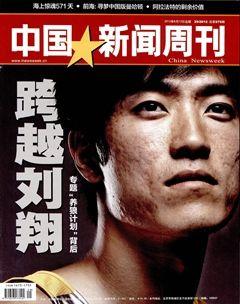保護(hù)老上海話(huà)的青年實(shí)驗(yàn)
劉炎迅
誰(shuí)對(duì)上海話(huà)的消沉最敏感?又是誰(shuí)站在新一輪保護(hù)和傳承上海話(huà)的第一線(xiàn)?一批年輕人在致力于重新發(fā)現(xiàn)和保護(hù)傳承上海話(huà)的過(guò)程中,有各自不同的主意,也獲得了各自不同的樂(lè)趣
颶、戉、罔、畀、黝……這些字,你能讀出來(lái)嗎?
它們并非“火星文”,而是正宗的漢字,來(lái)自上海大學(xué)中文教授錢(qián)乃榮很早就展開(kāi)一項(xiàng)研究,從古籍文獻(xiàn)里挖掘出它們來(lái),以便準(zhǔn)確無(wú)誤地表達(dá)上海話(huà)的發(fā)音。
正宗上海話(huà),在經(jīng)歷了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低沉后,最近兩年,又漸漸有恢復(fù)原來(lái)生氣的跡象。值得一提的是,掀起新一輪保護(hù)和傳承上海話(huà)的,大多是年輕人,有的還是外地人。他們?cè)诓粩喟l(fā)掘老上海話(huà)的過(guò)程中,也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樂(lè)趣。煙火味十足的上海《弄堂》
1979年出生的上海青年胡寶談,用一年時(shí)間,寫(xiě)了一本純上海話(huà)小說(shuō)《弄堂》。書(shū)一推出,立即引起上海學(xué)界熱議,評(píng)論人士甚至認(rèn)為,這是近幾十年真正的滬語(yǔ)文學(xué)的一個(gè)新起點(diǎn)。
胡寶談瘦瘦高高,戴著黑框眼鏡,留著稀疏的八字胡,看起來(lái)有些贏弱,談起上海話(huà),滔滔不絕。從商科畢業(yè)后,他做過(guò)很多工作,酒店餐飲,IT銷(xiāo)售,電視劇場(chǎng)記,偶然看到上海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錢(qián)乃榮研究上海話(huà)的文章,一下子就人迷了,于是萌發(fā)了用純上海話(huà)寫(xiě)一部小說(shuō)的念頭。
他開(kāi)始在生活中留意人們說(shuō)話(huà),馬路上、電車(chē)上、商店里、地鐵里的上海小囡講話(huà),很可怕,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普通話(huà),不但他們說(shuō)普通話(huà),連他們的父母,甚至六七十歲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這些老上海也在陪著他們說(shuō)“洋涇浜”普通話(huà)。
“有時(shí)候聽(tīng)見(jiàn)小囡一口流利上海話(huà),我馬上會(huì)高興起來(lái),口袋里拿出糖來(lái)請(qǐng)他們吃,有一次被一個(gè)家長(zhǎng)當(dāng)人販子一把揪住,差點(diǎn)打110。”
但一直沒(méi)敢下筆,他覺(jué)得很多上海話(huà)找不到準(zhǔn)確的漢字,直到他看到錢(qián)乃榮教授編寫(xiě)的《上海話(huà)大辭典》,那些“上海話(huà)正字”猶如天書(shū),但一下子打動(dòng)了他,“時(shí)機(jī)到了”。
他寫(xiě)的“弄堂”,活色生香,煙火十足。
1970年代“蛋票嘸沒(méi)了”(蛋票沒(méi)有了)、“畫(huà)圖調(diào)雞蛋”怎樣“贊”(好),老干部的太太為老公“解厭氣”而怎樣“拆神思”,外公是怎樣“做人家”又不是“做得膩心八臘”(惡心、小家子氣)的,生活趣味就是這樣娓娓道來(lái)。
年輕的上海人胡寶談扎進(jìn)故紙堆,像個(gè)考古的學(xué)究,他說(shuō),滬語(yǔ)語(yǔ)法上也有特色,保留不少古漢語(yǔ)句型,比如“你去什么地方”,滬語(yǔ)則是“儂啥地方去”;“看不起他”則成了“看伊勿起”;“快來(lái)了”則說(shuō)成“來(lái)快了”。
1990年代,港臺(tái)經(jīng)濟(jì)滲入大陸,粵語(yǔ)因此成為“時(shí)髦”,上海人也不例外,一度以學(xué)說(shuō)粵語(yǔ)為榮。最近幾年,以北京為背景和題材的電視劇越來(lái)越多,北京俚語(yǔ)也因此走紅。類(lèi)似“牛逼”“貓膩兒”等詞匯,迅速占領(lǐng)上海,而上海人一直說(shuō)的“搗糨糊”之類(lèi)的方言土語(yǔ),也逐漸被“不靠譜”等詞兒取代,說(shuō)多了,就成了一種心理潛意識(shí),張口就來(lái)。
胡寶談也難免有這樣的“潛意識(shí)”,他說(shuō):“開(kāi)頭我都寫(xiě)不標(biāo)準(zhǔn),甚至覺(jué)得寫(xiě)英文也比寫(xiě)滬語(yǔ)簡(jiǎn)單。有時(shí)候?qū)懸粋€(gè)字,我要反復(fù)查詞典,反復(fù)回憶小時(shí)候老人們是怎么說(shuō)的。”
胡寶談眼下的計(jì)劃是,寫(xiě)好一本《上海365夜》,專(zhuān)給小朋友看。
滬語(yǔ)保護(hù)潛流
7月28日晚,第六期滬語(yǔ)版《新聞坊》如期播出。楊曉明是上海電視臺(tái)新聞中心通聯(lián)部主任,也是《新聞坊》節(jié)目負(fù)責(zé)人。他坦言,這檔節(jié)目的想法很單純,“用上海話(huà)來(lái)說(shuō),更接地氣。”
但若放到二十年前,這樣節(jié)目恐怕會(huì)受到非議。
上海社科院前不久發(fā)布了《2012年上海市中小學(xué)生成長(zhǎng)情況最新調(diào)查報(bào)告》,其中提到方言問(wèn)題,主持這個(gè)調(diào)查的研究員周海旺接受《中國(guó)新聞周刊》采訪時(shí)說(shuō),人口變遷,對(duì)語(yǔ)言的影響很大,新中國(guó)成立后一直到80年代末,因?yàn)閼?hù)籍的嚴(yán)格管控,異地人口流動(dòng)很少,上海城市內(nèi)部的社會(huì)人群相對(duì)穩(wěn)定,語(yǔ)言也在那近30年里處于內(nèi)生穩(wěn)定狀態(tài)。90年代之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開(kāi)始實(shí)施,人口流動(dòng)加大,上海社會(huì)的語(yǔ)言開(kāi)始混雜融合。
普通話(huà)的推廣,一半是受到了建立統(tǒng)一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渴望的強(qiáng)烈推動(dòng),一半則是由于社會(huì)氛圍。很多外地人反映,在上海坐車(chē)買(mǎi)菜,聽(tīng)不懂上海話(huà),上海人也以此來(lái)區(qū)別是否為本地人,有時(shí)進(jìn)而會(huì)產(chǎn)生差別待遇。
這一度引起全國(guó)的關(guān)注,大家由此認(rèn)為上海人排外,不尊重外地人,并依賴(lài)語(yǔ)言來(lái)設(shè)置交流障礙。作為恢復(fù)和保護(hù)上海話(huà)的學(xué)者,上海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錢(qián)乃榮說(shuō),“這種現(xiàn)象不是上海話(huà)本身帶來(lái)的,而是使用上海話(huà)的人造成的,不能因?yàn)槭褂貌划?dāng)而使這個(gè)文化消失。”
錢(qián)乃榮回憶,當(dāng)年推廣普通話(huà)如火如荼,學(xué)校里甚至打出口號(hào):“進(jìn)了學(xué)校門(mén)兒,就到了北京城兒”,“上課講,下課也講,吃飯的時(shí)候、出去玩的時(shí)候,甚至在廁所里,都不許講上海話(huà),否則要扣品行分,孩子們彼此告密,向老師打小報(bào)告。”在錢(qián)乃榮看業(yè),那時(shí)很多口號(hào)標(biāo)語(yǔ),存在潛臺(tái)詞,比如:“說(shuō)普通話(huà),做文明人”“不說(shuō)臟話(huà),不說(shuō)方言,做文明的好孩子”等等。
社會(huì)上因此有了擔(dān)憂(yōu):“30年之后滬語(yǔ)會(huì)不會(huì)就此消失?”
上海滑稽劇團(tuán)對(duì)此感受最深。滑稽劇是一種以滬語(yǔ)為主要語(yǔ)言的劇種,但近二十年來(lái),要招到一口純正滬語(yǔ)的青年演員越來(lái)越難,幾百人里,往往只能挑出三四個(gè)。劇團(tuán)老演員徐維新回憶起80年代招收青年演員的情景,“只招20個(gè),報(bào)名3000多”。周立波就是那時(shí)進(jìn)入劇團(tuán)的。然而到1990年代,情景大為不同,計(jì)劃招收20個(gè),只有30人報(bào)名,最后勉強(qiáng)招了8人。
滬劇名角馬莉莉說(shuō):“如今上海滬劇專(zhuān)業(yè)團(tuán)體僅存3個(gè),編劇缺乏、演員流失,滬劇已大不景氣。從表面看,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沖擊的因素,但實(shí)質(zhì)是滬劇已缺失了它生存的土壤—一上海方言大大萎縮。”
事實(shí)上,保護(hù)上海話(huà)的潛流一直存在。
1990年代初,上海話(huà)電視連續(xù)劇《孽債》深受上海觀眾的歡迎,然而第二部滬語(yǔ)連續(xù)劇開(kāi)播之前被叫停,后來(lái)只播出了普通話(huà)配音版本。近幾年,滬語(yǔ)電視劇又重新回歸,比如一部叫《老娘舅》的情景喜劇,劇名都很有“上海味兒”。
在滬語(yǔ)版《新聞坊》之前,上海電視臺(tái)還有一檔出名的滬語(yǔ)節(jié)目《阿富根談家常》,不過(guò)播出時(shí)間一再變動(dòng),甚至兩度停播。滬語(yǔ)版《新聞坊》算是第一個(gè)固定時(shí)間播出的新聞欄目。
與電視不同,電臺(tái)一直在低調(diào)嘗試用滬語(yǔ)播音,比如FM103.7頻道有一檔上海話(huà)節(jié)目《越聽(tīng)越歡喜》,主持人用上海話(huà)介紹音樂(lè),有些成為口耳相傳的段子,比如張信哲的《難以抗拒你容顏》,主持人就用上海話(huà)說(shuō)成《實(shí)在趟伐牢儂迭只面孔》,而楊坤的《我比從前更寂寞》則被轉(zhuǎn)為《我比老早更嘎厭棄》,頗有喜感。
“世界上最遙遠(yuǎn)的距離是兩個(gè)上海人在一起,卻說(shuō)普通話(huà)。”
胡寶談不是個(gè)案。越來(lái)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到保護(hù)和恢復(fù)上海活的行動(dòng)中來(lái)。
錢(qián)翔和陸韻過(guò)完這個(gè)暑假,就是上海大學(xué)大三的學(xué)生,在《新聞坊》滬語(yǔ)版播出的第三天,他們就打算“跟個(gè)風(fēng)”,于是開(kāi)通了一個(gè)微博,取名“上海話(huà)播報(bào)新聞”。他們的第一條微博是在7月3日這天發(fā)出的,寫(xiě)的是:“世界上最遙遠(yuǎn)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兩個(gè)上海人在一起,卻說(shuō)普通話(huà)。”
陸韻是地道的上海人,而錢(qián)翔故鄉(xiāng)在浙江,算是新上海人,他告訴《中國(guó)新聞周刊》,滬語(yǔ)能聽(tīng)懂,也能說(shuō)一些,不流利,會(huì)有磕碰,但這不影響他喜歡滬語(yǔ)。
他覺(jué)得,來(lái)到上海,如果聽(tīng)不到滬語(yǔ),就有點(diǎn)缺憾,方言是一個(gè)地方特色和文化最直接的體現(xiàn)。
比如,上海話(huà)里實(shí)際上融入了很多英語(yǔ)詞匯,這與上海最早開(kāi)埠有關(guān)。鮮有人知道,“大亨”這個(gè)詞最早是上海人造出來(lái)的上海話(huà)與英文的合體。上海學(xué)者程乃珊的解釋是,早先上海人不懂洋文,為方便記敘,就將百元大票與英文“hundred”合拼一起:“唷,一張‘大亨!”眾人熟知的上海話(huà)“癟三”,則是從英文“a bitter cents”演繹而來(lái),幾乎—個(gè)先令都沒(méi)有,夠窮了吧?
一開(kāi)始,他們的微博全部用諧音漢字來(lái)寫(xiě)新聞,但難度太大,看起來(lái)也很吃力,后來(lái)改成新聞主體部分用普通話(huà),然后加上一句上海話(huà)評(píng)論。到7月30日,他們已經(jīng)擁有近6萬(wàn)粉絲。
在這個(gè)暑假,上海對(duì)外貿(mào)易學(xué)院的大學(xué)生也行動(dòng)起來(lái),他們自己編寫(xiě)了《校園上海話(huà)》小冊(cè)子,打算在社區(qū)里教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們學(xué)習(xí)上海話(huà)。該校團(tuán)委書(shū)記唐旭生說(shuō),這是他們暑期社會(huì)實(shí)踐的120個(gè)項(xiàng)目之一,名叫“上海話(huà)公益行”。
該校商務(wù)信息學(xué)院的章鳳慈同學(xué)是此項(xiàng)活動(dòng)的牽頭人。這個(gè)上海90后,此前在新聞里看到很多關(guān)于“上海話(huà)危機(jī)”的專(zhuān)題節(jié)目,于是召集同學(xué)們四處走訪調(diào)查,最后形成了這本小冊(cè)子。不過(guò)在他們的父輩看來(lái),這些倡導(dǎo)上海話(huà)的90后們,說(shuō)得也有些“洋涇浜”,“但這沒(méi)關(guān)系,上海話(huà)本身就是流動(dòng)變化的,推廣它,也要接受它的這種變化,總比徹底喪失好。”
當(dāng)上海話(huà)成為生意
讓上海話(huà)成為生意,如何?
想出這個(gè)點(diǎn)子的羅春樂(lè)卻是個(gè)溫州人。最初,學(xué)說(shuō)上海話(huà)只是他做生意的一門(mén)工具,不得不說(shuō),但日久天長(zhǎng),他也品出了語(yǔ)言背后的味道,“上海話(huà)是那種罵人也不帶臟字兒的語(yǔ)言”。
去年,羅春樂(lè)投資興建了一個(gè)網(wǎng)站:“滬語(yǔ)網(wǎng)”,將他感興趣的有關(guān)上海話(huà)的一切,都放到網(wǎng)站上。他說(shuō),這是一門(mén)生意,也是一份興趣。
當(dāng)然,真正做起來(lái)才發(fā)現(xiàn),很難。
他帶著團(tuán)隊(duì)采訪了上海很多文化名人,表演藝人,做關(guān)于滬語(yǔ)方言的專(zhuān)題欄目,但點(diǎn)擊率一直不高。他曾經(jīng)與靜安區(qū)某社區(qū)合作,搞了一場(chǎng)滬語(yǔ)晚會(huì),忙前忙后花了不少錢(qián),也請(qǐng)來(lái)錢(qián)乃榮等滬語(yǔ)學(xué)者,到頭來(lái),上海主流媒體鮮有關(guān)注,晚會(huì)落得個(gè)“清湯寡水”的結(jié)局。
網(wǎng)站還受到一些外地人的攻擊。有人留言道:這是個(gè)歧視外地人的網(wǎng)站。
作為外地人的羅春樂(lè)能夠理解這種情緒,但他覺(jué)得,“這不正是滬語(yǔ)網(wǎng)需要努力之處嗎?”他也反感不分場(chǎng)合、不顧對(duì)方聽(tīng)懂與否堅(jiān)持說(shuō)上海話(huà)的人,但這與語(yǔ)言無(wú)關(guān),他將一些類(lèi)似的交際案例放在網(wǎng)站上,期望能幫助人們改變對(duì)上海話(huà)的偏見(jiàn)。
不過(guò)維持網(wǎng)站的開(kāi)銷(xiāo)太大,于是羅春樂(lè)想再做一個(gè)“上海之聲”的資訊服務(wù)類(lèi)網(wǎng)站,以養(yǎng)活滬語(yǔ)網(wǎng)。
王佳梁,這個(gè)1979年出生的上海人,則將眼光放在了滬語(yǔ)輸入法上。
接受《中國(guó)新聞周刊》采訪時(shí),王佳梁帶著商務(wù)總監(jiān)李海峰匆匆吃了一頓盒飯,就從公司趕到約定地點(diǎn)。這家名為“觸寶”的公司目前只有10多位員工,員工平均年齡僅有26歲。
2007年到現(xiàn)在,王佳梁和他的伙伴們研發(fā)的觸寶手機(jī)輸入法已橫跨多個(gè)智能手機(jī)平臺(tái),支持40多種語(yǔ)言,擁有500萬(wàn)次的網(wǎng)絡(luò)下載量。
公司員工以外地人為主,除了在家里,王佳梁平時(shí)說(shuō)上海話(huà)的機(jī)會(huì)并不多。這也是許多上海人的現(xiàn)狀。他由此認(rèn)為,讓更多新上海人愛(ài)上上海話(huà),才是保護(hù)上海話(huà)的核心之道,他認(rèn)為手機(jī)輸入法提供了一個(gè)可能性。
他努力想讓上海話(huà)在使用時(shí)變得有趣一點(diǎn),抓住青年人的心,于是在設(shè)計(jì)輸入法時(shí),做了翻譯功能,即便那些不會(huì)上海話(huà)的人,也可以打出上海話(huà):如果打拼音“出租車(chē)”,同時(shí)還會(huì)跳出“差頭”的選項(xiàng);打“傻瓜”,看到的結(jié)果還有“戇大”,“挺好玩的”。
搜集字庫(kù)對(duì)于他們是最難的。他們最初在網(wǎng)絡(luò)上搜集字庫(kù),后來(lái)找到了錢(qián)乃榮教授,于是打算使用錢(qián)乃榮編輯的《上海話(huà)大詞典》里的正字,不過(guò)這也依賴(lài)使用者對(duì)上海話(huà)正字的熟悉程度,“期望有一天滬語(yǔ)正字能像粵語(yǔ)正字一樣,成為眾人熟知的書(shū)寫(xiě)體系。”
但也有人說(shuō),上海話(huà)其實(shí)內(nèi)部也有很大的差異,市區(qū)和郊區(qū)的差異就很大,這個(gè)輸入法能否抹平其問(wèn)的差異呢?
王佳梁說(shuō),這些恰是方言的魅力所在,以后或許會(huì)開(kāi)發(fā)出升級(jí)版,將這些多樣性放進(jìn)去,一定能吸引更多人的喜愛(ài)。
“現(xiàn)代社會(huì)必定是一個(gè)多言多語(yǔ)的社會(huì)。”上海語(yǔ)言文字工作委員會(huì)辦公室的張日培說(shuō),關(guān)于方言的保護(hù),已引起多方關(guān)注,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huì)上,關(guān)于文化工作建設(shè)的決議里,第一次提到語(yǔ)言文字的問(wèn)題,其中說(shuō)道:“大力推廣和規(guī)范使用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同時(shí),也要“科學(xué)保護(hù)各民族語(yǔ)言文字,包括漢語(yǔ)”。張日培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而方言是漢語(yǔ)的重要構(gòu)成。”
上海語(yǔ)委正在根據(jù)國(guó)家語(yǔ)委建設(shè)國(guó)家語(yǔ)言資源有聲數(shù)據(jù)庫(kù)的要求,建設(shè)上海話(huà)有聲數(shù)據(jù)庫(kù)。“歸根到底,上海話(huà)和普通話(huà)是可以共存的,是在不同的交際層面發(fā)揮各自不同的功能的。”張日培說(shuō),“我們現(xiàn)在的口號(hào)是:推廣普通話(huà),傳承上海話(huà)。保護(hù)和傳承上海話(huà),說(shuō)到底是一種文化需求,既是上海市民的心理層面的需求,也是城市管理者塑造城市獨(dú)特文化品位的追求,因此要將著力點(diǎn)聚焦在文化領(lǐng)域,上海的文化界應(yīng)當(dāng)‘生產(chǎn)出更多更好,甚至在全國(guó)都能打得響的上海話(huà)文化產(chǎn)品,包括戲曲、曲藝、文學(xué)和流行歌曲,等等。這一點(diǎn),上海還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