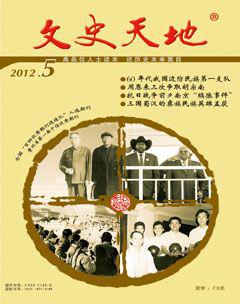鴉片戰爭中,英軍為何敗在舟山群島
校元明

英軍敗于疾病,固是清政府一大幸事,但也可見舟山生存環境之惡劣。
鴉片戰爭前夕,英軍的作戰方案是首先對珠江口實施封鎖,然后占領舟山群島并封鎖該島附近的長江入海口,最后到達天津白河口遞交英國政府的照會。可以說,占領舟山是英軍在鴉片戰爭中最為關鍵的一環。
1840年7月,英國侵略者近4000人仗著先進的槍炮,登上了舟山群島的定海一帶。然而,就在當年年底,他們卻不得不離開舟山群島,丟盔棄甲逃到香港。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舟山群島位于浙江省東北部,地處長江入海口南側,共有大小島嶼1300余處,其中最大的島嶼是舟山島(中國的第四大島,定海城位于該島的南端)。舟山不僅擁有富饒廣闊的江南腹地,而且是南北海運交通的要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經濟價值。
英國對舟山覬覦已久,早在17世紀末就有英國商船在該地活動。18世紀末馬戛爾尼來華時曾提出“將舟山的一個島嶼讓與英國”的請求,但沒有獲得乾隆帝的準許。鴉片戰爭前夕,為了建立一個侵華軍事基地,進而不斷地侵擾中國,英軍把占有舟山作為侵華的首要目標。
在英方看來,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并進占中國內地,必須建立一個穩固的軍事集結站和行動根據地,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在海軍部第二號機密文件中即明確指出:“舟山群島的中心位置在廣州與北京的中段,接近幾條通航的大河河口,從許多方面來看,能給遠征軍設立司令部提供一個合適的地點。”不僅如此,舟山優越的地理位置還可以為英國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并建立與日本的貿易聯系奠定基礎(因為中日貿易的中心乍浦即靠近舟山群島)。
鴉片戰爭爆發后,英軍的進軍路線便是按照上述構想進行的。
1840年6月28日,除留下部分軍隊封鎖珠江口外,其余大部向舟山進發。7月5日下午2時,英軍向定海發起攻擊,于次日凌晨占領定海。英軍之所以選擇在6、7月份發動進攻,主要是考慮到夏季風(有利于艦隊北上)的影響。
讓侵略者沒有想到的是,一旦踏上舟山群島這塊土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告別人世,去“天堂”報到。這一情況一度讓英國政府感到驚恐。
許多年后,當我們檢索那段歷史,就會發現,當侵略者踏足舟山群島之時,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夏秋兩季也正是蚊蟲肆虐、各種腸道傳染病的高發季節。他們雖不費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定海,但卻遇到了強大的“看不見的敵人”——病原菌。這種病菌所引發的各種傳染病,導致了英軍大規模的非戰損失。英國隨軍記者奧塞隆尼曾在《對華作戰記》一書中對1840年7月13日—12月31日英軍在舟山的疾病狀況作了詳細記錄,據不完全統計(僅有陸軍部分,缺少海軍記錄),英軍因病死亡448人,其中死于痢疾者為218人,死于間歇性發燒者91人,死于腹瀉者70人,其余的為各種不知名的疾病致死者(可能是交叉感染,癥狀復雜,不易判定為何病)。奧塞隆尼雖然沒有提供參戰部隊的具體人數,但從中還是能看出英軍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另外,以上統計數據僅僅是一個時間段的,而事實上,英軍還有大量的“后續死亡”。據英文版《中國叢報》對英軍第26團(參與鴉片戰爭的主力團之一)的戰史報告稱,該團離開印度前往中國參戰一年竟有500人死于疾病。
痢疾、腹瀉等腸胃傳染病和間歇性發燒等血液性疾病是夏秋季節多發性疾病,它們以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觸及蒼蠅等為主要傳播方式。在戰爭中,由于戰時生活條件的改變和衛生制度的不健全,發病率和病死率均比平時大為提高。這些疾病多發于濕熱沼澤之地,并導致了不同部隊相異的發病率和病死率(應該與部隊的不同駐扎地有關)。比如馬德拉斯炮兵在稻田中安營扎寨,死亡人數最多;孟加拉志愿軍駐扎在定海附近低洼的潘松地區,就連很多強壯的士兵也遭到了死亡的厄運。而英籍第18團的損失則相對較少,這與他們從一開始就駐扎在城郊的海濱有關;印度籍工兵營駐扎在城西空曠、地勢較高的地方,雖然工作最艱苦、暴曬最充分,但他們中卻很少有人送命。
除了氣候和地理條件,艱苦的生活條件引起的機體免疫力下降,也是英軍大規模感染疾病的重要因素。英軍剛剛占領舟山后,由于對“外人”的恐慌,舟山人民大多逃走,使得英軍缺少新鮮的食物,導致免疫力下降,給各種疾病以可乘之機。同時,不清潔的用水亦是英軍在舟山遇到的一大難題。定海的水質條件本來就差,而且當地人還不時地“向井中投毒”,使得英軍不得不從稻田的排水溝中取水,這為病菌的大肆擴張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此外,惡劣的居住條件也為疾病傳播提供了溫床。據奧塞隆尼在《對華作戰記》的記載,出于籠絡人心的目的,英軍當局規定部隊不能占用定海城中的民房、公房甚至寺廟做營房。于是乎,英軍各支部隊基本都住進了帳篷。帳篷白天要遭到烈日的暴曬,晚上還要受到來自潮濕發臭的土壤、稻田、水溝里的有害氣體的熏蒸。這樣的居住條件,人不患病才不正常!
1840這一年,受鴉片戰爭的影響,傳染病的流行要比以往嚴重得多,舟山、寧波、鎮海、杭州等地都有發生。但這些疾病對當地人影響不大,當地人依舊可以正常生活、生產(已經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對缺乏免疫力的英軍就大不一樣了。盡管英軍也遭遇清軍的頑強抵抗,但由于雙方在武器裝備、戰略戰術上的差距,英軍直接死于戰爭中的人數極少,而更多的是死于各種傳染病。茅海建認為,“就死亡數字而言,英軍在舟山病死的人數是其兩年多戰爭中戰死人數的10倍”。這應是他根據奧塞隆尼所記載的死亡人數448人得出的結論。事實上,英軍在舟山的死亡數字應大大高于此數。英軍在占領定海時未損一兵一卒。占領定海半年后,到了1841年1月,近4000人的軍隊只剩下1918人(據《中國叢報》)。當然這不包括義律在1840年11月前往廣州談判時帶走的部分部隊,但這部分人數極其有限。這樣算來,英軍在半年內竟然損失了1000多人。即便如此,活著的軍人中的絕大部分也都在患病,如英軍第26團1840年底在舟山的273人中就有163人患病(據《中國叢報》)。
英軍在舟山的“不健康”狀況,不但造成了軍隊戰斗力的嚴重下降,限制了英軍在舟山和周邊地區的“執行力”,而且亦是巴麥尊同意義律“將談判地點遷往廣州”的關鍵性原因。義律與琦善談判期間,舟山的“恐怖現象”進一步蔓延,殘酷的現實迫使義律做出了違反政府命令的行為——草草與琦善簽訂了《穿鼻草約》,并退出舟山,改占香港。
如此一來,英軍在中國的勢力再次退到珠江一帶。正是由于這樣,義律沒有完成英軍的既定計劃,引起了英方的極大不滿,導致英國政府臨時改任璞鼎查為全權大使(代替了義律)。由于先期戰略目標沒有達到,英軍調整了侵華的戰略部署,制定了更具野心的“長江攻略”,決定擇時發動向江南腹地的大規模進攻。而這一戰略部署的改變,亦延長了鴉片戰爭的進程。
對于英軍在舟山的糟糕狀況,當時清政府的一些官員似乎也有所了解。比如林則徐就在奏折中說道:“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兩江總督裕謙也曾說:“該夷生長外洋,不服中國水土,探問竊據定海后出天花或染時疫,死亡相繼,殆無虛日。”諸如此類的言說不勝枚舉。但即便如此,清政府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錯失了難得的抗擊機會。惜乎?悲哉!
作者單位:鄭州十九中
責任編輯:姚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