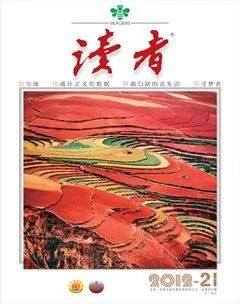美女
契訶夫
我正念大學的時候,坐火車到南方去。那是5月。好像是在別爾哥羅德和哈爾科夫之間的一個火車站,我走出車廂,在站臺上散步。
黃昏的陰影已經落在車站的小花園、站臺和田野,車站遮蔽了落日。不過,從機車里冒出的一團團煙霧被染成淡淡的玫瑰色來看,顯然,太陽還沒有完全落下去。
當我在站臺上走來走去的時候,忽然發現,大多數散步的旅客都往一節二等車廂那邊擁,帶著異樣的神情停在車廂旁邊,仿佛那節車廂里坐著什么知名人物。在這節車廂旁邊,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其中有一個正是我的同車旅伴——一個矮個子炮兵軍官,聰明、熱情、好客,跟我們在旅行中偶然相識、沒有深交的人們一樣。
“您在這兒看什么呢?”我問。
他什么也沒說,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個女人。那是個年輕姑娘,十七八歲,穿的是俄羅斯服裝,頭上什么也沒戴,只有一小塊披巾不經意地搭在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長的女兒或妹妹。她站在車廂的窗子旁,跟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乘客談話。
這姑娘是個美女。這一點無論是我,還是跟我一起欣賞她的那些人,都絕不懷疑。
要是照老規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繪一番,那么她最具魅力的就是那一頭淡黃色、波浪起伏、厚厚的秀發。它們披散著,頭頂上系著根黑色的發帶。至于她身上的其他部分,要么不太合適,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雙眼睛,不知是出于賣俏呢還是由于近視,總是微微瞇縫著,鼻子微微向上翹起,嘴很小,側影輪廓不分明,肩膀窄得與年齡不相稱。盡管如此,姑娘給人的總體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麗。望著她,完全可以確信,俄羅斯人的臉無需整齊端正便能顯出其美麗。不僅如此,如果把這姑娘的翹鼻子換成一個端正又完美的,反倒會使她的臉喪失全部的嫵媚。
站在窗旁談話的時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氣而瑟瑟顫抖。她不住地回頭看我們,一會兒挺起身子兩手叉腰,一會兒又抬起手整理頭發。她有說有笑,臉上的表情忽而驚奇,忽而恐懼,我就沒見過她的身體和面容有安靜的時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這些細微而無限優美的動作,在于她的微笑、表情的變化,在于她向我們投來的匆匆一瞥,在于這些優美的動作與青春、活力、笑語聲中流露出的純潔,以及我們所喜愛的小孩、小鳥、小鹿、小樹身上的纖弱與和諧。
這種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與華爾茲在花園里飛舞,歡笑和快樂相映成趣,卻不能與嚴肅的思想、悲傷和寧靜相容。似乎只要站臺上吹過一陣大風或下一場大雨,她那柔弱的身子就會枯萎,她那變幻莫測的美就會像花粉一樣消散。
“是的,果然……”軍官在第二遍鈴響過后,往自己的車廂走時嘆氣說。
至于“是的,果然……”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妄加評論了。
也許他感到惆悵,極不情愿地離開美女和春的晚會,走回窒悶的車廂;也許他跟我一樣,正不由自主地為美女、為自己、為所有垂頭喪氣地走回自己車廂的旅客而惋惜。軍官走過車站的一個窗口,看到里邊電報機旁坐著一個臉色蒼白、頭發發紅的電報員,便嘆口氣,說道:
“我敢打賭,這電報員一定愛那姑娘。生活在天地間同一屋檐下,與那個輕盈的人物在一起而不相戀,豈不超越了人的本能?然而,我的朋友,如果你弓腰駝背、蓬頭垢面、單調乏味、油頭滑腦,卻愛上這對你并無好感、俊俏可愛的小姑娘,將是怎樣的不幸、怎樣的嘲弄啊!或許事情會更糟——試想,這個電報員墮入情網,同時卻早已婚配,而他的妻子同他本人一樣也是個弓腰駝背、蓬頭垢面的人……那真是苦透了!”
在我們這節車廂旁邊,乘務員正胳膊肘靠著門口的扶手站著,往美女那邊觀望。他那張臉因晝夜顛倒和車廂的顛簸而疲憊不堪,顯得憔悴、松弛,令人膩煩,現在卻流露出脈脈的溫情和深深的憂傷,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純潔、妻子、兒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為姑娘不屬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遲鈍、滿臉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們的幸福,對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鈴響了,汽笛長鳴,火車懶洋洋地開動了。站務員、站長從我們的窗前閃過,接著是花園、美女以及她那俏麗、天真、慧黠的微笑……我把頭探出車窗往后看,看見她目送火車走后,在站臺上走動,經過電報員所在的那扇窗戶,朝花園跑去。車站已不再遮蔽西邊的景色,田野敞開了胸懷。太陽已經落山了,一縷縷黑煙在綠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氣息中,暗淡的天空下,我們的車廂里處處是憂傷。
我們熟識的乘務員走進車廂,點起了蠟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