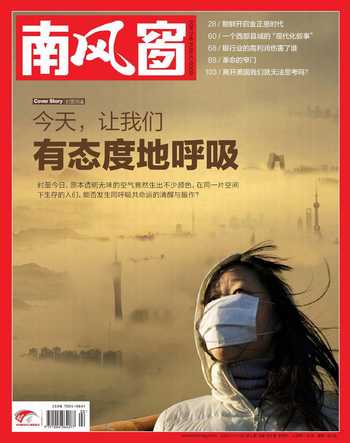外交妥協的藝術
謝奕秋
一份預定1月5日由五角大樓公布的美軍戰略利益評估報告,建議白宮放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略,改采“1+”戰略,即全力投入一場戰爭,同時干擾潛在的敵人。批評者說,這也許會誘使野心國家在美國卷入一場戰爭時,挑起另一場戰亂。其實,財政困窘下能屈能伸是美國戰略界的傳統,明智的妥協比死撐面子更利于美國恢復生機。尼克松與中國媾和,從越南戰場撤軍,成全了北越,也撐大了蘇聯的胃口,最終讓阿富汗戰場埋葬了蘇聯帝國。
即便是被指為越戰“始作俑者”的肯尼迪,也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一展妥協智慧:用對古巴海上封鎖而不是入侵的方式,迫使赫魯曉夫以宣布撤回在古42枚導彈,交換美同意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舊型號導彈。試想,如果美國在逼迫古巴附近蘇聯核導彈潛艇上浮時使用的是大威力的深彈,第三次世界大戰恐怕早已是歷史名詞了。
不久前一名中國外交官談到,不能簡單地用“軟”、“硬”來界定中國外交,斗爭和妥協都不是外交的目的,而是方式和選項。但他一句“中國無意也無力在亞太排擠美國”卻引來無數板磚,而其“智慧比拳頭更重要”論,也招來“主權相讓,國土被占,烽煙四起,群狼環伺,漁民被抓,漁船被扣。一味忍讓,唾面自干,這算哪門子智慧?”的詰問。可見,不少國人把哲言“外交是妥協的藝術”單純理解為“外交就是妥協”,而把“藝術”二字丟了。
外交“藝術”通常不是官僚系統的產物,當不時“求諸野”。而民間智慧五花八門,是否能寬容“天真、危險”的新思維,決定了“外交藝術”的想象空間。美國學界去年出現華府應該“放棄臺灣”的論調,先是格拉瑟教授發文稱,放棄臺灣防務可能是讓美國與中國大陸維持和平,避免惡性武力競爭的辦法;大半年后,保羅·凱恩發文稱,美國當以停止對臺軍售與援助、提前終止“協防臺灣至2015年”的公報,換取中國“一筆勾銷”目前所持美國公債。這些挑戰美國現行法案的論說,得到主流媒體如《外交》雙月刊和《紐約時報》的青睞,引發社會熱議,正說明了外交藝術的生成是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需要海納百川的機制。
未經公開辯論的密室政治,或許曾推開中美間緊閉的大門,但那是時勢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時勢。作為基辛格的門生,里根第三任國家安全助理麥克法蘭曾異想天開,利用伊朗深陷“兩伊戰爭”、急需先進武器的窘境,以出售數千枚美制導彈為籌碼,試圖與伊朗改革派握手言和,締造震驚世界的外交奇跡。但麥克法蘭不是基辛格,他秘密飛往戰火紛飛的德黑蘭,結果沒有見到伊方任何高官。美方以軍售為突破口的妥協外交遭受慘敗,不但對釋放被黎巴嫩真主黨扣押的人質影響甚微,而且還在國會山引發了“尼加拉瓜軍援門”的險惡風暴。
眼下阿富汗塔利班又在玩在外國設辦事處、談判“交換關押在關塔那摩之囚犯”的把戲,美國外交部門的回答很婉轉:“如果這隸屬于一個由阿富汗人倡導、并得到阿富汗人支持的進程,并且阿富汗政府認為這將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話,那么我們也將在其中發揮作用。”瞧,沒有義正詞嚴,也沒有一廂情愿,進可攻退可守。所謂的外交妥協藝術,盡在只言片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