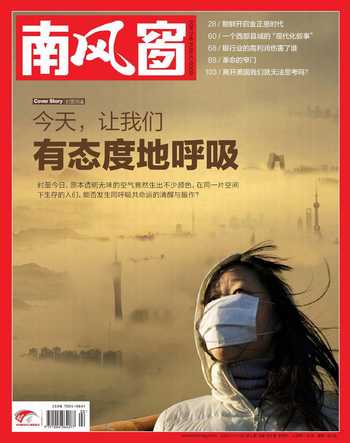為什么借法官?
葉竹盛
有一種狀元叫做“辦案狀元”。
鄭州市金水區法院的“辦案狀元”鄭文文法官靠下面這組數字走上了“狀元之路”:“鄭文文結案情況:2007年,164件;2008年,177件;2009年,273件;2010年,332件;2011年,截至目前收案561件,結案95%。”
2008年至2010年,連續3年榮膺南京市玄武區法院“年度辦案狀元”的李偉法官,每年的辦案量都在400件以上。巾幗不讓須眉,2004年,無錫市惠山區法院女法官徐琳一年內審結案件420多起,成為當年的“辦案狀元”。
更為驚人的紀錄由上海市閔行區法院的“辦案狀元”徐玉弟法官所創造。根據閔行區政府網站報道,2005年至2007年,徐玉弟每年經辦的案件都在1000件以上。
如果扣除周末和公共假期,一年辦理400件案子就意味著每個工作日要辦兩件。也就是說,半天時間內,法官就要重組案件事實,從繁復的法律條文中準確鎖定法律依據,然后再寫出文理通暢、法理到位的判決書。“基本上神仙都來不及。”有過法院工作經歷的著名律師陳有西說。
盡管法官們的勤勉值得贊許,我們也不能任意揣測法官們故意枉法裁判,但是當一個案子在短時間就迅速裁決了,我們還是有理由質疑辦案的質量。
大家都說“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卻很少人說“倉促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審判”。倉促與拖延一樣,都是司法裁判的大忌,都有損于司法正義。那么,面對日益增多的案子,我們是否應該給法官“減負”呢?要如何才能給法官“減負”呢?
“請借我幾個法官”
面對沉重工作負擔的不僅僅是“辦案狀元”,經濟發達地區的法官普遍超負荷工作,根據2008年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統計數據,2007年,東莞市兩級法院審判法官人均結案240件。“尤其是下半年,經常寫判決書要到深夜,周末也要忙著處理案件。”東莞市一位基層法官對《南風窗》記者說。因此一些法官常戲謔稱自己的工作是“5+2”和“白+黑”。東莞市法院幾乎是全國最忙的法院。據統計,2007年,東莞市法院人均結案數是全國法官人均結案數的5.14倍,而這個數字還在逐漸增大中。
為了給法官“減負”,能夠想到的第一個方案自然是增加人手。2011年12月14日,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貼出公告,向全國借用4名法官和一名研究室工作人員。公告稱:“借用法官報酬從優,并向所在法院支付一定的借用費用。”這不是該法院第一次向外借用法官,“往年借的更多,都是10幾20多個的借。”一位在該法院工作的法官告訴本刊記者。
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第25條提出:“實行法官定額制度。在考慮中國國情、審判工作量、轄區面積和人口、經濟發展水平各種因素的基礎上,在現有編制內,合理確定各級人民法院法官定額。”在實際操作中,法院轄區的戶籍人口是確定法官編制的首要指標。但是在類似東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人口數往往占了總人口很大的比例,根據戶籍人口所確定的法官數量無法應對日益增多的案件。
吊詭的是,若按法官總人數計算,中國法官的平均案負并不重。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2011年3月向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所做的工作報告,全國地方各級法院2010年共受理1137萬余案件。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的數據,同期全國法官人數約為19萬。按這個數字計算,法官人均辦案約為60件,遠遠低于“辦案狀元”動輒高達數百的辦案數量。
若按人口比例計算,我國平均6842人就有一個法官。這個比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并不算低。
奧妙就在于,不少掛著法官頭銜的法官,并不從事審判業務。按照我國《法官法》規定,只有具有“審判員”或者“助理審判員”職稱的才能進行審判。19萬法官指的就是至少具備助理審判員職稱的法院工作人員。
一位研究者在一篇題為《建立中國法官定額制度若干問題研究》的文章中總結說,由于法官職位的行政化、法院執行人員與法官混為一談等原因,我國有近2/3的法官并不直接從事審判業務。即便按照保守統計,第一線審判法官也僅占法官總數的60%。這位研究者在文章中說:“如此之多的資深法官并不直接審理案件,這在世界各國恐怕都是少有的。”
這么說來,類似“借用法官”的辦法來解決案負太大的問題也就可以理解了。一方面是法官總編制已滿,難以在編制內引進新法官,而一部分法官又忙于非審判業務;另一方面則是案件累積太多,受到“審限”和“結案率”等硬指標的約束。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法官人手緊缺,卻又一時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法官“減負”的加減法
案負沉重是一個事實,法官人數短缺卻不是本質原因。因此東莞法院借用法官的做法也許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畢竟這只是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在陳有西看來,要解決案負太重的問題,“很多人想的是增加法官,我的意見是減少法官,從19萬減少到5萬,也能夠辦好案子。法官就是審案子,大量的文字工作、輔助性的工作等等交給法官助理做。每個法官配四五個助手。法官就是抓判決主文。”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孫笑俠也持類似觀點,他提出,應該“讓一部分特別優秀的、業務精湛的法官脫穎而出,這些人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官,其他人員作為他們的助理。法律難題由這些法官裁斷,助理人員輔助解決基礎性的工作”。
19萬法官解決不了的問題,為什么5萬法官就能解決呢?孫笑俠以美國最高法院為例,每名大法官可配備1名秘書和4名法官助理(首席大法官可配備5名),在輔助人員的幫助下,“9個法官就能處理很多問題”。在他看來,真正的法官應該是“思想者”,而不是“事務官”,“中國的所有法官都在做一些不該歸他們做的事情”。要將“不該歸他們做的事情”剝離出去,就要實現法官職業化。要實現這一點,也就是要明確法官的職責,使他們獲得自主審判權。
“如果主審法官有自主權,很多案子都能辦好。很多案子之所以久拖不決,不是法官的原因,是外部干預的原因。”陳有西說。
當然,另一方面,法官職業化也要求法官有較好的素質,才可能像“思想者”一樣高效地解決案件中的法律疑難問題。陳有西的實踐經驗告訴他,“有些法官法律功底不行,對法律構成要件,案件焦點等等自己都心里無數,在法庭上隨便雙方律師怎么講,基本上沒有主意。”
要給法官做“減法”,從19萬法官中挑出優秀法官成為“真正的法官”,孫笑俠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狀態下,存在很現實的難題。“上海高院曾搞過試點,但后來停下來了。原因一方面在于編制,另一方面則是同事的積極性問題。從100個里面挑出30個,另外70個是有意見的。”
既然法院內部難以推行法官職業化的改革,陳有西則想到了從律師中直接選拔法官的做法。法官和律師同屬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兩者之間本應沒有職業障礙。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向社會公開招考法官,最后有4名律師通過招考成為了最高院法官。但這一做法在基層法院系統并沒有鋪開。
除了因為法官受制于《公務員法》以外,孫笑俠認為從律師中選拔法官主要障礙有兩個,一是“決策者在觀念上對律師的信任不夠,對律師的看法也比較偏頗”;另外則是因為中國法律職業的統一性還沒有建立起來,“中國法官和律師最大的不統一在于職業信仰和職業倫理上。司法職業中應該有一些共同點,大家都應以憲法、法律至上,但是法官的職業倫理被統一到行政官的倫理上了,律師就被晾在一邊了。”
一方面減少非職業化的法官,另一方面增加優秀的職業化法官,一加一減之間,法官們才能做到真正“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