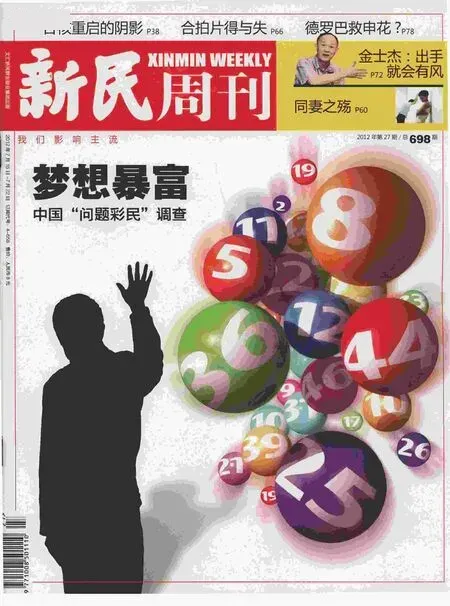香港“文化遺老”也斯
蘇慶先

也斯罹患肺癌的消息已在文友中傳開,但眼前的他,卻絲毫顯不出遭受病痛折磨的痕跡。記者在香港會展中心一間會議室里見到他時,他一身格子西服,頭戴鴨舌帽,就那么溫文爾雅地、安靜地坐著。
也斯是香港名作家,也是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今年有些特別,他被書展舉辦方評為“年度作家”,并將在書展現場設立專區,以“人文對話”為主題,展示他的詩作、攝影作品、書評等,以及他與多名攝影家、藝術家及設計師的跨媒體合作。
他的獲選可謂實至名歸。因為正如有人說過的,在香港,你也許再難找到像也斯那樣的作家,其個人的成長、寫作經歷和香港這座城市60多年的發展如此緊密相連。
寫不盡的香港
也斯原名梁秉均,其作品講述的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記憶,以及一座城市背后的故事。
香港似是也斯寫之不盡的題材。他最先引起人們注意的作品,是上世紀70年代結合中國神話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書寫香港現實的短篇集《養龍人師門》及中篇《剪紙》。直到年前出版的小說《后殖民食物與愛情》,仍然嘗試細說回歸十多年的香港故事,獲得第十一屆香港文學雙年獎。除了小說,他也寫了不少以香港為題材的詩和散文,如三聯“作家與故鄉”系列的《也斯的香港》。
也斯也非常關心香港的文化,以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文化脈絡。談到最近港陸之間的口誅筆伐,他說,研究香港50年代的文化,可以幫助我們面對這種現狀。
1949年以后,有近百萬人從上海、北京、廣東等地移居香港,其中包括眾多知名文化人,如宋琪、曹聚仁、葉靈鳳、費穆、力匡、胡金銓、易文等,他們這些“南來一輩”,豐富了香港的文化,為香港帶來一些正面的能量。
之后,到1952年邊界確定下來后,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文化交流戛然而止,但傳統戲劇、通俗小說以及都市文化等,在香港一脈傳承的同時,也都有各自的發展。因此可以說,香港文化的根是在大陸,雙方歷史上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香港本來的優勢是,跟中國大陸和西方都有溝通和對話。西方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或者中國對西方文學的理解,現在還存在很多隔膜。如果能更好地對話,進一步認識對方,對大家都有好處。”
近些年來,也斯慢慢地發現自己所認識的香港,“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慢慢發生了變化,某一天醒來,習以為常的事物又少了一件,先是騎警,然后是電車,接著是老字號的店鋪,以及整條街都慢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地鐵,是摩天樓,是連鎖店和大商場。現在我能做的,是通過文字引起大家思考和反省”。
他承認香港的商業化對文化的影響。首先是1995年《蘋果日報》在香港的誕生,在也斯看來是香港報業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現,直接導致報業競爭加劇,幾家碩果僅存的知識分子報紙,如《星島晚報》等——其書評版或小說連載版一度成為香港文化人的陣地——在1995年之后相繼關門大吉,成為香港報業“蘋果化”的犧牲品。還有,香港以前的書店都是開在二樓,現在要被迫搬到六樓,之后六樓也呆不下去只能關門。“作家寫書不容易出版,詩集就更沒人愿意出,年輕人可能更愿意去買樓。”
也斯善寫人情,“我寫政論未必好過李怡、黎智英及林山木,我是寫小說的人,對人的觀察可能較好”。他從1998年開始用小說寫回歸后的港人生活,后來寫成《后殖民食物與愛情》。這本小說其實是多角度地寫了1997年之后一般人的心態。“因為大家覺得回歸之后,會不會很慘?會不會很高興?其實,一般人的生活還是如常的,但中間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有一些是個人的,也有一些是社會上的,比如非典時期,有很多問題出現,怎樣處理這些問題?我就想從普通人的角度去寫香港生活。”
成為作家
也斯1949年生,當年,父母抱著五個月大的他從廣東新會移居到香港。雙親都是知識分子,“父母不懂帶錢來港,只會帶書”。也斯4歲那年父親積勞成疾,郁郁而終,他的筆名“也斯”,與父親有關。他說:“我爸爸的名字中有‘斯字,嗯,那么我就‘也有‘斯字。”這或許就是“也斯”的出處了。
與父親的郁郁寡歡不同,他的媽媽很開朗,與其妹妹一邊貼火柴盒穿膠花,一邊念《赤壁賦》、《李陵答蘇武書》、《長恨歌》,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就像現在唱卡拉OK,我當時覺得很好聽”。他對文學的興趣,就始于當時。
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畢業后,也斯在報館工作了8年,做翻譯,寫專欄,專欄文章涉及書評、影評、藝術評論等,之后到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修讀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寫過不少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論文,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詩。回到香港后,他先后在浸會、港大、嶺大教授比較文學,去年患病后,每周只上一天課。
在香港,有人說學者易為,文人難做,他卻說:“現在做作家幸福,做學者辛苦。80年代我在港大教書,兩年班不用考試,4月底學期結束,今日港大就不是這樣了。”反而作家容易做。 當然這可能只是表面,實際上卻是“現在年輕作者要出第一本書很容易,藝術發展局一定支持,你寫的東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這對作者是不是好事?放在書店,一個星期銷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遠不見天日”。
有學生問他如何做個大作家,也斯回答:“不如你先做一個好讀者。”他的作品《半途》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獎,《布拉格的明信片》也獲同一獎項小說組獎。不過,他說自己以前鄙視文學獎,但看到作家越來越難做,也終于認同了,“但要將評審公開,讓作者明白為什么得獎,比起三尖八角的獎杯或幾千元獎金更有意思”。
對也斯而言,寫詩是一種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時間靜下來寫詩,是幫你向內看,反省自己的生活。”香港新詩日漸式微,反而歌詞精彩絕倫。他認為新詩并未過時,“林夕也是讀新詩出身的,他也寫新詩,因此寫歌詞修養便好一點。現在的詞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寫得好的詞我覺得也是詩,鮑勃?迪倫的歌詞其實也是詩”。
患病之后
也斯并不抽煙,卻患上了肺癌,為此一直喊冤。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何必偏偏揀著我”,但他可沒工夫悲哭,“喊苦喊悲都沒用,我都沒喊過,也不挺胸做英雄,我只希望泰然處之,找個方法面對它”。
當初醫生懷疑他患了腸癌,之后證實是肺癌,“第三期,差不多接近第四期”。消息傳出后,即使素昧平生的讀者也介紹醫生給他。他看過臺灣一個使用另類療法的“神醫”,讓他只喝果汁,服食營養素,其他食物都別碰。“我問為什么,他說:‘你不要問!那我不能接受,我一定要弄明白,即使輸了也是自己的選擇。”
也斯一生游走于中西方文學之間,看病亦然,他找了一名中醫主診醫生,“我做人一以貫之,毫不復雜,從念書到治病都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我尊重西醫,他們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又想中醫可能也會有所幫助。”對于未來的路怎么走,他態度樂觀,但不敢說處境樂觀。
訪談中的也斯時而沉靜,時而咧嘴大笑,那是一種至真至誠的態度。如果用他作品中的一句話來形容,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中的描述再確切不過了:臉上的表情不是憂傷也不是歡喜,只是坐在那里,好像真的在沉思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