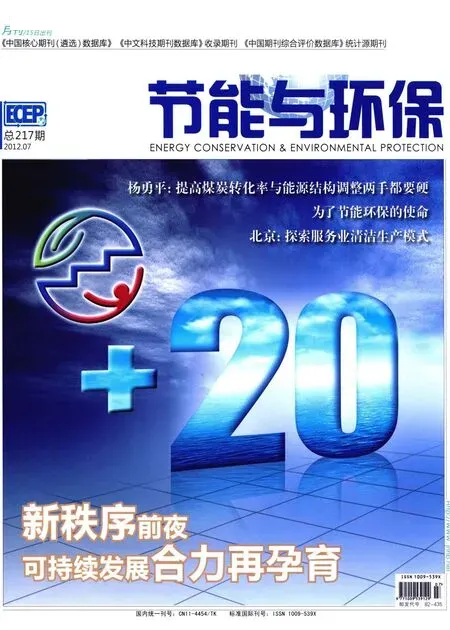新秩序前夜,可持續發展合力再孕育

曾幾何時,“里約+20”峰會被民眾寄予厚望,被稱之為拯救人類的最后機會。然而,這種厚望,這最后的機會,隨著會議的結束,在民眾心里烙上了深深遺憾的印記。之所以關乎全球環境保護、關乎傳統化石能源使用、關乎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峰會與20年前的地球峰會相比,呈明顯倒退,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一支獨大的一元社會的舊秩序正在瓦解,發達國家不愿履行作出的承諾;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力量雖然已經不可小覷,但還沒有能力取代舊秩序。新舊交替之際,關于全球不同需求、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必然面臨更多的難題。
p26 峰會成果被視為“我們不希望的未來”
p28 倒退是因為新秩序尚未形成
p30 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正在重新孕育
p32 理性認識峰會成果

峰會成果被視為“我們不希望的未來”
6月22日,“里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的成果文件《我們憧憬的未來》正式出爐。然而,這個有著令人憧憬的名頭、卻由于缺乏實質的可操作性的內容備受詬病。
成果被指是新花瓶
對于峰會的成果,各國官方都比較高調,而在官方之外的聲音則是異口同聲的口誅筆伐。對于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中外對話》北京副總編徐楠介紹,政治家們予以高度評價,是因為深知其得來不易;而公民社會的普遍不滿,來自常識。徐楠所說的常識恐怕是指與1992年里約地球首腦會議所取得的成果相對比。
20年前,各國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仍然達成了里約系列原則、三大環境治理公約、二十一世紀議程等重要成果。“但二十年后在同一個城市,我們看到的是各國政治雄心的退步。在這里,甚至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性問題上都往后退縮了。峰會談判在資金援助與技術轉讓問題上依舊沒有進展;淘汰化石燃料補貼仍是兩行空話;綠色經濟的概念定義模糊指導意義不足;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改革為新的環境組織,同樣計劃落空……整個文本中,充滿了太多諸如‘認識到’、‘進一步探討’、‘決定考慮’等言而無物的辭令,進一步讓本已缺乏法律約束力的這份文件,成為一個新花瓶。”青年里約行動小組協調人那拉榮泰如是說。
“留給我的感覺是,五六萬人參加、全球矚目的‘里約+20’峰會,熱鬧過后,留下一紙沒有法律強制力的文本文件。”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陳迎對本刊記者說。陳迎以中國政府國家發展改革委專家成員的身份全程參加了本次大會。“峰會形成的文本是個大綱、一個框框,具體到各個領域還得到氣候變化大會去談。”陳迎補充道。
不滿源于失落
1972年斯德哥爾摩大會將環境保護的概念第一次上升為與會各國政府都高度認可的通用慨念,20年后的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搭建好了通往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機制和框架——也就是說,如何履行成為1992年人類可持續發展里程碑樹立之后,國際社會面臨的頭等重要大事。那么履行的情況怎樣呢?在此次全球矚目的峰會召開前夕,也就是6月6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里約發布了名為《全球環境展望5》的報告。報告顯示,全球90項重要目標中只有4項取得了顯著進步,40項目標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魚類種群破壞與退化,氣候變化與干旱等24項目標幾乎停滯不前。還有8項目標非但沒有進步,反而情況還在繼續惡化。如果以“顯著進步”為標準,衡量國際社會履行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所規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執行情況,就會得出履約4比90的超差成績!
抗議不斷
公民社會渴求改變,渴求在履行方面有實質性突破。但結果是,“認識到”、“進一步探討”、“決定考慮”等言而無物的辭令,成為峰會成果文本的主體。就在這個成果文本匆忙完成談判提交政府首腦會議后的第二天——21日,里約峰會會場爆發了民間組織的集中抗議。數百名來自青年、環境、婦女和土著人士組成的代表,集中在高級別會場門口,高喊口號表達各自對這份里約文件的不滿。世界自然基金會、世界環境與發展研究所等眾多國際機構,也以機構評論、新聞發布會和聯名公開信等方式,予以抗議。
一封針對峰會成果文本、題為《我們不期望的未來》的公開信對峰會的所謂成果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文中說到,“我們期望的未來需要承諾與行動,而非僅是許愿。需要治理社會、環境與經濟危機的緊迫性,而非一再拖延。需要與公民社會合作協調,而非僅是政府不痛不癢的立場。所有這些,在此次會議最后文件的283個段落中,沒有絲毫體現。這份題為《我們期望的未來》平庸無物,嚴重缺乏雄心和行動,甚至都沒有充分強調問題的緊迫性。”

20年前,12歲女孩鈴木瑟玟在里約世界高峰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大人們”對于環保要說到做到,否則就是對下一代的不負責任。然而20年過去了,一切都沒有改變。

峰會期間巴西土著部落的成員們在里約熱內盧的郊區建立起了“人民峰會”的會議營地。“人民峰會”是由200個世界各地的生態環保組織和社會活動組織發起,旨在聲討所謂的“綠色經濟”概念,而這一概念正是由115個國家領導人在一次聯合國會議上首次提出的。會議營地的名字為“Kari-Oca”,這在圖皮—瓜拉尼語里的意思是“白人的房子”。這個土著居民的會議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即“里約+20”)的對臺戲。

一位瓜拉尼男子帶著“里約+20”的腕帶
會場外,各種抗議活動也絕不少見。在峰會十幾公里外、里約城市最東端Flamengo的海灘,來自全球的非政府組織和巴西當地土著部落成員召開“人民峰會”,與里約中心的大會唱“對臺戲”。“20年前,我是為了我自己的未來在奮斗;今天我是為了我孩子的未來而奮斗!”曾在20年前里約地球峰會上用演講讓世界沉默了5分鐘的加拿大女孩鈴木瑟玟再次來到里約。如今,鈴木瑟玟已經是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她站在臺上說,“20年過去了,一切都沒有改變。”
“1992年,我們還在嚴厲地批評當時的努力做的不夠;但更具諷刺意義的是,20年過去了,我們還要回頭來保護當年的成果。如果把20年前的地球峰會作為一個標志,今天的我們倒退了很多。”創綠中心總干事盧思騁如是說。
倒退是因為新秩序尚未形成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風云際會,快如白駒過隙。三五十年不過彈指一揮間,恍如昨日。然今日必定是今日,往日已成明日黃花。站在今天的基點上看,1992年地球峰會所取得的成果堪稱輝煌,這輝煌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格局密切相關;20年后的今天,之所以倒退,也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巨變的結果,而且,這種變化早在10年前就已端倪初現。
帶頭大哥今非昔比
20年前,美蘇長達數十年的兩極冷戰,由于蘇聯的解體而告一段落。隨著冷戰烽火的熄滅,意識形態之爭似乎也就此銷聲匿跡。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國帶頭的歐美經濟、政治集團不失時機的規劃著一統天下的新未來。他們為這個新未來做出了讓步,甚至慷慨解囊。解決環境問題既是發達國家本身的問題,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貧困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在聯合國處于強勢地位、帶著戰勝強敵的自豪感和強大的美元,美歐等強國積極支持環境保護——花錢,沒問題,一切盡在掌握,作為強者,承擔更多的責任,意味著更大的規則主導權。
歐美國家除了答應直接給予資金技術的支持,同時還采取了既能迎合發展中國家發展需要,又能保護自家門口環境的一箭雙雕的經濟策略:將第二產業低成本輸出。然而,歐美國家的如意算盤卻未能如意。按照低成本原則輸出制造業、轉移高耗能產業和重工業,恰恰加速了自身的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20年內連續的金融和債務危機,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正是全球加速形成統一市場的結果;正是金融在全球范圍不斷驅逐實體經濟的結果;正是一元主義占據規則主導的結果。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不是歐美真心想要的,他們想要的只是市場,而非市場所在國的崛起。
另一方面,原本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的蘇東劇變,不僅沒有成為歐美強國領導力強化的因素,卻變成了西方領導地位下降的開始;經歷顏色革命之后的俄羅斯,在徘徊一段時間之后,竟然棄西方而去;中國不但沒有在蘇東劇變之后成為最后一塊倒下的社會主義多米諾骨牌,反而橫空出世;歐美在步入高峰體驗之后,迎來的竟然是“西方失去的十年”。
曾經雄心勃勃的歐美國家,愿意為新未來付出的國家,在策略不僅沒能達到預期目標,反而歪打正著幫助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這不能不令歐美國家懊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于推動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的責任與承諾很難不與推脫、反悔、刁難連在一起。
金磚國家正在影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迅速崛起的國家被稱之為金磚國家。這些國家以廉價商品、豐富資本、充足勞動力、巨大潛在市場等,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改變著世界經濟發展態勢,推動國際經濟關系的調整,促進力量格局的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教授認為,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從力量分布、決策體制、問題議程和發展模式四個層面給世界經濟帶來新變化。
首先,世界經濟權力和財富將加速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這種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版圖正在發生劇烈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加速了新興國家向西方的追趕過程。新興國家的崛起不是危機事態下的短暫現象,而是一種持續的長期趨勢,體現為全球經濟力量從西向東、由北到南的歷史性轉移。第二,全球經濟的決策權變得更加平等和均衡。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新興國家在世界經濟決策體制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提升。在全球經濟決策權的分配上,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參與數量趨于均等,影響效力也更加均衡。
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之在全球經濟議題上的話語權明顯提升。在發達國家主導的議題上,新興國家開始據理力爭,通過團結行動或臨時組合來維護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權益;新興國家開始主動倡議一些新的經濟議題,如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增加對貧困地區的經濟援助等。這對于改變南北發展失衡,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成果共享具有重要和積極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自主性凸顯。
上述的影響在幾乎與"里約+20"峰會同時召開的G20峰會有明顯的體現。6月18~19日,G20峰會在墨西哥舉行,輿論普遍認為:金磚國家提振了整個G20峰會。向IMF增資750億美元之舉引來全球關注,與歐盟的低落形成鮮明對照。應該說,金磚國家的崛起,和傳統大國抑制其壯大形成新一極的角力,也正是國際政治格局的基本現實。本次G20峰會,再次顯示了金磚國家的潛力和能量。

峰會期間,十幾名堅持關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青年代表悉數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這些成員是做為中國青年代表參與“里約+20”峰會的。
鴻溝加劇難修正果
1992年地球峰會之所以取得豐碩成果,與美歐對之后全局掌控能力的自信及新市場收益的預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那時的歐美,獨處全球政治、經濟領導地位,財大氣粗,在解決應該解決的環境問題的同時,又大大秀了一幕慷慨大度的姿態。而如今(其實從10年甚至更早之前),歐美國家已經對局勢有了新的認識:新的未來、新的市場不再是他手中的孫猴子,他,歐美國家也不再是無所不能、法力無邊的如來佛。
如今,發達國家面臨著與20年前完全不同的經濟形勢——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以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你看看誰最有錢,你就去找誰。”在“里約+20”峰會談判場內,一位歐盟代表在回應77國集團提出進一步加大資金資助的要求后,干脆這樣回應。在預期無法實現、局面難以一手遮天、經濟力量此消彼長的現實下,使歐美國家不愿履行所做出的承諾。
承諾打折是“歐美大哥”常用的伎倆。這種伎倆早在1992年里約峰會不久就開始上演了。僅舉一例:在2002年南非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大會上,以“行動”為主題擬定了包括資金支持在內的長達65頁的執行計劃后,僅僅不到一年,官方開發援助(ODA)就從1992年的583億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最低水平——487億。像這樣的背棄承諾時有發生。背棄承諾的行為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不僅沒有彌合,反而愈來愈深。這也直接導致了在此次大會提出的綠色經濟、體制框架以及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三大新議題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嚴重的互信問題。很難想象,在缺乏互信的氛圍內能達成什么有執行力的文本——況且,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的確像毒蝎一樣狠狠蟄了他們一下,雖然并不致命,但已經讓他們感到很痛。
一句話,在目前的情況下,舊秩序正在式微,讓那些只對自己未來著想、自己又有麻煩的歐美國家對環境保護負責、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恐怕真的不現實。
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正在重新孕育
在歐美國家政治、經濟式微而以金磚國家為首的的新興國家、經濟體實力不斷增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隔閡越來越大的現實背景下,“里約+20”峰會取得的成果必定是原則性、政治性強于其實質性、可操作性。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需要新的合力。
角力進行時
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是全球的事,全球力量必須凝聚起來——達成妥協后,制定實質性、可操作性強的國際合作契約。目前的情況是,各方力量都在角力——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角力。
這種角力在本次峰會的談判中尤其突出。以“綠色經濟”為例,從2010年發達國家提出概念,直到2012年6月2日第三輪非正式磋商結束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僅就“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重要工具”達成了一致,而在綠色經濟“可衡量的指標”和“可操作的機制”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為什么不能達成一致呢?6月20日下午,溫家寶總理在峰會演講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發展綠色經濟應當堅持因地制宜,支持各國自主選擇綠色經濟轉型的路徑和進程。發展綠色經濟要注重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有助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注重互利共贏,不以綠色經濟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把發展綠色經濟作為各國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的有效途徑。”溫總理的演講明確表明了發展綠色經濟的態度、立場和操作方法。
陳迎對發展中國家對發展綠色經濟的態度、擔心做了進一步的解析。“綠色經濟是歐盟提出來的,他們希圖在本屆峰會上確定路線圖及各種指標。發展中國家不反對發展綠色經濟,而且愿意為此努力,但一旦制訂了路線圖、確定各國指標,就得嚴格執行。而這樣,實質是抹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基本原則。”他解釋道:“發展綠色經濟是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而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發展、環境和經濟三者的協調,發展中國家正處在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快速發展階段,不可能將社會發展這一主題忽略掉,因為那樣的話,發展中國家將面臨現實的危機。”
陳迎告訴記者,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主導的綠色經濟有三怕:“一怕發達國家拿綠色經濟替代可持續發展;二怕主導國家制定一刀切目標;三怕在資金、技術匱乏的情況下,一旦承諾,就將面臨極大的違約風險。”他認為:“鑒于以上擔心,發展中國家只承認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工具之一、途徑之一,綠色經濟不能完全替代可持續發展;發展綠色經濟,應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因地制宜選擇模式,不能將一固有模式強加給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兩條腿走路
“在本次峰會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交鋒非常激烈,除在‘綠色經濟’有激烈交鋒外,在是否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否要將歐美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技術轉變為市場化等等問題都有明顯而激烈的交鋒。”陳迎對記者說。“發展中國家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基本原則,而發達國家則堅持共同無差別的原則。而一旦執行共同無差別的責任的原則,對于已經經過經濟高速發展期、現處于經濟穩定、成熟期的發達國家而言,就等于免除了他們之前因經濟快速發展造成對全球環境污染、破壞應負的責任;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環境保護固然重要,但發展經濟、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就業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為迫切的要求,如果要求發展中國家環境至上,而將社會發展置之度外,顯然不具有公平性。”陳迎對發展中國家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的必要性再次進行了闡述。
激烈的交鋒使談判的氛圍白熱化——白熱化的氛圍無助于談判成果的實質性推進。另一方面,歐美國家開始采取消極策略。這次被稱為“一代人一次的機會”的“里約+20”峰會眾多發達國家的首腦都是派代表參加的,如美、德等。“這首先表明這些發達國家不熱衷這次大會;其次,為了逃避因承諾的資金、技術支持的拖延、爽約而遭到的質責;最后因為歐美經濟狀況不好,更沒有出資金、出技術的意愿。”陳迎說。當然,這種改變并不是積極的改變:應該承擔更多責任的發達國家不重視這樣的峰會,對于急需資金、技術治理環境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肯定不是好事。說歐美國家不重視不是空口無憑。在幾乎與本次峰會同時召開的G20峰會上,歐美國家領導幾乎盡數到場。有學者稱,歐盟正在試圖淡化峰會、有步驟地推脫自己的責任。
“國際社會一直試圖推進談判進程,如2002年的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大會,但推進的路途充滿坎坷,推進形勢嚴峻。國際政府間談判舉步維艱,難以取得實質性、可操作性的進展,國際談判已經陷入僵持階段。”陳迎告訴記者。“面對這種難以推進的國際間政府談判,民間組織、地方政府組織積極行動,開展合作形式簡單、容易操作的推進模式。”陳迎說,在里約期間,她參加了兩次規模宏大的邊會,“一次是地方政府可持續聯盟召開的邊會,主題是世界各國地方政府可持續發展經驗借鑒與推廣,這次邊會有來自180個國家、1200多個城市、1500個主要城市負責人參加,會期3天。會議中見到不少亞洲面孔,臺中、臺南、首爾等都是高層官員參會。另一個邊會是C–FORTY召開的,與上一個邊會的性質相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綠色經濟、生態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設中都有一定的經驗,應該積極參與這樣的邊會。要兩條腿走路:國際政府間談判要力爭本該屬于我們的權利;另一方面,用民間合作、地區合作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進程。”
總之,發達國家與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角力仍在激烈的進行,政治形勢、力量對比都在發生較為深刻的變化。可以說,世界正在加速重整,新的秩序和規則還在形成過程中。在這個當口,很難想象出現什么極具行動力和決斷力、足以預期未來成效的國際共識。真正決定有效性的,將是下一個階段的現實格局。也就是說,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合力,或領導者正在重新孕育之中。在這個格局到來之前,在新的推動合力、領導者出現之前,應該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推進環境保護,推進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理性認識峰會成果
曾經被寄以厚望的“里約+20”峰會如期開幕,又如期閉幕了。對于峰會的成果,政治家們為了能夠今后繼續談下去,為了彼此都有些顏面,才在最后時刻達成妥協——如果這個妥協達不成,那么政府機制的談判就將徹底決裂——這對于推進環境保護、推進可持續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尤其對于亟待資金、技術支持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公民社會不必過于悲觀
談判過程是極其艱苦的。6月14日下午,77國集團(發展中國家集團)將正在進行的一場磋商會“叫停”。77國集團談判代表表示:若不在“行動措施”(包括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談判上有所進展,他們將拒絕進行綠色經濟的“小組磋商”會議。而談到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問題,歐盟的一位代表竟然說:“誰有錢,就找誰去!”大有“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拼命架勢。經過再三談判,相互妥協,在峰會成果文件中寫上了強調建立5130億美元可持續發展資金的文字。還有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歐美國家一直力圖將其改成共同無差別的原則。盡管相對于1992年地球峰會而言,對于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的強調弱化了,但畢竟保住了。
關于峰會的成果,中國籌委會代表團團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鷹22日說,本次大會最終達成的成果文件,內容全面、基調積極、總體平衡,反映了各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主要關切。盡管這些關切,是以前早就確定的,而且原則性、政治性遠超實質性、操作性,但正如杜鷹所說,最終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使國際發展合作指導原則免受侵蝕,維護了國際發展合作的基礎和框架。因此,峰會在談判環境激烈、復雜的情況下,能夠在原則性、政治性上再次取得一致,不能說不是積極的成果。下一步的關鍵是如何行動,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說,“'里約+20'峰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讓我們共同期待未來,不只是宣言,更是切實的行動。”
關于這次峰會的成果,巴斯夫大中華區管理董事會董事長關志華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在今年的“里約+20”峰會上,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積極采取行動,以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消耗,尋求更加可持續的發展。”“企業界期望作為解決方案供應商獲得認可。這與1992年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里約地球首腦會議時有很大不同。20年前,企業界并未發揮作用;如今,企業需要證明其公信力、嚴肅性,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由此可見,此次峰會還是有些實質進展的。

“里約+20”峰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讓我們共同期待未來,不只是宣言,更是切實的行動。
可持續發展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機制、系統
對于這次峰會成果的不甚理想,青年里約小組和不少民間組織認為是公民社會對政府間談判壓力不夠。對此,陳迎說,“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壓力夠大了吧?最終仍然沒取得實質進展。”實際上,如果冷靜回首過往的20年,就會得出可持續發展困難與進展共存的現實。這在6月6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全球環境展望5》報告中有客觀反映:盡管有8個項目非但沒有進步,反而繼續惡化,但畢竟有40項取得了進步,有4項取得了顯著進步。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郇慶治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與人類現代文明的綠色進化與變革相伴隨的相互學習過程,絕非只是發展中國家向西方國家學習或西方國家將現成模式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過程,是一條長期探索道路基礎上的更高發展階段和目標,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認真、嚴肅對待的復雜、系統的難題。“表面上看(本次峰會)不像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后那樣收獲頗豐,但這主要是由于一個兩極化世界中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切實困難(可持續的基本前提是發展的相對平衡),而且的確還是有一些實際進展,尤其是在共識聚合和闡發以及公眾意識培養方面。”郇慶治說。
中國要知道自己的處境
在本次峰會上,國際社會基于不同的目的對中國寄予厚望:發展中國家(不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地區)希望中國能當帶頭大哥;發達國家希望中國和他們承擔共同無差別的責任。“中國政府應該時刻想著自己的處境。”陳迎表示,盡管這次把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寫進文本,但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歐美國家認為,情況變化了,中國強大了,就得和他們一道負共同無差別的責任,這樣的論調,也來自最不發達國家(地區),中國等于是腹背受敵。”
不容置疑,的確,中國有著對于可持續發展最強有力的承諾,但這股力量目前并沒有轉化成強有力的國際領導力。同樣,被寄予厚望的基礎四國并未形成統一的政治立場并施加影響。“金磚國家在積蓄實力、擴大影響。在時機成熟之時,它們會在新的國際格局中擔當起新的責任。傳統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不太可能被完全取代,未來很有可能將是一種協調制衡的新格局。”徐楠如是說。這種新格局,就是舊秩序消失后,新秩序最終形成的結果。現在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也就是說,可持續發展的合力正在重新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