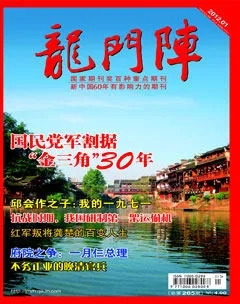北川鐵路憶舊
江義高
幼年時,我家住在文星場(現(xiàn)屬重慶市北碚區(qū)后豐巖鎮(zhèn))往北碚方向一公里遠(yuǎn)的一個名叫“新灣”的院子里。父親長年在外打工,母親在家耕種土改時分得的幾畝坡地。院子前有一條鐵路,路基低于院子三四米。每當(dāng)聽到遠(yuǎn)處響起“嗚——嗚”的火車汽笛聲,我就和在院壩里玩耍的小朋友們一窩蜂地跑到院子邊的路口上居高臨下地看火車。只見長長的列車滿載煤炭,在車頭的牽引下“咔嚓咔嚓”地呼嘯著遠(yuǎn)遠(yuǎn)而來,又從眼前“咔嚓咔嚓”地呼嘯著遠(yuǎn)遠(yuǎn)而去。那高亢的汽笛聲震撼著山村,也震撼著我的心靈。我總是目送著火車從視線里消失后,才悻悻地返回院中。
等我稍微長大了一點,姐姐就帶我到鐵路上去玩,告訴我哪是鐵軌,哪是枕木,哪是鋪路石,還教我聽到遠(yuǎn)處有火車的叫聲就要趕快離開鐵軌。鐵路兩邊各有一道兩尺來寬的人行道,偶爾可見上面有自行車行駛。這時,大一點的調(diào)皮娃兒往往會唱“洋馬兒叮叮當(dāng),上面坐了個死瘟喪(四川方言:罵人語,指討厭的人)”。惹來騎車人憤怒地咒罵后,調(diào)皮的娃兒才得意洋洋地嬉笑著逃去。每逢趕集,母親便挑著從坡地里收獲的蔬菜,沿著鐵路邊的人行道到文星場去賣,賣完菜后總要給我買點白糖糕、棒棒糖之類的零食。我5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和姐姐趕著一頭肥豬到文星場去賣。姐姐牽著豬在前面走,母親在后面用楠竹篾片趕豬,我也拿著一根小篾片跟在母親身邊幫忙。走到萬家灣時,一列火車鳴著汽笛駛來,肥豬受到驚嚇,掙脫繩子沖進(jìn)了路邊的水田。母親怪姐姐沒有把繩子拉緊,姐姐怪肥豬的力氣太大,我則急得哇哇大哭,后來好不容易才在路人的幫助下把豬趕了出來。
我會數(shù)數(shù)后,每當(dāng)有火車駛過時,就站在鐵路邊和姐姐一起數(shù)車皮。我們那時還玩一種看誰在鐵軌上走得遠(yuǎn)的游戲,兩人各站在一根鐵軌上,同時從某一點出發(fā),看誰走得遠(yuǎn)而且不從鐵軌上掉下來。雖然姐姐比我大8歲,卻常常輸給我。
再大一點,我便從大人的口中知道了從我家門前開過的火車是把從天府煤礦開采的煤運往白廟子,然后裝上停泊在嘉陵江邊的木船運往重慶。列車前面的車皮都是裝煤的貨車廂,最后兩節(jié)是搭載客人的客車廂。運送的煤分兩種,一種是從礦井開采出來的原煤,另一種是經(jīng)過加工后的焦炭(當(dāng)時都叫嵐炭)。因車皮裝得太滿及運行中的顛簸,原煤和焦炭免不了會從車上撒落下來,這給住在沿路的村民帶來了“實惠”,家家戶戶基本上不用花錢買煤,只需勤快一點,就可以在鐵路兩邊撿到煤炭。撿原煤的辦法是“掃”:先把路基上的鋪路石一段段地移開,地面上露出指頭厚的一層原煤,用掃帚把這些煤掃在一堆,用撮箕“撮”走后,再把移動的鋪路石還原。我家就一直靠姐姐和哥哥“掃煤”來解決煮飯、煮豬食的燃料。運氣好的時候,碰到列車上那堆得高高的焦炭“垮一網(wǎng)”下來,能供一戶農(nóng)家燒十天半月的。有一次,我和姐姐一起到表姐家去串門。沿著鐵路快走到表姐家時,一列拉著焦炭的火車從我們身邊飛馳而來,我倆慌忙到鐵路邊的一塊草坪上去避讓。剛到草坪,車頭便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在“咔嚓咔嚓”的聲響中,一節(jié)車皮上“轟”地垮下一大“網(wǎng)”焦炭來。火車開過去后,姐姐欣喜地說:“老五,我在這兒守著,你趕快到表姐家去報信,叫他們來挑焦炭。”聽了姐姐的話,我飛快地跑往表姐家。表姐夫來挑了一大挑,表姐也背了一大背篼,我和姐姐還各抱了一大塊,才把那些焦炭搬完。
童年的記憶非常深刻,離開家鄉(xiāng)后,那鐵路、那火車、那震撼山村的“嗚——嗚”汽笛聲和“咔嚓咔嚓”的車輪撞擊鐵軌的聲音,時時在我腦海里出現(xiàn)。
1964年下半年,我讀初中三年級,有一次上語文課,語文老師朱英華布置了一篇《美麗的家鄉(xiāng)》的作文。我在作文中描寫了童年時代家鄉(xiāng)的美麗,寫了院子前的那條鐵路。作文交上去后沒兩天,朱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興奮地問我:“你小時候住在文星場,家門口有條鐵路?”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他又問:“你知道那條鐵路叫什么嗎?是誰主持修建的嗎?”我搖了搖頭。他說,那條鐵路雖小,卻是四川地區(qū)最早的鐵路。接著,他告訴了我那條鐵路的命名及修建背景。
他說,這條鐵路北起于合川縣的大田坎(現(xiàn)屬重慶北碚區(qū)),南止于江北縣的白廟子(現(xiàn)屬重慶北碚區(qū)),故命名為北川鐵路。這條僅十幾公里,只跑企業(yè)內(nèi)部小火車的鐵路,從醞釀到建成通車,前后花了近10年時間。之所以要建這條鐵路,是因為天府煤礦的煤炭原先都是靠人力肩挑背扛運到白廟子嘉陵江碼頭裝船運走。這一帶山路崎嶇,人力運輸效率極低,成本極高。1925年,江北、合川的有識之士唐建章、李云根、張藝耘等人,倡議修輕便鐵路,用火車代替人力挑運。但由于資金、征地等問題久久不能解決而未能如愿。1927年,愛國實業(yè)家盧作孚主政北碚后,排除重重困難組建了北川民業(yè)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籌集到了資金,聘請丹麥人守爾慈為總工程師,著手勘測地形,修建鐵路。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直到1934年從白廟子到大田坎全長16.8公里的鐵路才全部建成通車。全線設(shè)白廟子、水嵐埡、文星場、后豐巖、大田坎等11個車站。
聽了朱老師的介紹,我才知道,原來這條鐵路的修建竟經(jīng)歷了這么復(fù)雜艱難的過程。
朱老師還告訴我,這條鐵路為抗戰(zhàn)作過貢獻(xiàn)。抗戰(zhàn)爆發(fā)后,重慶成為陪都,其1/3以上的能源供應(yīng)靠這條鐵路運輸,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朱老師見我對他的介紹聽得如此入神,就對我說,你所知道的僅僅是從文星場到白廟子這一段。今后有機(jī)會,我?guī)闳套咭惶诉@條鐵路。我說,要得。
初中畢業(yè)后,我考上了市里一所重點中學(xué)讀高中。1967年初,時值“文化大革命”,學(xué)校成天搞“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可批來批去就那么幾句話,無聊極了。此時,我想起朱老師承諾帶我考察北川鐵路的往事來,便興沖沖地回到母校找朱老師,可他已被造反派打成了“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成天掛著黑牌沖廁所、掃操場,行動沒有自由。我只好決定一個人徒步考察北川鐵路全線。于是,我乘車沿渝碚公路到了白廟子,回到了闊別11年的故鄉(xiāng)。
啊,變了!嘉陵江上沒有了往來如織的運煤船。當(dāng)初熱鬧繁華的白廟子街也冷冷清清的,更不見鎮(zhèn)后坡壁上的“梭槽”有煤炭“梭”下來。我有些納悶。
我沿著當(dāng)年下山的石梯拾階而上。當(dāng)初被煤塵染黑的石梯又逐漸顯出原來的本色。走完石梯,來到記憶中的白廟子火車站的“壩子”,只覺“壩子”變小了,壩上沒有了鐵軌,只有荒草和凌亂的碎石,四周靜悄悄的空無一人。我清楚地記得,鐵道是從“壩子”的右側(cè)延伸過來的,我堅定地從右側(cè)那突出的路口往前走去,欲尋覓當(dāng)年的鐵道。在“文革”的大串聯(lián)中,我到過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見識過火車。此刻,我猛地覺得腳下這窄窄的路基不可能承載“鐵路”,難道我走錯了地方?這時一個挑著菜筐的農(nóng)民迎面走來,我忙上前向他打聽。他告訴我說,這就是以前通往文星場的鐵路路基,幾年前鐵軌就拆了。聽了他的話,一種莫名的惆悵涌上心頭,我站在那兒默默地呆立了十幾分鐘,只得掃興地“打道回府”。
后來我才得知,隨著天府煤礦老礦的開采價值漸失及新礦的開發(fā),北川鐵路已分期分批被拆除,而新礦區(qū)開發(fā)的煤炭則從磨心坡那條路運往黃桷樹鎮(zhèn)了。
重慶三峽博物館建立后,有一次我去參觀,看到館里陳列著一個小小的火車頭。我最初以為是個模型,看了解說詞才知道,這就是當(dāng)年奔跑在北川鐵路上的55千瓦蒸汽機(jī)車的火車頭。
北川鐵路是在舊中國國弱民窮、四川軍閥連年混戰(zhàn)的背景下,依靠民營經(jīng)濟(jì)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建成的。盡管它已經(jīng)完成歷史使命,銷聲匿跡了近半個世紀(jì),可它承載了以盧作孚為代表的一代愛國實業(yè)家富民強(qiáng)國的美好愿望,也給我的童年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記憶。(壓題圖:存放在“重慶三峽博物館”的小火車頭)(責(zé)編: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