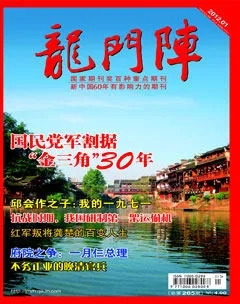東城根街的故事
姚錫倫
街名京味兒十足
舊時,成都穿城九里三,老城區內500余條街巷,哪條街最長?據《成都城區街名通覽》記載,是東城根街。這條街由東城根南街、上街、中街、下街和老東城根街、橫東城根街6條街組成,全長1989米。
東城根街很長,但《李劼人說成都》一書中說它“成街日子較淺”。該街始建于民國之初,不足百年。街名中的“東城”,特指清代滿城(亦稱少城)的東城墻,而非成都大城的東城墻。清初,滿蒙八旗官兵打進成都,他們的家眷也一起來此安營扎寨,在成都的西邊修建了滿城。過去許多外地人到成都,因為不了解這段歷史,對這條分明是位于成都西邊的街卻稱“東城”而感到不解。這滿城的東城墻還與明蜀王府的外城西墻有關。辛亥革命后,在拆除滿城東城墻時,曾發現此墻雜有明代城磚,還有蜀王府建造人姓名,這也足以證明滿城的東城墻是以蜀王府外城的西墻為墻基的。而“城根”,是指“靠近城墻的地方”。將“城根”作為街名源于北京方言。滿族人歷來將靠近滿城東城墻的地方叫“東城根”,所以民國初年拆除滿城之后,在這里形成的街道也自然而然地被命名為“東城根街”了。
在成都方言里,歷來沒有“城根”一說,北京人稱之為“城根”的地方,老成都人叫“城墻邊兒”或“城邊”。比如,靠老南門城墻有一條街就叫“城邊街”(今更名為錦里東路)。今天的琴臺路在20世紀70年代也因它靠城墻的緣故,曾被命名為“西城邊街”。很明顯,東城根街的街名,與滿城和滿人有關,現在北京也還有叫“皇城根街”的街名。
辛亥革命后,滿城內的胡同一律廢除,統統改名為街巷,靠滿城西城墻的西城根街也被更名為同仁路。最后連“東城根街”這街名也差點改名。1918年,當時的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將此街命名為“靖國路”,還在今天的東勝街口立有一碑,上書“靖國路”。由于群眾沒接受,這個靖國路的街名最終沒有流行,市民仍舊稱這街為“東城根街”。“東城根街”這個滿城的活見證、一條有著濃郁北京味兒的街名就這樣幸存下來,確實是十分難得。
紅樓不是夢
許是老街情結太深吧,我有一位朋友一提到他土生土長的東城根街就很洋盤,開腔就說:“我們這條街西靠省委,東臨市委,那可是省市委直接領導下的一條街。”接著又說:“要是回到20世紀50年代,五一、十一皇城壩開大會,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一過主席臺,只消一會兒就得‘乖乖地倒拐,從東城根街經過,我們坐在家門口就能‘檢閱游行隊伍。再一抬頭還會看見飛機在撒傳單,那才叫‘近水樓臺先得月啊!”說到高興時,老兄免不了還會炫耀這街當年“擴街建紅樓”的光輝歷史。
老兄所說的紅樓,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從東城根上街一直到東城根下街,在街的西側所建造的一幢幢3層磚木結構的紅磚房。1962年,我供職的西城區蔬菜公司就在東城根上街,每天上下班都會路過這里,看到一棟棟外表沒有抹水泥,全是光胴胴(四川方言:裸露的)的紅磚房。老百姓把這些紅磚房稱為“紅樓”。再按所處方位的不同,又分別將靠桂花巷的叫“桂樓”;靠仁厚街的叫“仁樓”,靠多子巷的叫“多樓”……
為何要在這條街上建那么多紅樓呢?
當時的省市有關領導都覺得,成都一直沒修一條像樣的街道,沒有修成片的街房。于是為壯觀瞻,決定擴寬并整修進出省委必經之路的東城根街,同時投資修建兩邊街房。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只在街西邊修建了“紅樓”,而東邊破爛的民房卻依然保留著。今天看來,那時所建的紅樓就質量、外形與現在的樓盤相比,簡直太寒酸了。但在當時,突兀而起的一溜樓房,著實讓成都市民眼前一亮,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大手筆了。久住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瓦片兒房”的市民喬遷紅樓之后,都會驕傲地說:“紅樓夢,紅樓夢,而今紅樓不是夢。”顯得很知足。
當然,成都的舊城改造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難忘的教訓。當年主管城市建設的領導馬識途就在他的《解放初期成都城市建設的日日夜夜》一文中擺過這樣一個精彩的笑話:為了保存人糞支援農業生產,有領導提議,在東城根街北頭修了幾個單元帶有旱廁的住房,每一層人家都在后房有一間旱廁,上下相通,屙屎撒尿可以從四樓廁一直掉到底層茅坑里。上面有人方便,下面就傳出咚咚之聲,頗為壯觀。只是因為不能像抽水馬桶那樣地放水沖洗,那臭味便無法去掉。幾層樓的住戶都反映太臭了!罵我們出這樣的“臭主意”。沒有人愿意去為貢獻寶貴的肥料而天天聞臭氣。那棟“名居”早已被改造掉了,那段“高空作業”且彌漫著不快氣味的往事,今天知道的人恐怕也不多了。
難忘“錦春樓三絕”
東城根街在許多“老成都”的記憶里,最讓人刻骨銘心的莫過于“錦春樓三絕”。
錦春茶樓位于東城根南街口,其“三絕”中分別是賈瞎子演唱四川竹琴,周麻子摻茶,司胖子賣的花生米。
四川竹琴,又稱道琴,始于道教演唱二十四孝之勸善說道。據傳,成都著名竹琴老藝人瞎子賈樹三僅用一個竹筒、兩片竹片作樂器,即能一人唱出一臺戲,且唱多個角色。千軍萬馬的氣勢、悲歌慷慨之情都在他的精彩的演唱中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難能可貴的是,他善于把川劇和揚琴的唱腔精華融入竹琴演唱中,開創了“賈派竹琴”。聽他的演唱,人人屏氣凝神,個個如癡如醉。當年抗日將領馮玉祥,一聽完賈瞎子的演唱,便贊不絕口:“成都的賈樹三完全可以跟北方京韻大鼓鼓王劉保全并稱雙絕。”
第二絕就是周麻子的摻茶絕技。只要茶客一入座,他即右手提壺,左手卡著一摞銅茶船和白瓷茶碗,來到客人座位前。只見他手一松,“嘩”的一聲脆響,茶船全都撒落在桌上飛快地旋轉起來,待這些茶船還沒“安靜”下來,個個茶碗即穩穩當當地被他放到茶船上。緊接著,一柱水從1米之外的銅壺內傾瀉而下,斟滿每個茶碗卻滴水不漏。茶客觀之,正瞠目結舌之時,他再用小指把茶蓋輕輕一挑,茶碗就被蓋得嚴嚴實實。就連慕名而來的馮玉祥,也不得不心悅誠服地贊美周麻子:“不錯,你算一絕!”至于周麻子真名叫啥?好像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最后一絕則是司胖子賣的花生米。茶客要想吃到他賣的花生米,必須等到賈瞎子唱完一折戲后中途休息這個時段。這時,一聽樓梯響,就可見司胖子和他徒弟提著幾個大包上樓來。客人只要一示意,他立馬就給你送上一包花生米,一包瓜子。拆開一看,顆顆花生米大小一樣,勻勻凈凈(四川方言:很整齊)且紅衣完好無損,丟在嘴里一嚼,又香又脆。這又是一絕!
可惜,今天我們已無緣領略“錦春樓三絕”了!但它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絕活,我們依然期盼著有人將之傳承下去。
街邊茶鋪
今天大家看到的老東城根街,早先它并不叫這個名字,而是叫東城根下街。它的易名與街道擴建有關。20世紀50年代,擴建東城根街時,為了把街拉直,切斷了東城根下街的彎道。在原東城根下街以西,橫穿紅墻巷、過街樓及東二道街新開辟了一段街直至八寶街,這就是實際意義上的“新東城根街”。興許是當初考慮到這條新辟的街道既在主干道上,又與東城根中街緊緊相連,于是這段新街最終沒有“按慣例”命名為“新東城根街”,而是讓它取代了原東城根下街之名。這樣一來,原來的東城根下街只好改名,1981年地名普查時,正式更名為了“老東城根街”。
老東城根街朝向東北,僅是一條狹窄的小巷而已,少了車馬的喧鬧,稱得上是一條鑲嵌在鬧市中的幽深小巷。因其不當道,曾一度被辟為“東下農貿市場”。小巷南端,是赫赫有名的四川省曲藝團。揚琴大師李德才、諧劇創始人王永梭、清音演唱藝術家肖順瑜、二胡演奏家車向前等名家以及他們的傳人均匯聚于此。
省曲藝團旁,株株芭蕉、棕櫚、銀杏樹陰下的街邊,便是“社區小茶園”。天氣好時,這里茶客真不少。茶不貴,三五元一杯。茶客中年長者居多。最長者是103歲的龍驤老大爺,他的家就在本街上,僅隔茶園數米遠。來這里喝茶的老茶客都知道,他畢業于黃埔軍校,后來是百貨公司的老職工,81歲才退休,是這兒最受愛戴的老人。我見過他,視力很好,看報還能看清標題,也略知內中講了些啥。不消說,他來喝茶是免費的,只要見他杯中水不多了,小茶園的老板自然會親自來給他老人家斟上。
我也常到這里喝茶。茶園的設施顯然上不了檔次,無非是安放了些普通人家常用的方桌、圓桌、小茶幾,竹椅、木椅、鋼架椅之類。每桌配開水瓶1個,供茶客自斟自飲。設施雖然簡陋了些,但卻貼近尋常成都百姓的實際生活。我們這些住慣了瓦片兒鋪板房、有著類似經歷的老人在此喝茶,免不了會觸景生情——想當年,誰家不是這樣?閑暇時光,抬上一把小竹椅或馬架子在自家門口喝茶不也是這般“風景”么?難怪有人感慨:這兒喝茶,真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只是如今的成都到處高樓林立,像這類街邊茶園已經不多見啰!
老人們在茶園喝茶、擺龍門陣,快到下午4點半時,有幾位大爺便微笑起身,拱手告辭,他們被茶客們戲稱為“雙規人士”——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東城根街小學門口”接孫子回家。
“雙規人士”剛離去,又有大爺坐不住了。他們不是去學校接孫子,而是趕著到“省委機關食堂”買全家人都愛吃的包子、饅頭、窩窩頭。省委機關食堂離“社區小茶園”不遠,就在東城根中街3號。據我所知,“食堂”對外服務已有些年頭了,天天都要供應面點、豆制品和鹵菜等熟食,品種多達近百種,深受群眾歡迎。購買者以附近居民為主,也有搭公交車、開車趕來的“遠客”。由于買主多,排輪子是常有的事,而且還不能去晚了,否則就賣完了。有老買主對我說,這兒的東西干凈衛生,沒得潲水油,吃起來放心。
(壓題圖:《老成都食俗畫》林洪德繪)(責編:王 容)